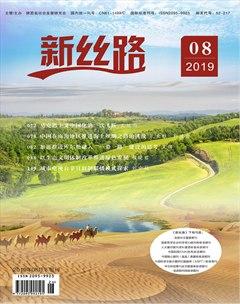變與不變
吳小軍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黔東南地區(qū)銀飾鍛制技藝在當(dāng)下社會(huì)轉(zhuǎn)型中變與不變的內(nèi)容,以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對(duì)該地區(qū)的工匠遷徙和技藝體系等方面進(jìn)行梳理和總結(jié)。社會(huì)發(fā)展、市場(chǎng)細(xì)分以及文化變遷是多元發(fā)展的主因,深入理解和研究苗族特有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傳統(tǒng)銀飾的技藝體系才是傳承與發(fā)展的理論基礎(chǔ)和發(fā)展方向。
關(guān)鍵詞:藝術(shù)人類學(xué);苗族銀飾;黔東南;民間工藝
貴州黔東南地區(qū)的雷山縣、臺(tái)江縣和劍河縣的銀飾鍛制技藝先后入選第一批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和第三批國(guó)家國(guó)家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擴(kuò)展項(xiàng)目名錄。該地區(qū)有著豐富的苗族銀飾種類和深厚的銀飾文化,不同地區(qū)產(chǎn)品的樣式、造型、圖案和佩戴方式均有差異,苗族銀飾的傳統(tǒng)技藝在歷史沿革和現(xiàn)代工業(yè)的影響下也呈現(xiàn)多元發(fā)展的態(tài)勢(shì)。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在關(guān)于加強(qiáng)我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隨著全球化趨勢(shì)的加強(qiáng)和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加快,我國(guó)的文化生態(tài)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 [1]。作者在凱里雷山控拜村、臺(tái)江施洞鎮(zhèn)及塘龍村和凱里市考察過程中發(fā)現(xiàn)原有苗族地區(qū)的銀飾鍛制工藝在當(dāng)下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間存在諸多問題,如:施洞鎮(zhèn)及塘龍村地區(qū)的傳承人整體年齡結(jié)構(gòu)偏大,后繼乏人;控拜村的工匠則集中向各級(jí)城市遷徙,本地手工藝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堪憂;凱里市區(qū)的機(jī)械設(shè)備和精密鑄造不斷替代手工,市場(chǎng)上機(jī)制產(chǎn)品和手工產(chǎn)品魚目混珠等。
一、發(fā)展現(xiàn)狀
臺(tái)江縣施洞鎮(zhèn)及塘龍村是以“座家”方式為主進(jìn)行銀飾的打制和經(jīng)營(yíng),施洞鎮(zhèn)上有名的銀匠是劉永貴、劉永福和劉永龍三兄弟,塘龍村則以吳姓為主,較為有名的是吳通云、吳智等師傅。施洞鎮(zhèn)或塘龍村所制作的銀飾主要面向本地及周邊苗族,偶有上門定制或外來游客作為旅游產(chǎn)品少量購(gòu)置,主要通過鎮(zhèn)里的集市在趕集過程中銷售。其“座家”的意思是指在鎮(zhèn)里或村里有固定的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場(chǎng)所,因此工匠師傅一般都較為注重自身的產(chǎn)品質(zhì)量和工藝水平,目的是為了樹立良好的工藝和市場(chǎng)口碑并形成長(zhǎng)期經(jīng)營(yíng)的態(tài)勢(shì)。雷山縣控拜村是有名的銀匠村,原本該村幾乎所有男性都會(huì)打制銀飾,其祖上流傳下來的制作技藝和早年農(nóng)閑時(shí)挑著工具箱進(jìn)行串寨上門打制銀飾的習(xí)慣和經(jīng)驗(yàn)讓本地工匠聲名遠(yuǎn)揚(yáng)。但作者在控拜村考察時(shí)發(fā)現(xiàn)村里幾百戶人家家中目前只有陽(yáng)太陽(yáng)一家在制作銀飾,其余銀匠遠(yuǎn)走他鄉(xiāng),家中僅有留守老人和兒童,甚至部分人家大門緊鎖常年無人居住。控拜村原有的銀匠主要前往雷山縣、凱里市、貴陽(yáng)、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去加工或經(jīng)營(yíng)銀飾,銀匠的流失已經(jīng)導(dǎo)致了本地銀飾制作的工藝環(huán)境受到嚴(yán)重破壞,已形成了一個(gè)沒有銀匠的銀匠村。
圖一 ?節(jié)慶中穿戴銀飾盛裝的凱里市區(qū)苗族
二、變與不變
苗族銀飾鍛制工藝是對(duì)其工藝體系的總稱,其“鍛”有鍛造、打造之意,是黔東南地區(qū)民族民俗文化中對(duì)銀制品制作工藝的民間認(rèn)識(shí)。是苗族地區(qū)銀匠對(duì)銀材質(zhì)物理和物性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之上所進(jìn)行的熔煉、鍛打、壓片、拉絲、編結(jié)、模壓、鏨刻、銼磨、金珠粒、焊接、打磨、拋光等工藝環(huán)節(jié)的綜合稱謂,也較為形象的概括了銀飾制作的過程。縱觀整個(gè)凱里地區(qū)的苗族銀飾,一是以花絲工藝為主所制作的各種發(fā)簪、項(xiàng)圈、手鐲及手圈、吊墜、耳墜等首飾;二是以鏨刻工藝為主所制作大銀角、小銀角、銀圍帕(俗稱馬牌)、龍項(xiàng)圈、銀衣上的各式銀片、大銀梳等產(chǎn)品;也有花絲和鏨刻工藝綜合運(yùn)用所制作的產(chǎn)品樣式,并在技藝傳承和延續(xù)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苗族民族特色和地域風(fēng)情的銀飾鍛制技藝體系。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這種傳統(tǒng)工藝也在發(fā)生著不同程度的變遷,表現(xiàn)出了“興盛”“變異與延續(xù)并存”等不同的變遷模式[2]。下面主要從銀匠以及工藝兩方面進(jìn)行論述。
1.銀匠的守望和遷徙
控拜村本地銀匠帶有集體遷徙特征的現(xiàn)狀與控拜所處地域及工匠的思想有關(guān)。首先,控拜村所處山區(qū),原有半農(nóng)耕半手工以手藝輔助農(nóng)業(yè)并達(dá)到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方式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造就了中國(guó)第一銀匠村的繁榮景象,但原有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本身就屬于為周邊地區(qū)服務(wù)的性質(zhì);第二是世代以走街串巷上門打銀為生的游藝活動(dòng)中積累了豐富的手工藝經(jīng)驗(yàn)并拓展了對(duì)不同苗族支系及其他民族對(duì)銀飾文化細(xì)分差異的認(rèn)識(shí)。游藝的生活方式使其往周邊遷徙更具有可行性和實(shí)踐性;第三是遷徙后所形成的新的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條件及市場(chǎng)等工藝環(huán)境比控拜村現(xiàn)有狀況更好,更有發(fā)展的空間和創(chuàng)造財(cái)富的機(jī)遇;第四是遷徙本身即是一種文化的流通與融進(jìn)過程,對(duì)外界文化的認(rèn)識(shí),新工藝、新技術(shù)的接收和轉(zhuǎn)化以及自身手工藝的拓展都具有良好的融通作用。因此,控拜村銀匠在社會(huì)發(fā)展過程中不斷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最終形成了現(xiàn)在的遷徙狀態(tài)。施洞鎮(zhèn)及塘龍村在守望中也有遷徙,如劉氏三兄弟的中子女也分別前往貴州凱里、湖南鳳凰古鎮(zhèn)等地開設(shè)銀飾加工小作坊,以手工藝與現(xiàn)代機(jī)械合作加工生產(chǎn),其生產(chǎn)產(chǎn)品既有祖輩所傳下來的一些傳統(tǒng)樣式,也用機(jī)械沖壓生產(chǎn)部分現(xiàn)代銀飾商品。控拜村集體遷徙的大背景下還有陽(yáng)太陽(yáng)一家繼續(xù)留守,沿襲著傳統(tǒng)技藝的同時(shí)還以控拜村的地理資源開辦休閑旅游和手工藝體驗(yàn),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傳承方式。
銀匠的守望和遷徙都是銀匠根據(jù)自身的技藝或資源條件所做出的不同從藝方式的選擇,不存在厚此薄彼也不需要擔(dān)心技藝的消失,至少在當(dāng)代社會(huì)文化根基沒有本質(zhì)動(dòng)搖的前提下手工藝和工業(yè)生產(chǎn)方式可以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甚至互為補(bǔ)充。銀匠作為銀飾制作工藝的勞動(dòng)者,通過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制作銀飾品并獲得相應(yīng)的物質(zhì)利益才是最初的原動(dòng)力和能否傳承延續(xù)技藝的根本。同時(shí),銀匠當(dāng)其技藝達(dá)到一定程度和物質(zhì)條件得到一定滿足后往往會(huì)自覺的參與到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工藝的改進(jìn)以及文化的創(chuàng)造。
2.工藝的傳承與發(fā)展
在銀制品的制作過程中需要對(duì)銀材質(zhì)的屬性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苗族銀匠在歷代打造銀飾的過程中已經(jīng)熟練地掌握了銀的可熔性、穩(wěn)定性和延展性等物性,并在實(shí)踐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銀材料熔煉、鍛打模壓和拉絲編結(jié)等成型技術(shù),鏨刻花紋及花絲點(diǎn)綴等裝飾技術(shù)以及銼磨和清洗拋光等表面處理工藝。與其他地區(qū)或民族的銀飾制作工藝相比較,苗族的花絲工藝和鏨花工藝最具特色也頗有民族風(fēng)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