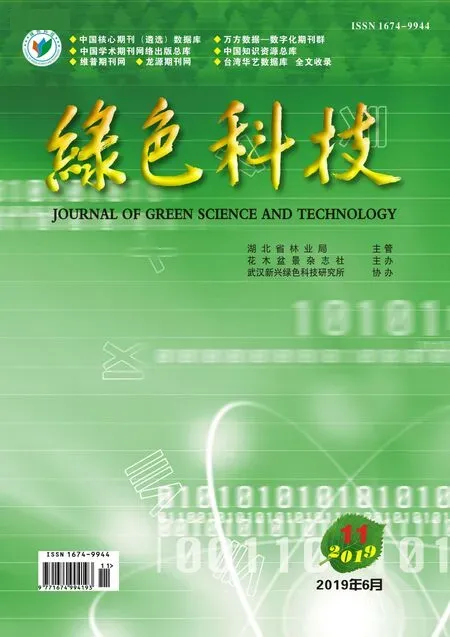植物地域性特征在園林營(yíng)造中的應(yīng)用
陳 方
(珠海城市建設(shè)集團(tuán)有限公司, 廣東 珠海 519000)
1 引言
目前,植物景觀營(yíng)造普遍存在著相互借鑒、模仿、甚至直接套用的現(xiàn)象,缺乏本土的手法和風(fēng)格,使城市失去了自己特有的色彩。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學(xué)者越來(lái)越注重植物地域性的研究,其主要通過(guò)植物群落、植物的季相性及文化來(lái)體現(xiàn),也有學(xué)者通過(guò)鄉(xiāng)土植物來(lái)體現(xiàn)植物的地域性。研究旨在解讀園林植物景觀地域性的基礎(chǔ)上,探討園林植物景觀的特征與表達(dá)手段 。
2 植物景觀地域性闡釋
地域性與 “地域 ”直接相關(guān) , 體現(xiàn)的是一個(gè)地域內(nèi)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的相對(duì)類似性 。地域性本身并不代表著差異性 , 只是由于地域本身存在差異 , 才造成了地域性之間的差異 ,從而形成了地域的個(gè)性[1]。
植物景觀的地域性指的是在特定的時(shí)間與空間范圍內(nèi),受當(dāng)?shù)氐臍夂颉⑺摹⑼寥馈⑽幕⒚袼椎纫蛩氐挠绊懀灾参锏男螒B(tài)、配置形式的方式來(lái)展示其差異性與獨(dú)特性,詮釋區(qū)域或是城市的特色。
3 植物景觀地域性特征
與其他景觀元素不同的是,植物景觀有其特有的生命性,也正是其生命性讓植物景觀更具活力。植物景觀的生命性主要體現(xiàn)在時(shí)間性和空間性上。
3.1 時(shí)間性
是指植物隨著季節(jié)的變化其形態(tài)跟著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花、葉、果實(shí)等器官,這種變化稱之為植物的季相性。植物隨著時(shí)間逐漸成長(zhǎng),形成植物群落,其空間的變化也給人不同的感受。在植物設(shè)計(jì)中應(yīng)充分考慮植物的生長(zhǎng)速度和季相性。如利用早花植物,營(yíng)造春花浪漫的景觀,營(yíng)造春季中生命銳意進(jìn)取、蓄勢(shì)而發(fā)的意境(圖1);種植冠大濃蔭的植物,以綠色為基底,營(yíng)造涼爽的景觀效果;種植彩葉植物樹(shù)種,營(yíng)造秋季色彩豐富的景觀效果;利用植物落葉后,干、枝所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或蒼勁、或柔美、或粗獷的姿態(tài),營(yíng)造冬季特有的景觀效果,構(gòu)建一副冬季水墨畫(huà)(圖2)。

圖1 植物早春效果

圖2 植物冬季效果
3.2 空間性
指的是通過(guò)植物配置所形成的植物空間。按植物的空間特點(diǎn)可分為私密性空間、開(kāi)放性空間、半開(kāi)放性空間。如通過(guò)綠籬的圍合,可形成私密性空間;通過(guò)大草坪形式形成開(kāi)放性活動(dòng)空間;通過(guò)樹(shù)林草地所形成半開(kāi)放空間。
4 植物景觀地域性的形成
4.1 植物生態(tài)習(xí)性地域性
我國(guó)地域廣闊,跨度大,從南至北跨越6個(gè)氣候帶,從東到西經(jīng)度跨越將近 60°,地理環(huán)境復(fù)雜,這樣特色的地域條件使得植物的地域性特征十分顯著[2]。全國(guó)共有8個(gè)植物區(qū)域:寒溫帶針葉林區(qū)域、溫帶針闊葉混交林區(qū)域、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qū)域、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區(qū)域、熱帶季雨林區(qū)域、溫帶草原區(qū)域、溫帶荒漠區(qū)域、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區(qū)域。如亞熱帶的棕櫚科植物,樹(shù)姿挺直高大,葉片飄逸瀟灑,采用叢植、群植搭配方式,可營(yíng)造濃郁亞熱帶風(fēng)情和海島情調(diào);如溫帶落葉闊葉的梧桐、柿樹(shù)、槐樹(shù)等,因西北干燥涼爽的氣候特征,植物生長(zhǎng)緩慢,主干明顯,分支少,在冬季形成枝干蒼勁的景觀形態(tài),與大西北的蒼涼、厚重感相融合。區(qū)域分布的植物是造成地區(qū)間園林植物景觀差異的必然因素,是形成地域特色的一個(gè)要條件。
4.2 植物文化的地域性
我國(guó)共有56個(gè)民族,不同民族其習(xí)俗及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因此其植物文化也不同。植物文化特質(zhì)分為時(shí)令類、民俗類、宗教類、比德類4種類型。時(shí)令類指植物的四季,如春日萬(wàn)紫千紅、夏時(shí)枝繁葉茂、秋至果實(shí)累累、冬季銀裝素裹;民俗類更多的反應(yīng)的是人類社會(huì)生活的需求,與民俗有關(guān)的植物文化特性主要通過(guò)植物的諧音、寓意來(lái)體現(xiàn)。如桂有榮華富貴之意,玉蘭+海棠則有玉堂富貴之意,柿樹(shù)+海棠則有幾世同堂之意。此外,古人用桃木制做桃符以避邪,門(mén)前插柳避鬼。西方古希臘將棕櫚樹(shù)、懸鈴木等作為神樹(shù);宗教類是指在寺廟內(nèi)常種植松柏類植物、銀杏等來(lái)烘托寺廟莊嚴(yán)的氛圍;比德類是將自然物象看作是人某種倫理道德的表現(xiàn)或象征,如屈原在《離騷》中就以香草比喻君子,作為人格高潔的象征。《楚辭》用香木、香草來(lái)比喻忠臣,而用惡木、惡草來(lái)諷刺奸臣。
5 地域性植物景觀營(yíng)造策略
5.1 依托鄉(xiāng)土植物營(yíng)造地域性特色
植物的生長(zhǎng)主要受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植物的選擇除了觀賞性外,還需考慮其功能性及適生性[3]。市花、市樹(shù)是城市最具代表性植物,應(yīng)作為城市的象征大量引用。例如廣州市市樹(shù)——木棉,樹(shù)形高大雄偉,春季紅花盛開(kāi),被廣州人譽(yù)“英雄樹(shù)”,木棉花也就成了“英雄花”,因此無(wú)論木棉以何種植物形式配置,都能凸顯廣州的地域性;棕櫚科植物在廣州大量應(yīng)用,已經(jīng)成為廣州植物地域性的代表。棕櫚科植物景觀有其獨(dú)特的觀賞性,列植高達(dá)雄偉,叢植層次分明,群植結(jié)構(gòu)豐富多彩,無(wú)論以何種方式配置,棕櫚科植物都容易營(yíng)造出熱帶、亞熱帶及海島風(fēng)情。此外,廣州還素有“花城”的美譽(yù),受地域的影響,廣州有大量的觀花樹(shù)種,如扶桑、紅花羊蹄甲、鳳凰木、黃槐等,這些觀花植物花期長(zhǎng),觀賞性好,與其他景觀搭配形成四季觀花的城市景觀。
5.2 依托季相植物群落構(gòu)建地域特色
植物的生長(zhǎng)周期決定了植物的季相性,以長(zhǎng)沙為例。長(zhǎng)沙的春季主要集中在4、5月份,春季主要觀花植物有櫻花、紫荊、白玉蘭、紫玉蘭、二喬玉蘭、海棠、桃等,以薔薇科,木蘭科植物居多,每年的4月份,植物園都會(huì)舉行櫻花節(jié);夏季以綠色濃郁的常綠喬木為主,仍有不少夏季開(kāi)花植物如復(fù)羽葉欒樹(shù)、廣玉蘭、紫薇等,及觀色葉植物金葉女貞、紫葉李、紫葉小檗等豐富夏季景觀;秋季景觀最突出的就是岳麓山,其主要秋色葉樹(shù)種為楓香、南酸棗、樸樹(shù)、欒樹(shù)、烏桕等,形成熱烈的紅色景觀。
5.3 依托植物文化構(gòu)建地域性特色
人們常將植物景觀的個(gè)體美進(jìn)行人格化,很多植物被人格化后往往具有其獨(dú)特的品格和象征意義[4]。植物文化中最常見(jiàn)的應(yīng)用為松、竹、梅,被譽(yù)為蘇寒三友。如香山公園的聽(tīng)法松,被譽(yù)為寺廟的“神樹(shù)”,二松為油松,常綠喬木,樹(shù)齡長(zhǎng)壽,寓意著寺廟香火不斷、源遠(yuǎn)流長(zhǎng);而“聽(tīng)法”的命名,又與寺廟的環(huán)境相呼應(yīng)。二松姿態(tài)挺拔,很好的烘托了寺廟莊重的氛圍,而兩冠又相對(duì)而生,大枝延伸,形式虔誠(chéng)佛教徒合手聽(tīng)法。無(wú)論從形態(tài)、寓意都很好的與寺廟相融合,達(dá)到了“寺因木而古,木因寺而神”的效果。
江南的園林常借助自然界的流水、風(fēng)聲、鳥(niǎo)語(yǔ)、日光等來(lái)凸顯植物的意境。如杭州的柳浪聞鶯,入園處列植柳樹(shù),而成排的柳樹(shù)讓人容易聯(lián)想到“兩個(gè)黃鸝鳴翠柳”的意境;拙政園的聽(tīng)雨軒,小天井內(nèi)種植芭蕉,借助雨水敲打芭蕉葉,形成窗前雨打芭蕉的意境。
6 結(jié)語(yǔ)
植物的地域性,有利于延續(xù)城市的文脈,展現(xiàn)城市的獨(dú)特性。要想充分展現(xiàn)植物的地域性,需要了解植物的生態(tài)習(xí)性、文化內(nèi)涵,從本土的人文風(fēng)情出發(fā),豐富植物群落,將植物的“情境、意境、物境”相融合,從而營(yíng)造其獨(dú)特的地域性植物景觀[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