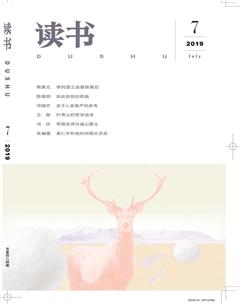景觀史記
唐曉峰
段義孚這本《神州》是半個世紀之前寫的。當時他受牛津大學地理學教授休斯頓之邀,為“世界風土叢書 ”(The Worlds Landscapes)寫一本關(guān)于中國地理景觀歷史的書,對象是英語讀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學時就有了這本書,但當時并沒有細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歷史內(nèi)容,就收起來了。現(xiàn)在譯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讀起來便捷,所以看得比較仔細了。雖然仍然要略過不少熟悉的歷史內(nèi)容,但對一些特質(zhì)的東西,也漸漸有所領(lǐng)悟。
段義孚在中文版的序言中點明了當初寫這本書的想法。除了在情感上要 “向故土致獻敬意 ”,在學術(shù)上,他是要 “寫一本不落窠臼的區(qū)域地理書 ”。所謂落入窠臼的區(qū)域地理寫法,是把自然與人文分別敘述,“缺陷是二者之間的割裂 ”。半個世紀前的情形確實如此,即使現(xiàn)在,做得好的也不多。《神州》努力將二者融合為一體。段義孚很幸運,中國的歷史地理特色恰恰是人地交融,這使他可以 “輕松地采取這種寫法 ”。
另外,他還希望地理學要 “將經(jīng)濟、社會和文學、藝術(shù)貫通起來。我期望這本書翻譯出版之后,能拋磚引玉,中國的地理學者能夠真正實現(xiàn)歷史與人文、經(jīng)濟與社會并重 ”。這是段義孚對中國同行的建言,也是呼應了他在原版序言中談到的一個重要觀點:
工匠的景觀是他的手工制品,他將自然界主要視為機會,他創(chuàng)造的景觀是見證人類意志和力量的豐碑,存在于幾千里長的大運河中,存在于巨大的布局嚴謹?shù)某且刂校嬖谟诮F(xiàn)代以來的鋼鐵廠、堤壩、水庫和治理沙漠的防護林帶中。但是景觀的含義遠比這里所歷數(shù)的幾種豐富得多。
作為人文地理大師,段義孚當然不滿足于 “工匠景觀 ”,而提倡更寬泛的人文景觀的概念。其實,對于整個地理學,何嘗不是如此?這正是中國地理學與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地理學的差異。中國目前的地理學中,充滿著帶有計量特色的 “工匠 ”精神。
在段義孚等人文地理學家看來,景觀不僅僅是景色,而是一種包羅萬象的復雜文本、感悟氛圍。休斯頓在主編序言中也簡略地談到景觀概念的歷史。Landscape這個英文詞的意義與中文尋常使用的 “景觀 ”是有區(qū)別的,應引起我們的注意。Landscape,“其盎格魯 -撒克遜語原詞是 landscipe,意指某個作為自然實體的地域單元 ”。這種情形下,它幾乎等同于一般所說的 “地理 ”。“直到十六世紀末,由于荷蘭風景畫家的影響,這個詞具有了視覺意義,也指一片景色。德文 landschaft一詞兼具兩種含義。”在西方當代地理學中,學者們在使用 landscape這個學術(shù)概念時,是指地表的整個 “情景 ”,不僅有面前的 “景況 ”,還有背后的 “情況”。
《神州》一書就是研究歷史景況和情況的書,可以稱為景觀史通論。它以歷史中景觀的演變?yōu)閿⑹轮骶€,這是其地理學屬性最重要的體現(xiàn)。而不像他后來撰寫的一批人本主義地理著作那么指向個體的內(nèi)心(段義孚因此獲得過心理學界的嘉獎),這本書的概述相當宏觀,充分體現(xiàn)了這位地理學大師多樣的駕馭能力。
我們當然也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情況。在中文版序言的最后,段義孚表達了二 ○○五年回中國兩個星期后的幾點感受。因看到公園、小區(qū)中人們下棋的悠閑、兒童嬉戲的溫馨,段義孚十分感慨:“如果我年輕二十歲(可惜我現(xiàn)在八十六了),我干嗎不把這些場景寫進我關(guān)于中國的書里?”公園小區(qū)的場景,對于離開中國幾十年的段義孚,是一個十分新鮮的 “地方 ”,是能催生想法的 “景觀 ”。這是段義孚人本主義的自然流露。
這本書的第一句話是:“追蹤人類主觀能動性對中國地貌所造成的種種變化,我們的討論理應從自然環(huán)境開始。”原始自然景觀,在人類的干預下,變?yōu)槿宋木坝^。這是美國地理學界伯克利學派(Berkeley School)的典型思路。索爾是這一學派的領(lǐng)袖。段義孚在伯克利大學地理系讀過研究生,自然會受這一思路的影響。
推動景觀變化的動力,大自然的力量當然是首要的,段義孚將中國古代文明核心區(qū)的自然地貌變化總趨勢,分為兩大類地區(qū):一個是水土流失區(qū),另一個是沉積區(qū)。在這兩類地區(qū)中,原始人類的發(fā)展是不一樣的。黃土高原是流失區(qū),東部黃淮海大平原是沉積區(qū)。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積區(qū)。今天,在沉積區(qū)的古代遺址,大都埋在地下深處。
相對于大自然的變化,人類對于自然環(huán)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經(jīng)驗意義,即歷史意義,在大地景觀層面上,足以顯示時代差異。而這類顯示歷史演變的景觀,又可以通稱為文化景觀。索爾說,文化景觀是變化的結(jié)果,文化是造成變化的動力。段義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稱造成變化的動力是人口。從文化層面回歸到人本身,這一觀點有些七十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地理學 ”的味道。
第二章 “人在自然中的作用 ”,代表本書的主要問題意識,或者說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卻、村鎮(zhèn)聚落發(fā)展、建筑景觀形態(tài)等,是全書關(guān)注的主要議題。在這一章中段義孚引述了索爾的話,強調(diào)人類在狩獵與采集的蒙昧時代便已經(jīng)開啟了改變景觀、使天然植被發(fā)生變化的進程。索爾對于細微變化的關(guān)注是令人贊嘆的。例如 “在營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進較多的陽光,也由于不怕踐踏和其他困擾,野草沿足跡在路邊叢生 ”。索爾的這種觀察,令人聯(lián)想到在課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實驗。事情雖然細小,但其示范意義是深遠的。
當然在歷史發(fā)展中,人類的影響是巨大的。段義孚在后面章節(jié)的歷史敘述中,往往從人口變化說起,這是動力。人類首先是對土地植被的干預,這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結(jié)果。接下來是村鎮(zhèn)、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這些事情在一般歷史敘事中常常出現(xiàn),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義孚在本書中則強調(diào)它們是景觀。因為是景觀,就要指出它們的重要細節(jié)。比如講漢代農(nóng)業(yè)景觀,段義孚參考《氾勝之書》,講到田間的細節(jié):“種糯小米的地塊位于桑樹之間 ”;在貧瘠地區(qū),“對山嶺、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圍墻里的坡地加以利用 ”;“稻田不應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適當?shù)乃?”;稻田 “肯定是地的坡度越大,田的面積越小。在等高的地形中小小的稻田連成或許窄窄的條條帶帶 ”。
中外景觀的對比,這對于在西方生活多年的段義孚,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很有意義的。我舉幾個例子。
“像(北美)連綿的嶺谷、圓形小山、低地、寬廣起伏的平原,這類地貌在中國并不多。”在中國,到處都是陡峭的山嶺,“只有直立和平面的鮮明對比,沒有類似于山麓小丘那樣柔和起伏的坡地作為緩沖 ”。大多中國山水畫正是取材于這些陡峭的峰巒。再加上被砍伐掉的林木,這些山從 “土質(zhì) ”變成了 “石質(zhì) ”,于是 “在中國山水畫中,林木蔥蘢的山景十分少見,多是光禿的山壁上矗立著幾棵頑強的松樹 ”。其實,森林在人類活動面前退卻,正是歐洲歷史中最主要的景觀變化之一,在歐洲歷史地理研究中是重要議題。段義孚對于中國的觀察,也十分關(guān)注這類問題。
而關(guān)于城鄉(xiāng)村鎮(zhèn)景觀,段義孚的看法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是 “寄生性都城的暴富和鄉(xiāng)村的貧困 ”。即使是富有的鄉(xiāng)村,也仍然不如城市的景觀顯赫。這種情況又與歐洲不同。在講東漢的塢壁即 “豪門大族的莊園”時,他說:“大莊園主富比王侯,他的宅邸有房屋數(shù)百,肥田沃土連綿阡陌,奴仆成千上萬。”“如果說的是歐洲,我們可能應設想一個豪華的鄉(xiāng)村住宅,或者甚至一座宮殿坐落在園林環(huán)繞的景觀中,周圍環(huán)繞著農(nóng)莊和務農(nóng)的村落。但是這幅圖景不適用于中國。”中國的 “鄉(xiāng)村宅邸可能闊大而興旺,但是一般來說在建筑上卻樸實無華。家族中胸少文墨,卻野心勃勃的成員住在那里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那些飽讀詩書,出相入仕的成員們則成為朝廷的命官,住在京城宅邸中 ”。
關(guān)于中國北方的院落,段義孚看到的景觀是房子圍出一塊空地,形成封閉院落,這與歐美院落圍著房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國主持費城建設的建筑師培根(N. Bacon)也曾發(fā)表過這樣的感慨。院落是基本生活單元的景觀,在這里也可以用現(xiàn)在人們喜用的新詞 “樣貌 ”,意思差不多。解讀封閉院落的 “樣貌 ”“情景 ”,是將注意力放在了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基礎層面。現(xiàn)在人們使用 “樣貌 ”這個詞,也是在強調(diào)畫面感。
為什么要有畫面感?為什么要關(guān)注景觀?畫面感是增加細節(jié)的真實感,有些重要的細節(jié)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事物的本質(zhì)。與此相反的情形是,現(xiàn)在很多地理研究幾乎喪失了畫面感,甚至在人文地理論述中也是如此,通篇是概念,拿出來的是一個由概念堆砌的抽象結(jié)構(gòu),而遠離地上的實景。對于地理學來說,以概念代替實景的考察研究,不應該是主要方向,會造成許多生動的細節(jié)被忽略,許多關(guān)聯(lián)事物本質(zhì)的細節(jié)被拋棄。例如,缺乏景觀尺度與色彩特點的北京胡同宅院考察,不可能認識胡同的親和質(zhì)感,以及在這一質(zhì)感中產(chǎn)生的社區(qū)特性。
特別要意識到的是,把西方的抽象詞匯用在中國的事情上,要謹慎,否則很容易掩蓋重要的實情。即使是現(xiàn)代科學地圖,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現(xiàn)代地圖上都是由抽象的點、線、圈做標識,展開一幅世界地圖,除了南極洲外,其他六大洲都是 “世界大同 ”的符號群。要真正了解一個地方、一個區(qū)域,除了地圖,一定要加上景觀,地理學家必須要有對景觀圖片的解讀能力。地理景觀,或者地表樣貌,永遠是地理學的基本議題,是不能放棄的研究對象。為尋求高度一致性的科學目標,排除了大量個性資料,進而排除了大量個性事實,在人文研究中是大成問題的。現(xiàn)代地圖其實就是這類科學技術(shù)目標的樣本。在這一點上,現(xiàn)代科學地圖并不比一些古老文明的景觀地圖 “準確 ”。
城鎮(zhèn)也是景觀,“華夏大地的人造景觀中很少有比圍墻環(huán)繞的城市更界限分明,更令人驚嘆的景色 ”。這是段義孚,以及許多西方人初次來華時面對傳統(tǒng)景觀時的感受。段義孚對于中國古代城鄉(xiāng)的消長提出這樣的看法: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城鎮(zhèn)的發(fā)展是歷史的領(lǐng)先角色,是新時期的代表,而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會滯后。所以在周代初年,“商代遺留的村莊同
周朝圍墻環(huán)繞的城鎮(zhèn)比鄰而居 ”。這是歷史正面發(fā)展的情況。而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地區(qū),會出現(xiàn) “負面 ”的狀況。“在大分裂時期,蠻族占據(jù)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向南方遷徙,依賴重疊墻門進行監(jiān)督的嚴格控制體系分崩離析。小的鄉(xiāng)和亭衰落了,村莊卻增加了。”
關(guān)于中國近現(xiàn)代景觀的變化,占了全書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謂年頭不長,篇幅不短,說明段義孚對這一時期很是重視。在講述近代景觀變化之前,他首先對中國進行了分區(qū)景觀描述,分別是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四川盆地、長江平原、西南與嶺南。這實際上是對傳統(tǒng)時代各地景觀發(fā)展結(jié)果的一個總結(jié),也是近現(xiàn)代變化起步的基礎。我們可以讀出二十世紀初年各個區(qū)域的 “樣貌 ”,這是很有意思的部分。
段義孚主要從經(jīng)濟發(fā)展角度敘述近現(xiàn)代景觀變化。近現(xiàn)代中國變化巨大,且經(jīng)歷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因而變化方式是不一樣的。關(guān)于這一方面,段義孚以一九五 ○年為分界,進行了這樣的概括:在一九五 ○年以后的二十年間,“中國所發(fā)生的變化更為獨具一格,因為農(nóng)村的變化同城市一樣劇烈。變化的過程不是通過幾個點和線,順應經(jīng)濟規(guī)律緩慢滲透,而是遵循理論的革命性改變;一種本質(zhì)上的意識形態(tài)性力量可以將其影響迅速推及整個國家的社會機制 ”。當然,面對 “大躍進 ”時期的一些做法,他也提出了質(zhì)疑。
段義孚本人少年時期便離開了中國,他在本書中的講述,主要是依賴他人的研究,但并不因此使書的內(nèi)容流于抽象籠統(tǒng)。可以看出,段義孚著意于從參考書中提取關(guān)于景觀的細節(jié)內(nèi)容,所以我們常常讀到這樣的描述:在黃土高原,“在較為潮濕的地區(qū),黃土遍布的小山被精心造成階梯式金字塔形的梯田。巖石坡地表層岌岌可危的小片 ‘黃土 也被建成臺階,平整成石墻環(huán)繞的平臺狀耕地 ”。在華北平原,“在夏天時鳥瞰大地,所見到的是繁復而且土地極其細碎的景觀。由于地里不同莊稼長勢各不相同,每個農(nóng)民的栽種時間并不完全一致,田野變成一塊光怪陸離的調(diào)色板,布滿黃色、褐色、深淺不一的綠色,但是同畫家的調(diào)色板不同,顏色變化極其突兀 ”。讀到這樣的描述,仿佛與作者一起身臨其境。
追求身臨其境式的觀察、研究、敘事,是地理學家的基本責任。即使不能身體力行,也要力爭在閱讀中捕捉有意義的景觀細節(jié)。在對一些問題(特別是單純要素)進行分析和展示時,可以適當?shù)亟柚剑罱K卻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 “情景 ”。即使做當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將現(xiàn)代性簡化為公式。這其實是缺乏對現(xiàn)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現(xiàn)代性同樣對應特定的景觀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證,他的人本主義地理思想,就是在貼近情景的感悟中產(chǎn)生出來的。眾所周知,段義孚的這一思想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影響,而成為當代地理學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
(《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美 ]段義孚著,趙世玲譯,周尚意校,北京大學出版社二 ○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