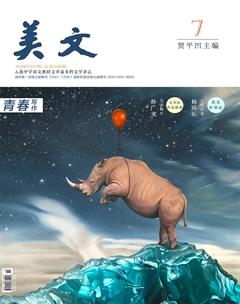甘地墓沉思

云使
這是一座黑色大理石墓地。
墓地簡樸、肅穆。一塊長方形大理石墓體,一盞長明燈,就是它的全部。
黑色墓臺上纖塵不染,明亮鑒人。印度人精心守護著它,猶如守護自己珍貴的心臟。一串串美麗的鮮花敬放上面,在次大陸驕陽的映照下,顯得分外絢麗燦爛。
71年了,前來瞻仰的人流依然不斷。他們扶老攜幼,赤足虔敬地在沙地、草坪上走過,佇立墓前,靜靜地合十祈禱。沒有喧嘩,沒有嬉鬧,連孩子的臉上都是靜穆。從喃喃的語言、面部特征和衣著上,可以看出他們來自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不同教派,雖然信仰不同,但他們都走到一起來了,因為這里埋葬著一位圣人,他的理想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間友愛相處如兄弟。他的理想,也是他們的理想。
人流中有許多外國游客,他們同樣赤足輕行,同樣肅穆禮拜,因為這里安息的不僅是印度人民偉大的兒子,也是全人類的兒子。在戰(zhàn)爭不斷、暴力彌漫的歲月里,他堅韌不拔地追尋著人類最寶貴的信念,他要向全世界證明,在這個星球上,還存在著比武力更強大的力量,比生命更崇高的東西,那就是真理和愛。
黑色墓體正面,鐫刻著兩個金色銘文:“噢,羅摩!”
71年前,圣雄甘地念誦著它,倒在了血泊中。
1948年1月30日下午5時,當白布素裹、赤足木屐的甘地走向晚禱會場,微笑著向熱愛他的民眾致意時,一位挺身向前、雙手合十的青年卻掏出了罪惡的手槍,連發(fā)三槍,刺殺了這位可敬的老人。
“噢,羅摩!”這是甘地留在世間的最后一句話。羅摩是印度教大神,可以把它解釋為:“噢,神啊!”
可是,誰又能明白這最后的嘆息中所包含的一切?
5個月前,歷經數(shù)百年蹂躪的印度剛剛宣布獨立。1947年8月15日零時,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尼赫魯滿懷豪情地莊嚴宣布:“在這午夜鐘聲敲響之時,在這全世界都還在睡夢中時,印度,將在獲得生命和自由中醒來!”當?shù)谝幻娉取住⒕G三色國旗在德里上空升起,整個印度都為之沸騰時,甘地卻正獨自前往教派沖突激烈的孟加拉邦。
在這舉國狂歡之日,這位“印度獨立之父”卻滿懷悲愴!
他無法接受印度分裂的事實。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的印度,為自己的同胞贏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主人的權利和尊嚴,那是他一生的企望啊!為了這個理想,他褪下了洋服,放棄了南非年薪10萬英鎊的律師職業(yè),捐贈出全部家產,返回印度。從此,白布裹腰,策杖赤足,如古代的苦行僧般走遍他飽受苦難的祖國。他先后18次絕食,無數(shù)次入獄,然而,當獨立曙光初現(xiàn)時,迎來的竟是印度因歷史和宗教原因而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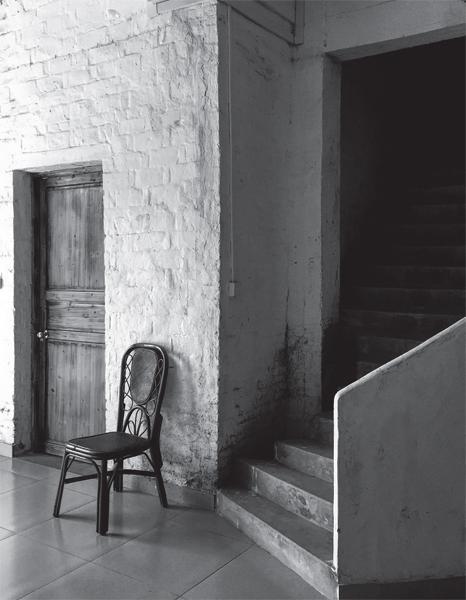
也許無人知曉這是怎樣一種痛苦,但人們知道,平生憎惡暴力至極的甘地,甚至懇求最后一任英國總督蒙巴頓勛爵說:“請您拒絕分裂印度,即使這一拒絕招致一場血流成河的戰(zhàn)爭。”極度絕望之下,他甚至說,“您可以把整個印度送給穆斯林,但千萬不能割裂她。”最后,自知回天無力的甘地深含痛苦地嘆道:對印度的分裂,是一次冷酷的“活體解剖”。有誰知道,對于甘地這樣的“古典英雄”,祖國的分裂就如同是他自己的肉身在經歷一場錐心斷骨、痛徹肺腑的撕裂!
而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宗教之間的相互仇視、相互憎恨,大規(guī)模的暴力沖突和流血事件連綿不斷。當人們在德里紅堡為獨立而歡慶時,78歲高齡的甘地正在加爾各答的一處陋室中絕食,老人企圖在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以他一生都在踐行的非暴力主義的道德力量,來平息愈演愈烈的宗教沖突。
奇跡出現(xiàn)了!當旁遮普邦5萬多軍隊都無法遏制騷亂的浪潮時,單槍匹馬、獨身一人的甘地,卻在孟加拉邦阻止了仇殺。他的對手——英國總督蒙巴頓——也不得不感嘆:“未來數(shù)百年間,印度乃至全世界再也不會出現(xiàn)像他這樣出類拔萃的人物。”
甘地貌不驚人,干瘦、矮小,似乎是他那貧窮而苦難祖國的一個注腳。可是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讓見過它的人難以忘懷。那里面有智慧、勇氣、意志和力量,有雄健的靈魂和山一般的堅韌。就是這樣一位瘦弱的人,曾迫使南非白人當局不得不頒布《印度人慰藉法》,給予印度僑民以應有的權利與尊重;就是這樣一位堅持自紡紗線、自制土衣來抵制英國洋布的人,訪問英格蘭棉紡城蘭開夏時,因此而失業(yè)的棉紡工人卻為他的勇氣和真誠歡呼喝彩;就是這樣一位“穿著半露腳爪的鞋子”的人,一路風塵地走進了英國總督府,走進了白金漢宮。
他的取勝法寶是什么?人說“沙堤格拉赫”就是他的傳世至寶,就是他征服世界的強大武器。“沙堤格拉赫”,意即“真理的力量”,是他非暴力主義的源泉。它并非弱者的武器,在它面前,一向自恃強大的殖民帝國也感受到一股逼人的力量,被迫坐在了談判桌前。半個多世紀后,他們?yōu)樗谟鴩业淖钪行奈恢谩獋惗氐膰鴷V場,豎起一尊青銅雕像。
然而,終生倡導非暴力的人,卻倒在了暴力的槍口下;為民族獨立奮斗了一生的人,卻在獨立到來之際離去……
甘地的葬禮在神圣的朱木拿河邊舉行,百萬民眾迎候他的靈柩。熊熊燃燒的大火持續(xù)了十四個小時,之后,就一直燃燒在這黑色大理石墓地的長明燈中。
71年了,長明燈中的火從未熄滅。
71年了,甘地也從未離開過印度。
他的肖像隨處可見,他的名字頻繁出現(xiàn),他的語錄常被引用,他的傳奇故事也已轉化成新的神話,甚至他的土織白衣都成為政客們的最愛,成為無私奉獻和服務的標記;他的手搖紡車被賦魅,成為思想修煉的瑜伽,成為修行與凈化的象征。是的,甘地無處不在。他活在深沉愛戴他的民眾心里,也活在政治家們將其抽空后的象征符號中;他活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偉大運動中,也活在新生印度走向現(xiàn)代化的艱難步履中,活在關于其現(xiàn)代意義的持續(xù)激辯中:
在走向共和的今天,傳統(tǒng)村社主義的“羅摩之治”,還能夠召喚回來嗎?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用紡車去戰(zhàn)勝機器的故事,還能重演嗎?
在互聯(lián)網信息時代的印度,仍以“古代情感、懷舊記憶”將貧困轉化為田園牧歌式的美好,還有可能嗎?
時移世易,甘地還在,而他親切稱呼為“婆羅多母親”的祖國已經改變,“黑水”之外的世界已經改變。
是的,甘地屬于一個特定的時代,不可復制,不可重現(xiàn)。然而,他對祖國和人民深沉的愛,對和平與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偉大人格、不朽精神和驚人的道德力量,就如同眼前的這盞長明燈,永遠不會熄滅。
“噢,羅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