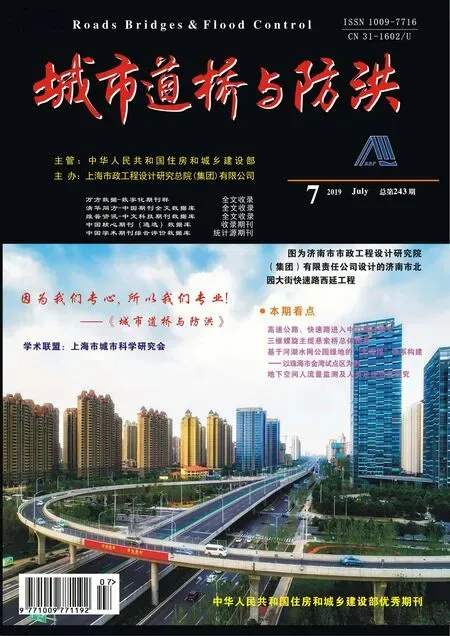斜拉橋鉆石型主塔承臺(tái)受力分析研究
宋煒
(上海市政工程設(shè)計(jì)研究總院(集團(tuán))有限公司,上海市 200092)
0 引言
典型的斜拉橋主要由主梁、拉索、主塔及基礎(chǔ)四部分組成。主塔作為斜拉橋的主要承重構(gòu)件,承擔(dān)著將作用于主梁及其自身的各類荷載作用傳至基礎(chǔ)的功能;同時(shí)主塔也是最能表達(dá)斜拉橋個(gè)性和視覺(jué)效果的結(jié)構(gòu)物,因此,城市中的斜拉橋需要更多地從造型、景觀及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等建筑藝術(shù)方面的要求來(lái)確定主塔的結(jié)構(gòu)型式。
斜拉橋主塔常見(jiàn)的結(jié)構(gòu)型式有獨(dú)柱型、A型、倒Y型、門型、H型、鉆石或花瓶型等各種型式[1],如圖1所示。其中鉆石型主塔造型優(yōu)美,穩(wěn)定感強(qiáng),該塔型主要特點(diǎn)是橫向剛度大,在橫向荷載作用下索塔受力性能良好,同時(shí)下塔柱傾斜向內(nèi)靠攏,大大減小承臺(tái)及基礎(chǔ)尺寸,因此在橋面寬度有一定要求的大跨徑斜拉橋中應(yīng)用較為廣泛。但由于兩側(cè)下塔柱內(nèi)傾固結(jié)于整體式承臺(tái)上,承臺(tái)橫向受力較大,且與傳統(tǒng)承臺(tái)有所不同。本文針對(duì)鉆石型主塔承臺(tái)構(gòu)造特點(diǎn),分別采用桿系模型及三維實(shí)體有限元分析方法對(duì)其受力情況進(jìn)行分析研究。

圖1 斜拉橋主塔的各種結(jié)構(gòu)型式
1 工程概況
新井岡山大橋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主城區(qū),是吉安市二環(huán)線的重要越江通道。跨贛江主橋采用(150+150)m獨(dú)塔雙索面結(jié)合梁斜拉橋,橋?qū)?8.0m,主塔采用弧形鉆石型橋塔,總高約125.0m,其中下塔柱高度為19.9m,塔柱中心線內(nèi)傾斜度為2.8∶1,采用變截面單箱單室箱形截面,如圖2所示,為保證塔底反力均勻傳遞到主塔承臺(tái)上,塔底設(shè)置2m厚塔座。

圖2 新井岡山大橋斜拉橋主橋
主塔基礎(chǔ)位于贛江河道深水區(qū),承臺(tái)順橋向?yàn)?7.0 m,橫橋向約為52.5 m,厚為5.0 m,兩端設(shè)圓端尖角,以減少對(duì)水流的影響,如圖3所示。基礎(chǔ)采用22根直徑2.5m鉆孔灌注樁,梅花形布置,樁基持力層為中風(fēng)化含礫泥質(zhì)砂巖,按嵌巖樁設(shè)計(jì)。
根據(jù)《公路鋼筋混凝土及預(yù)應(yīng)力混凝土橋涵設(shè)計(jì)規(guī)范》(JTG 3362—2018)[2](以下簡(jiǎn)稱橋涵規(guī)范)及參考文獻(xiàn)[3],目前承臺(tái)設(shè)計(jì)主要可概括為兩類:一類是將承臺(tái)作為受彎構(gòu)件,按“梁式體系”進(jìn)行抗彎、抗剪承載力計(jì)算;另一類是按“撐桿-系桿體系”的拉壓桿模型進(jìn)行分析。橋涵規(guī)范中對(duì)這兩類設(shè)計(jì)方法的適用條件進(jìn)行了規(guī)定,顯然,主塔承臺(tái)順橋向受力符合“撐桿-系桿體系”計(jì)算模式,而橫橋向受力較為復(fù)雜,上述計(jì)算模式是否適用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本文僅對(duì)承臺(tái)橫橋向受力展開(kāi)分析。

圖3 主塔承臺(tái)基礎(chǔ)結(jié)構(gòu)布置圖(單位:cm)
2 分析模型及荷載
2.1 分析模型
采用三維結(jié)構(gòu)分析軟件M ID A S C i v i l進(jìn)行分析,首先將主塔承臺(tái)按“梁式體系”簡(jiǎn)化為桿系模型,承臺(tái)采用等效至截面中心處的梁?jiǎn)卧M,主塔下塔柱保留一定長(zhǎng)度并延伸至承臺(tái)與其剛接,承臺(tái)底樁基礎(chǔ)取10m處固結(jié),并根據(jù)樁基實(shí)際長(zhǎng)度對(duì)其軸向剛度進(jìn)行修正[4],承臺(tái)簡(jiǎn)化的桿系模型如圖4所示。

圖4 主塔承臺(tái)簡(jiǎn)化桿系模型
同時(shí),為了對(duì)承臺(tái)進(jìn)行更為精細(xì)化地分析,并與桿系模型相比較,建立承臺(tái)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如圖5所示。

圖5 主塔承臺(tái)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
根據(jù)圣維南原理,實(shí)體模型中承臺(tái)頂保留一定長(zhǎng)度的下塔柱,荷載通過(guò)剛臂等效分?jǐn)偸┘佑陧敹巳珨嗝妗痘A(chǔ)同樣采用梁?jiǎn)卧⑷堕L(zhǎng)10m位置嵌固,樁頂節(jié)點(diǎn)與承臺(tái)底接觸區(qū)域內(nèi)節(jié)點(diǎn)通過(guò)剛臂約束,以保證不同單元變形耦合。
2.2 輸入荷載
將主橋總體計(jì)算得到的主塔下塔柱相應(yīng)位置處單元內(nèi)力作為輸入荷載,反向作用于上述承臺(tái)模型的塔柱頂端,這里僅取成橋階段作用標(biāo)準(zhǔn)組合下的塔柱內(nèi)力進(jìn)行分析,其中標(biāo)準(zhǔn)組合包括恒載、活載、溫度效應(yīng)、風(fēng)荷載及基礎(chǔ)不均勻沉降等作用。
此外,塔柱單元內(nèi)力需由其單元局部坐標(biāo)系轉(zhuǎn)換至整體坐標(biāo)系,模型輸入荷載值見(jiàn)表1。

表1 主塔承臺(tái)模型輸入荷載
3 結(jié)果分析及研究
3.1 承臺(tái)桿系模型與實(shí)體模型計(jì)算對(duì)比
根據(jù)橋涵規(guī)范,該工程鉆石型主塔承臺(tái)部分樁基離塔柱邊緣距離大于承臺(tái)厚度,可作為受彎構(gòu)件按“梁式體系”進(jìn)行受力分析。對(duì)此,首先通過(guò)兩種模型對(duì)承臺(tái)內(nèi)力分布進(jìn)行對(duì)比。
顯然,承臺(tái)簡(jiǎn)化桿系模型很容易得到承臺(tái)內(nèi)力圖,而對(duì)于實(shí)體模型,需將不同位置截面所切的所有實(shí)體單元應(yīng)力進(jìn)行積分,方可得到相應(yīng)截面的等效內(nèi)力。這里主要關(guān)心承臺(tái)順橋向彎矩My,如圖6和圖7所示,分別對(duì)承臺(tái)跨中位置及與塔柱軸線相交處截面所有單元應(yīng)力進(jìn)行積分,得到相應(yīng)等效截面彎矩My(這里X軸、Y軸分別為水平橫橋向及順橋向,Z軸為豎向)。

圖6 承臺(tái)塔柱軸線相交處截面實(shí)體模型切面應(yīng)力積分(單位:kN·m)

圖7 承臺(tái)塔中位置實(shí)體模型切面應(yīng)力積分(單位:kN·m)
以此進(jìn)一步計(jì)算,承臺(tái)對(duì)應(yīng)兩種分析模型不同位置處順橋向彎矩分布如圖8所示。
可以看到,兩種模型計(jì)算結(jié)果差異較大,其中承臺(tái)中部及與塔柱固結(jié)區(qū)段,桿系模型所得彎矩普遍比實(shí)體模型計(jì)算值大(絕對(duì)數(shù)值),而在承臺(tái)塔柱固結(jié)點(diǎn)附近,桿系模型由于無(wú)法考慮固結(jié)區(qū)域內(nèi)力擴(kuò)散等影響,其值遠(yuǎn)遠(yuǎn)高于實(shí)體計(jì)算結(jié)果。

圖8 主塔承臺(tái)兩種模型順橋向彎矩分布對(duì)比(單位:kN·m)
選擇承臺(tái)部分關(guān)鍵斷面,如圖9所示,分別對(duì)其桿系模型及實(shí)體模型的順橋向彎矩計(jì)算結(jié)果進(jìn)行比較,見(jiàn)表2,由于桿系模型難以考慮塔柱截面范圍內(nèi)彎矩折減,其結(jié)果不具有可比性,故這里僅取塔柱底外邊緣所對(duì)應(yīng)的承臺(tái)截面。

圖9 承臺(tái)對(duì)比分析部分截面位置

表2 主塔承臺(tái)兩種模型順橋向彎矩計(jì)算對(duì)比
由以上對(duì)比可以看出,相較于實(shí)體有限元分析,采用桿系模型梁?jiǎn)卧椒ㄟM(jìn)行的承臺(tái)受力計(jì)算雖然趨勢(shì)大致相同,但結(jié)果偏于保守,特別是塔柱與承臺(tái)固結(jié)區(qū)域,所得結(jié)果與實(shí)際受力相差很大。對(duì)于此類承臺(tái),桿系模型分析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為了更準(zhǔn)確地反映其空間力學(xué)效應(yīng)往往需要建立更精細(xì)化的三維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
3.2 承臺(tái)塔座影響分析
為保證主塔塔柱內(nèi)力均勻傳遞至承臺(tái),往往在塔底承臺(tái)頂設(shè)置一定厚度的塔座,該工程塔底亦設(shè)有2m厚塔座。
為了對(duì)承臺(tái)受力計(jì)算時(shí)塔座的影響進(jìn)行研究,在上述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基礎(chǔ)上,建立一不含塔座的承臺(tái)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如圖10所示,其余包括邊界及荷載模擬等則完全相同。

圖10 主塔承臺(tái)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無(wú)塔座)
對(duì)此,標(biāo)準(zhǔn)組合作用下,有無(wú)塔座的兩種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其等效順橋向彎矩分布對(duì)比如圖11所示。

圖11 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有無(wú)塔座順橋向彎矩對(duì)比(單位:kN·m)
很明顯,除塔座局部范圍外,兩模型計(jì)算結(jié)果較為接近;而塔座區(qū)段內(nèi),不考慮塔座影響時(shí),承臺(tái)彎矩出現(xiàn)峰值,有塔座模型此區(qū)段彎矩分布則較為均勻。這說(shuō)明經(jīng)過(guò)塔座的過(guò)渡及擴(kuò)散,承臺(tái)與塔柱固結(jié)區(qū)域的彎矩出現(xiàn)明顯削減。
同樣,對(duì)于前面定義的4個(gè)關(guān)鍵截面,不含塔座的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順橋向彎矩值與前述桿系模型及(含塔座)實(shí)體模型計(jì)算結(jié)果對(duì)比見(jiàn)表3。

表3 主塔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塔座影響對(duì)比
可以看到,若不考慮塔座影響,標(biāo)準(zhǔn)組合作用下承臺(tái)跨中截面順橋向彎矩增大約18%,塔座范圍更是相差超過(guò)30%,承臺(tái)部分區(qū)段受力有與桿系模型類似的趨勢(shì),這表明塔座對(duì)于傳遞擴(kuò)散塔底內(nèi)力、改善承臺(tái)受力的作用較為明顯。
3.3 承臺(tái)應(yīng)力結(jié)果
進(jìn)一步,對(duì)有無(wú)塔座兩種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的順橋向正應(yīng)力及主拉應(yīng)力進(jìn)行對(duì)比如圖12~圖15所示。

圖12 主塔承臺(tái)橫橋向正應(yīng)力對(duì)比(承臺(tái)實(shí)體有塔座)(單位:MPa)

圖13 主塔承臺(tái)橫橋向正應(yīng)力對(duì)比(承臺(tái)實(shí)體無(wú)塔座)(單位:MPa)

圖14 主塔承臺(tái)橫橋向主拉應(yīng)力對(duì)比(承臺(tái)實(shí)體有塔座)(單位:MPa)

圖15 主塔承臺(tái)橫橋向主拉應(yīng)力對(duì)比(承臺(tái)實(shí)體無(wú)塔座)(單位:MPa)
由于鉆石型主塔下塔柱內(nèi)傾,下塔柱軸力傳遞至承臺(tái)使其中間區(qū)段受壓,同時(shí)下塔柱內(nèi)力使承臺(tái)產(chǎn)生順橋向彎矩My(前面已對(duì)此進(jìn)行分析),兩者相疊加后,承臺(tái)中間區(qū)段表現(xiàn)為上緣受拉,下緣受壓,但最大應(yīng)力均在2MPa以內(nèi)。
塔柱作用范圍內(nèi)的承臺(tái)頂部均受壓,所不同的是,考慮塔座影響時(shí),頂部最大壓應(yīng)力為4.1MPa,主要分布于塔座內(nèi)側(cè)邊緣,而不考慮塔座時(shí)最大壓應(yīng)力約為5.1 MPa,分布在塔臂與承臺(tái)接觸區(qū)域;與塔柱固結(jié)段承臺(tái)底部局部受拉,對(duì)應(yīng)有無(wú)塔座的最大拉應(yīng)力分別為3.1MPa、4.6 MPa,主拉應(yīng)力最大值亦集中在此范圍內(nèi)。
3.4 不同模型的樁基反力對(duì)比
標(biāo)準(zhǔn)組合作用下,分別對(duì)承臺(tái)桿系模型及有無(wú)塔座的實(shí)體模型的樁基反力分布情況進(jìn)行分析,如圖16所示。
由于承臺(tái)受力對(duì)稱,僅選取不同模型下相同四分之一承臺(tái)對(duì)應(yīng)的7根樁基反力進(jìn)行對(duì)比,其樁基編號(hào)布置及反力值見(jiàn)表4。

圖16 不同模型樁基反力分布情況(單位:kN)

表4 不同模型樁基反力計(jì)算值對(duì)比
可以看到,不同模型的最大豎向反力樁基位置相同,均位于中間排第2列,即均為⑥號(hào)樁,所不同的是其反力數(shù)值,其中桿系模型最大,而考慮塔座影響的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最小。此外,有塔座的承臺(tái)實(shí)體模型其樁基反力分布最均勻,而桿系模型變化最大。
這表明桿系模型難以考慮承臺(tái)空間受力分布效應(yīng),同時(shí)在一定程度上,塔座的設(shè)置使承臺(tái)荷載傳遞及樁基反力分配更為均勻。
4 結(jié)語(yǔ)
以吉安市新井岡山大橋工程為背景,對(duì)其主橋主塔承臺(tái)分別建立梁?jiǎn)卧獥U系模型及三維實(shí)體有限元模型,對(duì)鉆石型主塔傾斜式塔柱傳力下的承臺(tái)受力情況及樁基反力分配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分析探討,研究表明此類內(nèi)傾塔柱下的整體式承臺(tái)受力按桿系模型進(jìn)行計(jì)算偏于保守,且有一定局限性,往往需要借助于更精細(xì)化的實(shí)體有限元分析;同時(shí),承臺(tái)頂所設(shè)塔座對(duì)擴(kuò)散塔柱內(nèi)力、改善承臺(tái)受力效果較為明顯,也一定程度上使樁基反力分配更為均勻。研究結(jié)果可對(duì)此類承臺(tái)的分析計(jì)算及配筋設(shè)計(jì)提供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