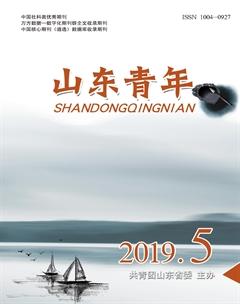東漢中期東漢與鮮卑之和戰關系及其原因探析
孫宸 宋佳
摘 要:鮮卑在內附于東漢之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至東漢中期成為足以與東漢政權抗衡的一股勢力。其與東漢時戰時和,一方面是因為東漢政權在當時動蕩不安,政權內部矛盾較為復雜,國力有所下降,致使對邊境控制力下降,同時邊疆政策也出現失誤;一方面是因為東漢在解決匈奴問題時,鮮卑趁隙發展,使得其自身實力增加,另外民族利益的驅動也是其與東漢政府之間戰和不定的原因。
關鍵詞:東漢;鮮卑;和戰關系;原因
鮮卑本東胡種,東漢初年,因勢力較弱,曾依附于匈奴隨其寇邊。建武二十一年,鮮卑又一次隨匈奴入侵遼東,被遼東太守祭彤擊破,“斬獲殆盡”。[1]根據《后漢書》的記載可知,鮮卑的勢力經過打擊,變得更弱。而東漢王朝則處于國力相對強盛之時,鮮卑審時度勢,采取蟄伏的策略,表面上歸附東漢政權,而實際上是在積蓄其力量。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于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2]鮮卑內附之后,協助東漢政權平定其它民族政權的入侵。同時,東漢政府每年給予其二億七千萬錢的賞賜。因此,東漢一方面依靠強大的武力震懾,一方面巨額的經濟拉攏使得明、章二世邊境無事,而鮮卑同時也據此獲得較快發展。
一、 東漢中期東漢與鮮卑的和戰關系
最初鮮卑與漢總體上保持了和平的臣屬關系,但是這種情況在和帝永元年間發生了變化,“(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3]東漢對匈奴的作戰使得北匈奴遠遁,塞北地空,東漢政府經過權衡,①未同意南匈奴北遷,而鮮卑趁勢占據北匈奴故地,同時因匈奴十一萬眾的歸附,使得鮮卑勢力大增,其名義上雖仍然臣屬于東漢的,但一些小規模的犯邊戰爭不時發生。據《后漢書·鮮卑傳》,隨著鮮卑勢力的不斷增強,從和帝永元九年(97年)至沖帝時,其與東漢之間發生了18次規模不等的戰爭,而由鮮卑發起的戰爭共15次。除去史書中所載的這些戰爭,在雙方之間必然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的、未記入史冊的軍事沖突。這些是鮮卑在勢力逐漸變強的過程中一次次試探性軍事行動。而東漢發起的主動進攻共3次。而鮮卑在與東漢之間存在較多軍事沖突的同時,其首領燕荔陽、烏倫、其至鞬也曾于安帝永初年間及永寧元年先后入朝。
二、東漢與鮮卑和戰的原因
(一)東漢方面
縱觀東漢與鮮卑之間的戰爭,可以發現東漢基本上是呈防御狀態。有學者曾對漢安帝時期的對外戰爭進行研究,發現“大多是外族政權主動進攻東漢帝國,安帝時期東漢王朝甚少主動攻擊邊疆民族,僅有的主動出擊也是對入侵者的反擊,屬于防御性質的戰爭。”[4]造成此現象的原因,首先是東漢國力下降,對鮮卑只能采取防御為主的策略。東漢中期,政府面臨的情況相當棘手。朝中宦官及外戚干政等現象屢見不鮮,國家綱紀廢弛,官員的個人政治素養及水平良莠不齊,百姓身上所負擔的賦役繁重,邊境地區的反叛屢見不鮮。如永初四年,涼州爆發羌人叛
亂;[5]元鼎五年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6]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因賦斂繁數,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叛亂。[7]另據《后漢書·皇后紀》載“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8]此段史料中的“水旱十載”指的是鄧太后臨朝之后發生的“水旱。”據筆者統計,《后漢書》中和帝至順帝的五十多年中,關于蝗災的記載有20次、旱災24次、水患22次。②另據王文濤先生統計,“漢安帝在位的20個年頭不僅無年不災,而且一年數災。共發生自然災害86次。”[9]其中除水、旱、蝗災之外,還有地震、風災、雹災、寒凍災、疫災等,由此可以發現,不斷出現的天災可能會導致百姓流離失所,使得以農業立國的東漢王朝的財政收入受損,進而影響到其國力,相應的邊防力量也會有所減弱。頻繁的平叛戰爭就產生了數額巨大的軍費開支,③極大地消耗了國家的經濟實力,天災加上人禍,東漢在多數情況下無力主動發起對外戰爭,這就使鮮卑得以趁虛而入,不斷向東漢邊郡進軍。
其次,東漢政權雖已經認識到鮮卑勢力會發展壯大,對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手段,但顯然其對鮮卑的認識仍舊不足,邊疆政策出現一定的失誤。據《后漢書》:“匈奴熾于隆漢,西羌猛于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騎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兇桀,公據遼西之土。”[10]從中可以看出,在東漢中期,東漢王朝并未將鮮卑視為首要對手,而是認為邊疆的首要問題為西羌。東漢一代,大規模的羌族起義就有五次之多,而小規模的起義則此起彼伏,接連不斷。[11]而東漢中期的羌族十年叛亂使得東漢王朝將防范的重點放在了西部羌族,而鮮卑則自然下降到次要位置。因此東漢政府在此段時間內對鮮卑采取的是以安撫為主、防御為輔、偶見軍事威懾的政策。
(二)鮮卑方面
鮮卑對東漢的軍事行動或入朝內附,主要是基于其自身實力的發展和利益選擇。
鮮卑在東漢前期自知其力量較弱而蟄伏,“其后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12]之后的燕茘陽、烏倫、其至鞬等也曾先后內附,鮮卑因內附東漢從而得到發展,其勢力的快速發展也得益于東漢對北匈奴的征戰,一方面跟隨東漢出兵匈奴而獲得巨額賞賜,“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永平元年……于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13]一方面依靠東漢打壓北匈奴而使自己得以取而代之:“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14]北匈奴逃遁在客觀上給鮮卑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鮮卑則抓住這一時機壯大自己的力量。
鮮卑首領的變化也影響了其與東漢之間的關系。鮮卑“常推募勇健能理決斗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部落自為一部。”[15]鮮卑的首領大人為眾人推舉,一般為驍勇善戰、有識見者為之。在其首領燕茘陽封王后,鮮卑與東漢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和平,這可能是因為燕茘陽本人是一個守成型的部族首領,其更傾向于與東漢保持一種和平的狀態。所以幾年后出現的擾邊的也不是燕茘陽,而是連休。而永寧元年(120年)之后鮮卑的首領其至鞬對東漢多次發起的軍事行動。其至鞬在永寧元年被封為率眾侯,而后可能其至鞬部落實力發展壯大,漸有統領鮮卑各部的趨勢,成為鮮卑領袖。從歷次漢鮮戰爭中可以看出其至鞬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其至鞬死后,由于鮮卑缺少強有力的部落領袖,各部之間無法形成統一的軍事行動,于是“鮮卑抄盜差稀”。后桓、靈年間,在檀石槐的領導之下,鮮卑的抄掠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