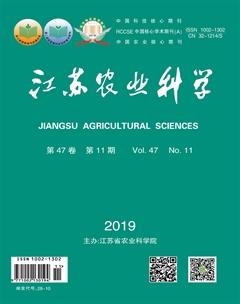基于主體視角的陜西省農村環境治理模式分析
汪紅梅
摘要:治理主體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發揮著根本性作用。陜西省在全國農村環境治理中樹立起陜西樣板,從治理主體角度歸納總結陜西省農村環境治理模式對于提升環境治理效果,以及為其他省份提供借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基于對陜西省5個縣(市、區)10個鄉(鎮)20個村莊的田野調查,總結出4種治理模式:政府包辦型、政府購買型、機構扶助型和農戶自治型。從供給-需求和成本-效益等2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結果表明,除了政府包辦型和“無為而治”的農戶自治模式之外,其他幾種模式在需求瞄準性方面均有良好表現;政府包辦型成本高、效益低;政府購買型和“有為而治”的農戶自治模式成本低、效益高;機構幫扶型成本低、效益不確定;“無為而治”的農戶自治模式成本低、效益低。提出優化農村環境治理的建議:針對不同治理內容和環節采取不同模式,協同采用多種模式。
關鍵詞:農村環境治理;治理主體;治理模式;供給-需求;成本-效益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9)11-0046-04
近年來,陜西省以農村環境連片整治為突破口,以生態創建為助推器,牢固樹立城鄉環境一體化治理的新思路,全面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和環境質量改善,在全國農村環境治理和美麗鄉村建設中樹立起陜西樣板。陜西省環保廳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全省累計投入財政資金31.39億元,其中中央資金16.22億元,省級配套8.21億元。在全省90個縣(市、區)、997個鄉鎮(街辦)、5 210個建制村(社區)實施農村環境綜合整治示范工程,共建成1 185處生活污水處理設施、2 431處飲用水源保護工程、231處垃圾中轉及處置設施、1 821處畜禽養殖污染防治設施,配備23 600輛生活垃圾收集車,受益人口近880萬。目前,全省已建成3個國家級生態縣(市、區)25個生態鎮11個生態村、28個省級生態縣(市、區)373個生態鄉鎮369個生態村。涌現出一批行之有效的技術和管理治理模式,如鳳縣采取了多級凈化人工濕地為主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方案;西鄉縣積極推廣“豬沼茶”“豬沼菜”“豬沼糧”等循環種養模式;扶風縣探索建立起了符合農村實際的“五有”長效機制等。
然而,隨著農村經濟社會改革不斷深入,工業化、城鎮化以及農業開發等都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諸多直接或潛在的負面影響[1],且這一影響還可能持續加劇。環境改善非一勞永逸,污染治理須持之以恒。為鞏固農村環境治理成果,防止污染“卷土重來”,須要探索出農村環境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洪大用等首先提出,從城鄉二元性角度探究治理困境形成的原因[2]。范和生等指出,城鄉生態共同體意識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3]。洪大用認為,治理失靈更為根本的原因是內生性和結構性問題,即治理主體不完整[4]。因而,從治理主體角度對農村環境治理模式進行歸納總結,對于穩固和提升陜西農村環境的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文獻將環境治理主體劃分為政府、市場、自主治理3種。然而鮮有學者對這些主體在農村環境治理中的具體實踐及其效果進行研究,對陜西省農村環境治理模式的研究更不多見。2017年9月和2018年1—2月,筆者與其課題組成員深入陜南、關中和陜北等5個縣(市、區)10個鄉(鎮)20個村莊,對縣(市、區)、鄉(鎮)和村干部進行深入訪談,總結出陜西省農村環境治理的4種典型模式,并利用供給-需求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對各種模式加以對比研究,從而得出優化農村環境治理模式的建議。
1 陜西農村環境治理模式
1.1 政府包辦型
政府包辦型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是指,政府提供環衛基礎設施,環境宣傳和教育等一切環境治理方面的服務,農戶完全不參與環境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日常維護。筆者以陜北Z村為例對該模式進行分析。Z行政村屬于黃土溝壑區,位于縣城溝口。全村共有331戶962人,貧困戶有129戶345人,屬于貧困縣里的貧困村。該村總土地面積為548.33 hm2,其中退耕還林面積為204.87 hm2,蘋果面積為186.67 hm2全村以果樹種植為主導產業,以大棚、養殖和外出務工為輔助產業。因為經濟不發達,青壯年外出務工比例較高,該村環境治理缺資金缺人的現象比較突出。
1.1.1 環衛基礎設施提供 Z村從多方爭取各種項目經費,完善基礎設施。解決了全村飲水問題,自來水入戶率達到90%以上。維修了黨員活動室,新修產業路15 km,硬化了村內道路3段4.5 km。村委會投入8萬元,為6戶貧困戶建設香豬圈舍,并投放36頭豬仔。利用機械清理河道堆積垃圾及轄區內國道道路兩旁雜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安排了保潔員,并分劃各自區域。雇傭工人和重型機械對公園河畔和上山路兩側溝渠的垃圾進行集中處理,投放4個垃圾箱;對影響市容市貌的汽車修理、廢品收購等經營場所進行了限期搬遷,共整頓16戶;栽植景觀樹8 000余棵,房前屋后種植牽牛花等本土花卉。
1.1.2 環境教育和宣傳 Z村制訂了《Z村衛生環境整治方案》,并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活動,通過張貼標語、發放宣傳單、倡議書、《村規民約》等方式,向廣大村民宣傳新農村建設的目的和意義。組織黨員同志對群眾進行倡議,如不焚燒垃圾、冬季使用環保型煤等。開展“四好教育”,加強輿論引導,使村民真正感受到創衛與他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由包村領導和第一書記帶隊,逐戶指導、督促村民自發對房前屋后、門庭院落進行整頓清理,發放1 000余個垃圾袋。由村支部牽頭,實行村“三委會”成員和黨員中心戶包戶制度,負責對村民的日常衛生習慣進行教育、引導、督促,并在每月10日的黨日活動上評比,獎優罰劣。
1.2 政府購買型
政府購買型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是指,政府給環衛公司付費,由公司負責提供轄區的日常環衛服務。筆者以陜南H村為例對該模式進行分析。H村屬于丘陵區,位于鎮東南部,距鎮政府4 km。全村總面積為32 km2,轄8個村民小組,共288戶902人,其中勞動力共440人,貧困戶有130戶347人。貧困發生率約為45%,屬于貧困縣中的貧困村。
1.2.1 環衛基礎設施提供 2016年由群眾自發投工投勞修建村組級公路路基工程5 km。爭取省級項目資金并利用“一村一策一戶一法”整村推進項目,修建通村水泥路10.8 km。包村單位出資修好了盤山路,改變了山頂村民下山1次要耗費5 h的狀況。目前,全村已經全部通組路,自來水普及率達到50%,恢復1條農田灌溉堰渠,對全村房屋進行“三清三改三化”,已完成改建60戶。縣級政府給每村每年150萬元貸款用于開展“農村環境入戶整治”項目。全村每戶均配備1個垃圾桶,每組配備2名保潔員或生態護林員,保潔員負責組里道路衛生,生態護林員負責林木安全以及河道和村里的環境衛生。
1.2.2 環境教育和宣傳 村委會組織農戶開展環境衛生整治工作,落實門前“四自一包”責任制及衛生監督員,利用發宣傳冊和辦黑板報對村民進行健康教育。村里還開辦“農民夜校”,每月評出“紅黑榜”,對當月涌現出來的環境先進分子進行表揚,對落后分子進行批評,并將先進分子和落后分子的照片和事跡張貼在村委會門口的宣傳欄中。
1.2.3 環境日常維護 H村所在鄉(鎮)于2014年成立了鄉(鎮)環衛公司,該公司是自收自支的民營企業。鄉(鎮)政府每年給公司撥款10萬元,公司負責集鎮及周邊村的水電、綠化等環境公共設施維護和垃圾清運等環境服務工作。公司每個月2次到村里垃圾集中點收集垃圾轉運到縣城垃圾處理場。如果因特殊情況垃圾增多,也可自行聯系環衛公司,運輸1趟垃圾村里須付費350元,鄉(鎮)政府每年給村里3 000元垃圾處理補貼款。
1.3 機構幫扶型
機構幫扶型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是指,農村環衛設施主要由第一書記、包村干部、幫扶單位、包聯單位等機構提供的模式。筆者以關中S村為例對該模式進行分析,S村屬于山區,離鄉(鎮)政府10 km。全村共350戶,總人口為1 423人,人均年收入6 000多元,貧困戶有55戶,其中42戶已經脫貧,2017年剛退出貧困村行列。該村主要農作物為蘋果和葡萄,其中秦冠蘋果多次獲得省級大獎,目前該村蘋果總量的80%出口尼泊爾。
1.3.1 環衛基礎設施提供 S村的幫扶單位為市交通局,該單位出資修好了村里主干道,并對主干道兩旁農舍墻面進行了美化,還為每戶修建了歐式花園圍欄,極大改觀了該村的村容村貌。由于陜西省規定滿足7條標準才能退出貧困村,交通局在“水、電、路、網、訊、醫療、就學”等方面都提供了相應的服務,實現了整村“硬化、亮化、美化、綠化”。在實施這些工程時,幫扶單位自己請工程隊來施工,村民采取自愿原則投勞參與。村里采用“記工”的方式記錄村民的參與情況,但務工是否有報酬、有多少報酬還不確定。該村聘請了5個保潔員,每月工資300元,由村集體土地承包費支付保潔員的工資。該村每人每年交10元衛生費,用于村環境治理支出。
1.3.2 環境教育和宣傳 S村近年才用上自來水,之前一直飲用集雨窖水。集雨窖水來源于天然雨水,不僅不衛生,口感也不好,村民對于能用上自來水非常滿意。由于“精準扶貧”前后村莊環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村民無須環境教育和宣傳都深刻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環境保護意識自覺提高了。此外,因為該村主要農產品為水果,采用親環境行為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價格更高,這一事實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有效的環境教育,村民們在生產中自覺采用水溶肥、農家肥,杜絕使用農藥。
1.4 農戶自治型
農戶自治型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是指,環衛基礎設施主要由農戶自己提供,農戶自發處理生活垃圾和生產垃圾。這種模式涉及2類農戶,一類是環衛設施難以覆蓋的居住偏遠的農戶,另一類是環境意識比較強、經濟基礎比較好的農戶。筆者分別以陜南Q村和關中D村為例進行分析。Q村地處秦巴山區,位于鎮西北部,距鎮政府3.5 km,全村共129戶374人。耕地面積為36.93 hm2,其中水田面積為15.33 hm2,2017年人均純收入9 000多元。村經濟收入以外出務工為主,袋料食用菌等產業為輔。近年來,全村的青壯年勞動力80%在外務工,主要從事建筑業、煤礦業和服務業。D村地處關中平原,位于鎮西南部,距鎮政府2 km,轄3個自然村,9個村民小組,共627戶2 287人,總面積為473.6 hm2,耕地面積為 440 hm2,主要產業以苗木花卉種植為主,人均收入達到 1萬元。
1.4.1 環衛基礎設施提供 Q村農戶居住分散,最小的組只有10戶人家。村民出行主要靠盤山公路,夏天山洪暴發沖毀道路,冬天道路結冰長達數月,使得交通非常不便。盡管精準扶貧中有易地搬遷政策,然而老人們安土重遷情結嚴重,另外還有一部分人擔心在異地失去生計,因此還是選擇居住在原址。該村主干道路面已經硬化,然而道路很難修到這部分偏遠農戶家門口。因為交通不便,垃圾收集車也無法顧及這部分區域。他們距離村里集中收集垃圾的垃圾臺很遠,垃圾不能集中收集,只能自行處理。他們一般采取焚燒生活垃圾、秸稈、農藥瓶、農膜等方式處理垃圾。盡管這樣處理的垃圾量比較少,環境也有一定的承載能力,但是這種處理模式存在的火災等安全隱患還是不容忽視的。另外,這部分村民的環境滿意度較低,相對不滿情緒比較高,干群關系較為緊張。
D村農戶居住比較集中,外出務工村民較少,特色產業發展不錯,經濟條件比較好。鎮村干部發展思路明確,早早確立了該村“農業觀光村”的定位,并著手整村環境整治工作。首先從每家每戶門口入手,借鑒城市商戶的“門前三包”,要求農戶管好自家門口的“三堆”:柴草堆、糞土堆、建材堆。然后在政府專項經費支持下,村民再自籌一部分資金,將村里原來的垃圾場變成了廣場,并在廣場上栽植花木,建起了文化長廊和村食堂,為開展觀光旅游奠定了基礎。村干部和村民一致認為,環境治理是村民的事情,即使沒有外部經費支持,農村環境治理也是要開展的。
1.4.2 環境教育和宣傳 Q村通過宣傳車、宣傳單、宣講會、夜校等方式進行環境保護教育和宣傳,甚至通過積分在村里的“愛心超市”換取小商品的方式提升大家的環境意識,激勵大家的環保行為。然而這些居住偏遠農戶參與的積極性不高。
D村干部認為,農村環境治理的命脈在于提升農戶的環境意識;農村經濟社會要發展,環境美化要先行。這些樸素的認識決定了該村環境治理的基本思路,他們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線工作法”:村“三委會”成員帶領本村所有幫扶干部,集體走訪入戶,了解戶中情況,聽取群眾意見,解決群眾困難,做到“情況在一線掌握、問題在一線解決、政策在一線落實、正氣在一線傳遞、感情在一線融洽、形象在一線樹立”。通過這種務實做法,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在環境治理等工作中意見高度一致,村民積極參與,各項工作開展都很順利。為讓村民意識到環境治理人人有責,該村每人每年收取1元象征性衛生費。為激勵村民積極美化環境,對于環境治理表現突出的家庭,每年獎勵15元象征性榮譽。環境治理表現也是該村“十星級農戶”評選標準中很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
2 農村環境治理模式比較分析
以上4種農村環境治理模式的出現都是當地特定自然、經濟和文化條件下的產物。政府包辦模式一般出現在經濟基礎比較落后、鄉(鎮)村干部工作思路比較保守、農戶配合程度比較低的村莊;政府購買模式一般出現在非農經濟比較發達、鄉(鎮)村干部工作思路比較先進、鄉(鎮)村干部工作任務比較重、農戶配合程度比較低的村莊;機構幫扶模式一般出現在經濟發展程度比較低、環境基礎設施存量比較少、鄉(鎮)村干部工作思路比較保守、幫扶單位比較有實力、農戶配合程度比較高的村莊;農戶自治模式一般出現在2種比較極端的條件下:一種是無為而治,即普適性政策惠及不到的地方,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模式;另一種是有為而治,農戶有意愿、有能力成為環境治理的主力軍,能夠按照發展目標積極采取適合自己的治理模式。只要因為自然的、歷史的原因存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農戶的村莊,“無為而治”的自治模式就可能產生。而“有為而治”的自治模式一般出現在經濟比較發達、鄉(鎮)村干部工作思路比較先進、農戶配合程度較高的村莊。然而存在不一定合理,筆者試圖從供給-需求和成本-效益2個視角對這4種模式進行比較分析。
2.1 基于供給-需求視角的分析
供給只有與需求對接,才是有效的供給。在農村環境治理中,農戶的環境目標訴求不同,對環衛設施的需求就不同,最好的環境服務應該是提供農戶需要的環衛設施。
在政府包辦模式中,農戶無須參與,也就沒有表達需求的渠道,因此提供的環衛設施難免“貨不對板”,農戶要么不愿意使用,要么對設施的維護漠不關心。政府為Z村每家每戶都建了1個沖水式廁所,然而在修建過程中就遭到很多農戶的反對,原因主要有2點:一是該村經常停水,沖水式廁所經常無法使用;二是農家肥是果樹肥料的主要來源,這種廁所使他們不方便取肥。筆者調研時發現,廁所建好已經大半年了,然而沒有1家農戶使用過這種廁所。該村主干道安裝了竹籬笆,為村莊增添了濃厚的田園氣息,然而問到竹籬笆的維護時,村民都表示“不關我們的事”。
在政府購買模式中,政府付費,公司為農戶提供環衛服務。公司和農戶之間是市場行為,公司對市場需求是敏感的,也能及時對需求的變化作出反應,因此是能夠瞄準農戶需求的。H村垃圾桶和垃圾臺上均印著環衛公司電話,一旦發現垃圾滿了,就可以聯系環衛公司來人清理,很方便。環衛公司也很樂意來清理,因為每次清理都可以獲得收入。
在機構幫扶模式中,幫聯個人長期住在農村,跟村民一起生活,了解村里的實際環境需求,因此提供的環境服務也是能瞄準需求的。S村最迫切的環境需求就是自來水和道路,幫扶單位在1年內提供了這種產品,農戶滿意度非常高。在通水和修路時,村民自發出工清路障、平地基。建設中占用的農地無須補償,損毀的苗木10年以下的無須補償,10年以上的僅要求20元/棵的極低補償。
在農戶自治模式中,“無為而治”情形下,農戶的需求難以被考慮,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也沒有什么環衛服務的供給,遑論供給的瞄準性。在“有為而治”情形下,農戶嚴格按照村莊發展規劃,自籌資金或者利用專項資金主動供給環衛服務,精準瞄準需求,效率高、效果好。D村農戶環境意識很強,村民不僅搞好自家門前的環境,還監督、幫助其他村民搞好環境。有1戶人家長期不在村內居住,他的鄰居主動出錢出力維護這家院子里的環境,目的是不影響整個村子的環境面貌。
從以上分析可知,除了政府包辦型治理模式和“無為而治”型農戶自治模式之外,其他幾種模式在需求瞄準性方面都表現不錯。在環境教育和宣傳方面,各種模式下采取的方式大同小異,農戶也比較能接受這些方式,因此在本研究中不特別作比較分析。
2.2 基于成本-效益視角的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作為一種經濟決策方法,將成本費用分析法運用于政府部門的計劃決策之中,以尋求在投資決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常用于評估需要量化社會效益的公共事業項目的價值。環境治理作為一項公共事業,對其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是有必要的。環境治理的成本體現在環境設施提供成本和環境日常維護成本等2個方面;效益體現在環境質量的價值,包括短期的環境質量和長期的環境質量。因為調研中各村環境設施種類和建設時間不同,無法對其成本進行統一核算,以下分析假定各種模式下環境設施提供成本都是相同的,因此只須對環境日常維護成本進行比較。
在政府包辦模式中,環境日常維護成本較高,因為農戶沒有參與環衛設施的提供,對他們認同感不強,甚至有排斥心理,難以發自內心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去精心管護它們,從而延緩他們的折舊。同時,因為農戶只是被動接受這些設施和現有的環境質量水平,他們缺乏創造性地改善環境質量的動力。長期環境質量只有靠政府不斷包辦才能得以延續,因此長期環境質量效益很難評估。
在政府購買模式中,環境日常維護成本比較低,因為環衛公司有嚴格的成本核算,會控制成本。只要公司有利可圖,長期環境質量也應該是有保障的。一旦農戶對環衛公司提供的服務滿意,形成了為環境服務付費的意識,他們是有支付意愿的。H村所在鎮擬在2年內對農戶征收衛生費,用于補貼公司運營。因此公司的可持續經營是可以預期的,長期環境治理效益也是可以獲得的。
在機構幫扶模式中,環境日常維護成本較低。因為幫扶單位提供的環衛設施是村民亟需的,在設施建設中他們自己還出力了,因此他們對設施有很強烈的認同感,使用中對設施很珍惜。然而,設施的折舊是不可避免的,幫扶單位的支持是暫時的,長期環境質量效益很難預估。
在農戶自治模式中,“無為而治”情形下,環境日常維護成本較低,因為無論是焚燒還是填埋都幾乎沒有成本。但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環境效益,都難以盡如人意。“有為而治”情形下,環境日常維護成本較低,因為環衛設施是農戶發展規劃實施的基礎,他們出資出力提供的,自然會倍加愛護。同時,因為有發展規劃書,村莊具有內生發展能力,設施的更新就有了保障,因而長期環境效益是可以預期的。
從以上分析可知,政府包辦模式成本高、效益低;政府購買和“有為而治”型農戶自治模式成本低、效益高;機構幫扶模式成本低、效益不確定;“無為而治”型農戶自治模式成本低、效益低。
3 提升農村環境治理效果的建議
3.1 有針對性地采取不同模式
應針對不同內容采取不同模式,如環境治理項目和服務宜采取政府購買模式,環境日常維護宜采取農戶自治模式。此外,還應針對不同環節采取不同模式。“環境治理,觀念先行”。首先進行環境保護教育和宣傳,提升農戶環境保護意識和環保行為能力,如學會垃圾分類以及垃圾減量化的方法,從源頭上降低垃圾收集和處理的成本。然后選擇合適的環境治理模式,提高環境治理效率。最后制定簡明嚴格的制度,使環境治理機制常態化,效果長效化。
3.2 協同采用多種模式
環境治理是一項綜合性工作,各主體都能發揮作用,也都應該發揮作用,但各主體發揮作用的領域應該有所側重[5-6]。政府應該主要在環境基礎設施提供方面發力,如道路、垃圾臺、垃圾桶的提供等;環衛公司主要負責環境日常維護,如垃圾轉運和處理等;村民應提高環境意識,自覺減少垃圾,集中垃圾等。只有各主體協同作用,農村環境治理才能取得成功,從而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魏 晉,李 娟,冉瑞平,等. 中國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研究綜述[J]. 生態環境學報,2010,19(9):2253-2259.
[2]洪大用,馬芳馨. 二元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中國農村面源污染的社會學分析[J]. 社會學研究,2004(4):1-7.
[3]范和生,唐惠敏. 農村環境治理結構的變遷與城鄉生態共同體的構建[J]. 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37(4):149-155.
[4]洪大用. 試論改進中國環境治理的新方向[J]. 湖南社會科學,2008(3):79-82.
[5]毛陽南. 新媒體背景下的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途徑[J]. 江蘇農業科學,2018,46(5):255-257.
[6]萬合鋒,武玉祥,秦華軍,等. 浮萍科植物水環境修復及其資源化利用綜述[J]. 江蘇農業科學,2018,46(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