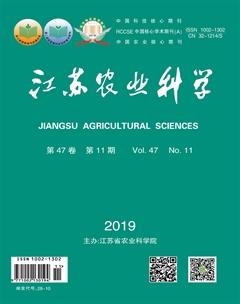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分異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張玉 任建蘭 谷縉



摘要:基于對綠色發展水平內涵的理解,構建四級指標體系,運用熵權TOPSIS法、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趨勢面分析及障礙度模型,分析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各層級和綜合水平的空間分異特征及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北京、山東、浙江、上海、廣東等5省(市)無論是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3個層級,還是在綜合評價方面處在高水平區,甘肅省處在低水平區;中國各省域綠色發展水平整體上空間差異明顯,聚合趨勢較顯著,冷熱點空間格局與其等級水平的空間格局基本吻合;空間指向性明顯,東西向呈“東高西低”的拋物線型分布,南北向呈“中間高、兩端低”的倒“U”形分布,出現較明顯的空間分異現象。針對不同地區制約因素提出不同的發展路徑,以期為提升區域綠色發展水平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綠色發展;生態文明;空間分異;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F129.9?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9)11-0339-08
收稿日期:2018-01-30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41571525);山東省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編號:16AWTJ05)。
作者簡介:張 玉(1993—),男,山東菏澤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E-mail:1142166974@qq.com。
通信作者:任建蘭,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人地系統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E-mail:renjianlan@sina.com。? 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日益凸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成為發展問題,中國提出可持續發展理念,平衡推進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三大領域的發展[1]。綠色發展是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實踐,是可持續發展的升級版。“綠色發展”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于2002年提出,強調綠色增長、綠色財富和綠色福利于一體的新型發展道路。生態文明是協同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生態環境保護所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進步的總和,是工業化后的社會文明形態。而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在工業化中期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超前提出的,重點是“建設”[2]。綠色發展不完全等同于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是全面的發展,不以犧牲生態環境、惡化人地關系為代價,而生態文明是發展的上層建筑,是一場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復興與進化的社會運動,綠色發展是實現生態文明發展階段的必然選擇。2016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印發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綠色發展愈發受到重視。近幾年,學者們對綠色發展的研究逐漸增加,主要集中在綠色發展理論探討[3-6]、綠色發展效率[7-9]、綠色發展水平測度[10-13]、綠色發展福利[14-15]以及綠色發展路徑選擇[16-19]。目前有關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眾多,參考依據也不同,評價結果有所差異,李琳等從產業綠色增長度、資源環境承載力、政府政策支撐力3個方面構建指標,評價中國區域產業綠色發展指數[20];鄭紅霞等圍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發展綜合指數、綠色發展測度體系等梳理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評價指標,并提出指標構建面臨的嚴峻挑戰[21]。從研究方法上看,層次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普遍被應用,基于GIS空間分析、DEA模型的研究逐漸增加,郭永杰等利用GIS空間分析對寧夏回族自治區縣域綠色發展區域差異進行研究[22];謝里等通過DEA模型探究中國31個省(市、區)農村綠色發展及內部差異[23]。本研究結合十八大以來國家部委發布的相關文件和“十三五”規劃的指標要求,從人地關系的視角構建中國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探討中國各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現狀,并對其制約因素進行診斷,針對不同地區提出不同的發展路徑,為提升區域綠色發展水平提供參考與借鑒。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以中國30個省域為研究單元,除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西藏自治區外,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6》《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6》《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6》《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6》等,部分缺失數據根據各省(市、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各省(市、區)統計年鑒進行補充。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權TOPSIS法 熵權TOPSIS法是熵值法和TOPSIS法的結合[24]。熵值法是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數值,能有效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具有較高的可信度[25]。TOPSIS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主要是通過評價對象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進行優劣度的評價,以此給評價對象進行排序,使評價結果具有客觀性、科學性[26]。依據相關參考文獻內容,具體過程如下。
(1)構造原始矩陣{vij}m×n。本研究中m=30,表示30個評價對象;n=38,表示38個評價指標。采用極差法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得到標準化矩陣{rij}m×n。
(2)利用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計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貼近度時分別取w1中相對應權重,計算綠色發展水平綜合指數時權重取w2。
(3)為提高中國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的客觀性,運用熵權wi構建權重規范化矩陣Y。
1.2.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廣泛運用到各種研究問題的空間格局分析上,能夠有效揭示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采用Morans I、Getis-Ord General G和 Getis-Ord Gi*測度空間關聯的結構模式,反映其全局、局部空間關聯特征以及熱點(hot spots)與冷點(cold spots)的空間分布。
式中:Xk、Xj表示區域屬性值;X表示均值;S2表示樣本方差;Wkj表示空間權重矩陣。Morans I值介于-1~1之間,當值小于0時,表示空間負相關,存在低值與高值集聚現象;當值等于0時,表示不存在空間自相關;當值大于0時,表示空間正相關,存在低低集聚或高高集聚現象。采用Z值對Morans I進行統計檢驗。
1.2.3 趨勢面分析 其中,Ti(xi,yi)為趨勢函數,表示大范圍的趨勢值。εi為自相關隨機誤差,表示第i趨勢面是實際曲面的近似值,能夠模擬不同地理要素在空間上的分布規律和變化趨勢。本研究運用趨勢面分析中國各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總體空間分異趨勢。假設Zi(xi,yi)為區域i的綠色發展綜合水平,(xi,yi)為平面空間坐標,根據趨勢面定義可知Zi(xi,yi)=Ti(xi,yi)+εi。
各區域的綠色發展水平的真實值與趨勢值之間存在的偏差,本研究采用二階多項式測算綠色發展水平的趨勢值,趨勢函數可表示為Ti(xi,yi)=β0+β1x+β2y+β3x2+β4y2+β5xy。
1.3 指標選取
合理的指標選取對區域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結果的客觀性、科學性具有關鍵作用。不管從廣義上看還是從狹義上看,有關綠色發展水平的評價還不統一,評價標準存在差異,學者們普遍從經濟、社會、生態3個子系統進行評價。本研究在參考十八大以來有關綠色發展的文件,尤其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國家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循環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考核指標等,構建新的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指標體系的總體設計全面詮釋了我國綠色發展的內涵。綠色發展水平評價主要包括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國土空間4個方面,經濟發展是動力,社會進步是目標,生態環境保護是發展的基礎,國土空間開發是基于綜合3個子系統的發展在空間上的協調。在閱讀大量文獻的基礎上,發現有關研究對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的空間分異具有一致性,本研究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列為1個層級。綠色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共涵蓋3個層級,包括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由于研究選取指標過多,二級指標權重參考《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報告》及相關文獻確定權重,其他層級指標通過熵權法計算得到,W1為各系統層級指標權重,W2為綜合評價指標權重。經濟發展是綠色發展的動力和條件,社會進步關乎到綠色發展的目的所在,關系到人們生活福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主要反映綠色發展水平的可持續性、穩定性與目的性;生態環境保護能力是提升綠色發展水平的基礎,資源節約有效利用是提升綠色發展水平的重要途徑,生態系統的穩定、平衡發展有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提升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是實現綠色發展的第一任務,目的是實現空間均衡發展,空間均衡就是主體功能區中生活空間、生產空間、生態空間的整治,反映發展過程中過度開發、無序開發等占用大量生態空間、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城鄉發展空間協調性問題(表1)。
2 結果與分析
2.1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布局
運用各評價指標數據及權重,利用TOPSIS模型計算出經濟社會發展貼近度、生態環境保護貼近度、國土空間開發貼近度、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貼近度。運用標準差分級法將各個貼近度進行水平等級分類,研究共分為高水平區、較高水平區、較低水平區、低水平區4類。V表示平均值;B表示標準差(表2)。為更加直觀地反映各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和綠色發展綜合水平,運用ArcGIS 10.2軟件進行空間統計分析,并繪制專題地圖(圖1)。
2.1.1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層級系統評價 通過TOPSIS模型計算出各層級貼近度,并運用標準差分級法將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進行等級分類,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3個層級分別進行分析。(1)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層級中,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呈“T”字形分布,高水平區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較高水平區沿長江經濟帶分布,甘肅省、云南省、貴州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處在低水平區。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的貼近度A1分別為0.625 7、0.682 5、0.609 9、0.595 3,遠高于其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處在最理想狀態。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東部沿海各地區憑借優越的區位條件,引領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沿江各省份依靠天然航道,強化與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聯系,經濟社會發展處于較高水平。低水平區的甘肅省、貴州省、云南省的貼近度分別為0.240 2、0.275 6、0.270 7,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還存在較大差距。甘肅、云南、貴州等省處于“老少邊山”地區,區位條件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2015年三省的貧困人口發生率分別為15.33%、14.12%、10.37%,脫貧任務還很嚴重,應不斷加強財政轉移支付、強化對口幫扶力度,提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2)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層級中,北京市、山東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等6省(市)的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屬于最高水平區,有11個省(市、區)(天津市、河北省、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重慶市、河南省、安徽省、江蘇省、湖南省、江西省、海南省)處于較高水平區。整體來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國土空間開發貼近度差異小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層級,其中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江西省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層級處在較低水平區,但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層級處在較高水平區,說明這些區域在現有發展條件下,從長遠考慮更關注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甘肅省、青海省生態環境脆弱、氣候條件惡劣,加上濫砍亂伐、過度開采,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生態環境保護能力較弱;黑龍江省長期依賴石油、煤炭等自然資源的高消耗,發展方式粗放,人地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威脅著區域生態系統的穩定,這些區域屬于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層級中低水平區。(3)國土空間開發治理層級的分類結果顯示,北京市、山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等6省(市)屬于高水平區,國土空間開發強度大,治理能力強,區域內雄厚的經濟實力推動城鄉基礎設施投資建設,農村生活條件逐步改善。受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加上自身優越的區位條件,河北省、江西省、福建省、海南省處在較高水平區,中西部地區只有重慶市的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狀況較理想。13個省(區)(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遼寧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陜西省、山西省、四川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國土空間開發治理處在較低水平,且集中分布在中國中部、西北和東北地區,一方面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主體功能區規劃有關。黑龍江省、甘肅省、貴州省、云南省的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狀況不理想,其中黑龍江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好于其他3個省份,但對于城鎮綠色發展和農村生活條件改善關注度還不夠,應加大政府財政投資力度,改善城鄉居民生活,進而實現空間均衡發展。
2.1.2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價 從綠色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結果看,整體上貼近度表現為東部>中部>東北、西部地區。高水平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其綜合貼近度(T)分別為0.624 8、0.590 4、0.556 8、0.586 5、0.640 1、0.627 4、0.582 4,遠高于其他地區,綠色發展水平最理想。北京市、山東省、浙江省、上海市、廣東省等5省(市)無論是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3個層級,還是在綜合評價方面都處在高水平區,其貼近度也遠高于其他地區。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重慶市、福建省的綠色發展水平較理想,有14個省(區)(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遼寧省、河北省、陜西省、山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安徽省、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的綠色發展水平屬于較低水平區,西北和東北地區分布較集中,中部地區的安徽省、江西省處在較低水平,其周圍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狀況都較理想。低水平區包括黑龍江省、甘肅省、貴州省、云南省,其綜合貼近度(T)分別為0.303 2、0.288 3、0.317 3、0.319 1。甘肅省氣候條件惡劣、生態系統脆弱、區位優勢不顯著,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和綜合評價中都處于低水平區,說明其發展過程存在一定問題,經濟社會發展緩慢,貧困問題突出,亂砍濫伐、過度放牧現象突出,生態系統破壞嚴重;黑龍江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好,但在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治理方面狀況不理想,導致綜合評價結果處在低水平區,應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注重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提升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平衡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而促進空間協調發展。
2.2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空間關聯格局
2.2.1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通過Geoda軟件對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數據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發現Z值為4.674 7≥1.98,說明返回的統計結果是可信的,且空間分布是集聚的;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點為空間正相關的點數據,Morans I值為0.490 007,表現為空間正相關;P值為0.000 03≤0.01,說明Morans I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空間關聯特征為綜合評價數據高的區域趨于和綜合評價數據高的區域相鄰,數值低的區域趨于和數值低的相鄰。大部分區域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中,即通常的熱點和冷點區域,這兩象限的空間單元具有強烈的空間正相關,說明中國綠色發展水平整體上空間差異明顯,聚合趨勢較顯著。
2.2.2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運用ArcGIS軟件將中國綠色發展水平局部空間關聯指數Getis-Ord Gi*的結果將研究空間分為熱點、次熱點、次冷點、冷點等4個區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熱點數量為7個,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是綠色發展水平高的集聚區域;次熱點數量為5個,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次冷點數量為13個,多集中在黃河以北地區;冷點數量為5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區,區域內生態系統脆弱,資源環境承載力差,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整體來看,中國綠色發展水平的冷熱點空間格局與其等級水平的空間格局基本吻合(圖2、圖3)。
局部空間自相關指標LISA用于反映一個區域單元的某一屬性值與相鄰區域單元的某一屬性值的相關程度。利用Geoda軟件生成的LISA聚集圖,用不同顏色渲染不同的空間自相關類別。黑色表示高高集聚,表明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等長江三角洲地區屬于綠色發展水平高水平集聚區;深灰色表示低高集聚,圖中區域沒有出現高低集聚,表明安徽省的綠色發展水平低于周圍區域,沒有某一區域的綜合水平數據高于周圍區域;灰色表示低低集聚,表明中國西部地區屬于綠色發展水平低水平集聚區,而白色表示不顯著。中國地域遼闊、地形復雜、氣候多樣,區域間區位條件差異明顯,西部地區尤其是甘肅、云南、貴州等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生態系統脆弱、國土空間開發治理能力不足,是中國綠色發展水平低水平集聚區(圖4)。
2.3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趨勢面分析
運用地統計分析方法,對中國各省域綠色發展水平各層級系統和綜合評價進行空間趨勢面分析。結果(圖5)表明,中國的綠色發展水平空間格局整體表現為東西向呈“東高西低”的拋物線型分布,南北向呈“中間高、兩端低”的倒“U”形分布,表明東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出現較明顯的分異現象。具體來看,東西方向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由東向西逐漸遞減的趨勢,而在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綜合評價水平上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分異不明顯,但西部地區明顯低于中部和東部地區;南北方向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綜合評價水平地區分異明顯,中部地區明顯高于南部和北部地區,國土空間開發治理方面的趨勢面相對平緩,沒有出現強烈的地域分異。
3 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為了更加深入研究造成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差異的原因,剖析其發展制約因素,以便為未來區域綠色發展指明方向,提升區域綠色發展能力,建設美麗中國。本研究引入障礙因子模型進一步對綠色發展的制約因素進行診斷,具體方法為:
式中:Mij表示障礙度;Nij表示指標偏離度。Mij越大,表示該指標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制約程度越大。
由于指標選取的數量眾多,導致指標障礙度數值偏小,各地區排名前3位的指標累計障礙度均值在15%左右。不同地區的指標障礙度存在較大差異,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廣東省的指標障礙度數值相對較高,其中北京市的前3位指標障礙度累計為25.44%,因為北京市的部分指標數據在所有研究樣本中是最大的,而這些指標數據的最大值所對應的障礙度為0。低水平區的障礙度數值較低且相對平均,說明低水平區綠色發展水平制約因素偏多且主導作用不顯著,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較多(表3)。
不同等級水平區的障礙度因素存在差異,低水平區主要受C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35(農民人均純收入)、C36(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等因素制約;較低水平區范圍廣,制約因素復雜,尤其是第一障礙度區域間差異明顯,前3位障礙度C5(R&D經費占GDP比重)出現頻次最高,受其制約較大;對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的障礙度統計,C4(7次)、C30(6次)等指標數值較高,東部、中部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普遍存在技術市場交易額不足、自然保護區面積小的狀況。從要素層上看,主要受經濟效益、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空間均衡等要素制約,說明綠色發展水平提升過程中存在經濟發展結構不夠合理、效益低下,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力度不足,國土空間開發不協調等問題(表3)。
總體的障礙度統計(表3)顯示,制約各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指標因素有較大差異,影響不同地區障礙度前3位的指標因素共32項,其中出現頻次較高的依次為C4(18次)>C5(16次)>C30(10次)>C20(9次),C4(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比重)、C5(R&D經費占GDP比重)出現頻次較高說明我國發展結構不夠合理,對科研投入的力度有待加強,技術市場潛力須進一步挖掘;其次為C30(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占陸地國土面積的比例)、C20(濕地保護率),說明我國的生態環境較脆弱,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任務依然嚴峻。今后在發展過程中應始終貫徹綠色發展理念,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不斷開拓技術市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保持經濟社會穩步發展,提升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治理能力,從而提升中國綠色發展水平,建設美麗中國。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首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層級,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呈“T”字形分布在東部沿海和長江經濟帶,甘肅省、云南省、貴州省的發展狀況不理想;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江西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處在較低水平區,但生態環境保護能力處在較高水平區,說明這些地區在現有發展條件下更加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國土空間開發治理方面,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集中分布在東部沿海,中西部地區只有重慶市處在較高水平區,其他地區的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狀況不理想。其次,通過對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價發現,北京、山東、浙江、上海、廣東5省(市)無論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國土空間開發治理3個層級,還是在綜合評價方面都處在高水平區,其貼近度也遠高于其他地區,甘肅省都處在低水平區,發展狀況不理想,這與其區位條件有著密切的聯系。中部地區的安徽省、江西省處在較低水平,其周圍地區的綠色發展狀況都較理想,黑龍江、甘肅、貴州、云南等省的綜合評價結果處在低水平區。再次,中國綠色發展水平整體上空間差異明顯,聚合趨勢較顯著,冷熱點空間格局與其等級水平的空間格局基本吻合。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等長江三角洲地區屬于綠色發展水平高水平集聚區,安徽省的綠色發展水平低于周圍區域,中國西部地區屬于綠色發展水平低水平集聚區。地統計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綠色發展水平空間格局整體表現為東西向呈“東高西低”的拋物線型分布,南北向呈“中間高、兩端低”的倒“U”形分布,出現較明顯的空間分異現象。最后,中國省域綠色發展水平障礙度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各省域制約因素存在著一定差異,但C4(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比重)、C5(R&D經費占GDP比重)、C30(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占陸地國土面積的比例)、C20(濕地保護率)是出現頻次較高的4項指標因素,說明我國在綠色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技術市場狹小、科研投入不足、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重視不夠等問題。高水平區和較高水平區普遍存在技術市場交易額不足、自然保護區面積小的狀況;較低水平區范圍廣,制約因素復雜,低水平區的障礙因素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和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當中的美麗鄉村建設方面。
4.2 對策建議
受不同障礙度因素制約,中國的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差異顯著,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4.2.1 推動技術創新與智能創造,提高發展質量與效益 傳統的發展方式已不能夠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影響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會進步。應著力發展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推動科技創新,加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提升綠色生產效率。東部地區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做好產業升級、社會轉型的排頭兵,輻射帶動周邊地區快速發展;中西部地區創新發展環境,增加就業機會,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保障人們生活質量,尤其是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4.2.2 加大生態系統修復與環境保護力度,促進資源節約高效利用 國家部委相繼發布“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積極推進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強化水、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節約利用,全面推進節能減排和污染防治,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東北、西北、西南地區在森林、草原、濕地覆蓋率方面優于中東部地區,在發展過程中應提高資源利用率,杜絕亂砍濫伐、過度放牧,東部則要注重公園綠地建設面積,提高綠化覆蓋率,提升生態文明建設能力。
4.2.3 強化主體功能區定位,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 堅定不移地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空間規劃體系,根據主體功能定位推動“多規合一”,加強城鄉規劃“三區四線”管理,科學合理布局和整治生活空間、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積極推進綠色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黑龍江省、甘肅省、貴州省、云南省等國土空間開發治理狀況不理想的地區,應更加關注城鎮綠色發展和農村生活條件改善,加大城鄉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力度,大力推進綠色城鎮化和美麗鄉村建設,進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4.2.4 建立健全法律法規,構建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目前我國有關綠色發展意識不強、責任不清,制度建設是綠色發展的重點,靠制度倒逼強化發展。完善生態環境監管制度,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堅持“誰污染、誰治理”“誰受益、誰繳費”的原則。健全政績考核制度,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強化指標約束,不以GDP論英雄。實行差別化的考核制度,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和環境責任離任審計,完善責任追究制度。
參考文獻:
[1]任建蘭,張 偉,張曉青,等. 基于“尺度”的區域環境管理的幾點思考——以中觀尺度區域(省域)環境管理為例[J]. 地理科學,2013,33(6):668-675.
[2]任建蘭,常 軍,張曉青,等. 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資源環境綜合承載力研究[J]. 山東社會科學,2013(1):140-145.
[3]劉紀遠,鄧祥征,劉衛東,等. 中國西部綠色發展概念框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0):1-7.
[4]胡鞍鋼,周紹杰. 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24(1):14-20.
[5]蔣南平,向仁康. 中國經濟綠色發展的若干問題[J]. 當代經濟研究,2013(2):50-54.
[6]劉思華. 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綠色發展[J]. 當代經濟研究,2011(5):65-70.
[7]楊志江,文超祥. 中國綠色發展效率的評價與區域差異[J]. 經濟地理,2017,37(3):10-18.
[8]趙領娣,張 磊,徐 樂,等. 人力資本、產業結構調整與綠色發展效率的作用機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11):106-114.
[9]穆學英,劉 凱,任建蘭. 中國綠色生產效率區域差異及空間格局演變[J]. 地理科學進展,2017,36(8):1006-1014.
[10]張 歡,羅 暢,成金華,等. 湖北省綠色發展水平測度及其空間關系[J]. 經濟地理,2016,36(9):158-165.
[11]盧 風. 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和根本[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7(1):1-9.
[12]黃 躍,李 琳. 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綜合測度與時空演化[J]. 地理研究,2017,36(7):1309-1322.
[13]劉 冰,張 磊. 山東綠色發展水平評價及對策探析[J]. 經濟問題探索,2017(7):141-152.
[14]臧漫丹,諸大建,劉國平. 生態福利績效:概念、內涵及G20實證[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5):118-124.
[15]鐘水映,馮英杰. 中國省際間綠色發展福利測量與評價[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9):196-204.
[16]Kruk R,Thompson D,Liu J Y.The road map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3,11(3):244-252.
[17]Saul C.Torontos green development policies get a passing grade[J]. Daily Commercial News and Construction Record,2008,81(114):1-3.
[18]謝雄標,吳 越,嚴 良. 數字化背景下企業綠色發展路徑及政策建議[J]. 生態經濟,2015,31(11):88-91.
[19]王 珂,秦成遜. 西部地區實現綠色發展的路徑探析[J]. 經濟問題探索,2013(1):89-93.
[20]李 琳,楚紫穗. 我國區域產業綠色發展指數評價及動態比較[J]. 經濟問題探索,2015(1):68-75.
[21]鄭紅霞,王 毅,黃寶榮. 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綜述[J]. 工業技術經濟,2013(2):142-152.
[22]郭永杰,米文寶,趙 瑩. 寧夏縣域綠色發展水平空間分異及影響因素[J]. 經濟地理,2015,35(3):45-51,8.
[23]謝 里,王瑾瑾. 中國農村綠色發展績效的空間差異[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6):20-26.
[24]程 鈺,任建蘭,崔 昊,等. 基于熵權TOPSIS法和三維結構下的區域發展模式——以山東省為例[J]. 經濟地理,2012,32(6):27-31.
[25]何 偉,楊春紅. 基于Topsis的江蘇省中心城市可持續發展狀況評價[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68-72.
[26]韓瑞玲,佟連軍,宋亞楠. 基于生態效率的遼寧省循環經濟分析[J]. 生態學報,2011,31(16):4732-4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