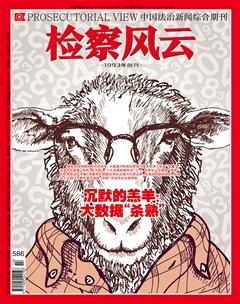你就站在布拉格黃昏的廣場上
林海
據說,一開始,布拉格人還會困惑地糾正來自中國的游客:這是“老城廣場”,而不是“布拉格廣場”。久了,也就漸漸接受了這個說法。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中國游客會來這里尋找“彩繪的玻璃窗裝飾著哥特式教堂”,另一方面,這座城市里曾有一位法學博士、工傷保險公司法務部職員,稱自己為中國人——他的名字叫作弗朗茨·卡夫卡。
少年卡夫卡閑逛過的大橋
和許多城市相似,布拉格依河建市。碧波粼粼的伏爾塔瓦河穿城而過,共有18座大橋橫架在河水之上。其中,歷史最悠久且仍在使用的,是距今已有650年歷史的查理大橋。卡夫卡就出生于這座大橋的橋墩邊一個猶太百貨商人的家庭。1934年5月,當他靜靜地躺在維也納郊外療養院時,留下的生命中最后一句話是:“我的生命和靈感全部來自偉大的查理大橋。”
當時陪伴在卡夫卡身邊的,是他的好友雅努斯。雅努斯在《卡夫卡對我說》中寫道:“我經常會為卡夫卡如此鐘情查理大橋而吃驚,他從3歲時便開始在橋上游蕩,他不但能說出大橋上所有雕像的典故,有好多次我甚至發現他竟在夜晚借著路燈的光亮在數著橋上的石子……”這座大橋修建于1357年,系遵照捷克國王查理四世之命而建。該橋使用波希米亞砂巖建造。有一個傳說,用來黏合石塊的灰漿中加入了雞蛋,使其更加堅固。
橋頭站立著的是查理四世皇帝的雕像。威嚴的查理四世頭戴皇冠,手握著名的《黃金詔書》。這部詔書從法律上規定了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由七大選帝侯推舉產生,擺脫了羅馬教宗對皇帝人選的干涉。雕像下方的基座面對四個方向各有一尊雕像,分別代表他于1348年創設的布拉格大學的四個學院:神學院、醫學院、哲學院和法學院。這所大學今天位于查理大橋以東,穿過一號線地鐵和布拉格天文鐘,走十分鐘左右就能到達。
據史書記載,查理四世中等身材,有點駝背,留著濃密的黑胡子,衣著樸素,卻嗜好讀西塞羅,并與彼得拉克交從甚密。他還資助了多位法學家,比如意大利人巴爾托魯、《論國王與皇帝的權力》的作者盧波爾德。查理四世以重金聘請著名學者前來任教。到他去世時,這所大學已有11萬學生。值得一提的是,1390年,一個名叫揚·胡斯的新生考入這所大學的文學專業。他出身農家,少年喪父,寡母認為教育是重中之重,便用盡全力供他上學。他亦不負母親期望,以優秀成績畢業后留校任教。1401年成為神學部主任,1409年升任為校長。
再無許愿墻的“布拉格廣場”
沿著布拉格大學向西走幾分鐘后向北一拐,就能在老城廣場的中央看到一座青銅雕像,那就是揚·胡斯。他對捷克有何深遠影響呢?原來,他是反對教會贖罪券制度、號召宗教改革的領袖人物,較馬丁·路德早了整整一百年。這些主張帶來了殺身之禍。在康斯坦茨大公會議上,他被宣布為異端。教會剝奪他教士職位后,緊接著將其移交世俗法庭,執行火刑。
胡斯死訊傳來,支持他的地方貴族及民眾開始激烈抗議教廷。最終教廷對整個波希米亞發布了“禁行圣事”的處罰禁令。1419年,以胡斯信徒為主的布拉格市議會更是被強制解散。胡斯信徒非常憤怒,7月30日,他們在神父揚·柴利夫斯基的率領下走上街頭示威游行,人潮聚集至老城廣場,要求釋放被逮捕的胡斯信徒。突然有人從市政廳的窗口向胡斯信徒丟擲石塊,局勢立刻被引爆。人們沖進去將市長及市議員共7人自窗戶扔向樓下,這就是著名的“拋窗事件”。
今天,老城廣場早已是市井熱鬧的平凡模樣。胡斯像下其實也沒有供人們“投下希望”的許愿池。2014年之前,人們倒是確實在胡斯像下的基座上貼上各種許愿紙條,形成了一座許愿墻;可是2014年市政廳對此進行整修,清除了墻上的紙條,并設置圍欄使人們不得近前。于是許愿墻也沒有了。人們大抵也不記得,胡斯臨死前在牢房里說的話:“你們燒死了一只天鵝(捷克語中‘胡斯的意思),但是一百年后,你們將會聽到一只天鵝的鳴唱,這是你們無法燒毀的,到那時你們將不得不聆聽它的歌聲。”一百年后,馬丁·路德認領了這段預言,這樣寫道:“揚·胡斯在波希米亞牢房中預言的那只天鵝就是我……是的,若上帝喜悅,這只天鵝將會持續不斷地歌唱下去。”這歌唱終于改變了世界——當然,胡斯對此已無知曉。
還算勝任工作的保險公司法務
老城廣場西北角有一棟尼古拉斯教堂。教堂隔壁的房子是許多人尋訪卡夫卡的起點。這棟房子建于1717—1730年間,本是尼古拉斯教堂神職人員的辦公室;1787年因國王下令改善猶太區環境而改為住宅。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就在這里出生。他在提交給布拉格保險總公司的求職簡歷中這樣寫道:“我……在老城人民小學讀到四年級,然后進入舊城德語國立中學;十八歲開始就讀于布拉格大學……通過了最后一次國家考試后,我于1906年4月1日進舊環城路理復德·略維博士的律師事務所當秘書。”
在這個律師事務所里,卡夫卡同略維律師達成協議,只在必要時才去事務所上班,以便充分利用時間。1907年10月1日,他完成了為期一年的實習,并拿到了法學博士學位,遂到一家意大利人開辦的保險公司找工作。在入職體檢中,醫生說他“體質纖弱,然而是健康的”。身材瘦長,身高一米八一。然而一年后,即1908年7月14日,他向公司出具了另一份醫生診斷:由于神經受損和“心臟極易興奮的特征”而必須辭職。人們推斷,對第二份醫生鑒定大可不必認真看待。其實,卡夫卡只是想以和平的方式從私人企業轉到工作輕松得多的勞工意外保險協會去。
總體上說,卡夫卡也算是勝任工作。據他自己所說:“我本來也根本不是堪稱楷模的職員,但在某些方面卻是很可一用的(我目前的頭銜是法律合同起草員)。”因為起草工傷事故保險方面的文書,時常要涉及許多法律條文和程序,這正是卡夫卡的專長。在14年保險公司職員的生涯中,他的生活在表面上似乎極為平淡無奇,既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也沒有大起大落的波瀾,大體上過著“上班——寫作——度假——上班”這樣一種固定不變的生活,然而,這14年間,他內心已經發展出無比豐富復雜和巨大廣闊的世界,并完成了幾乎所有的重要作品。
曾有七萬多猶太人在此停止呼吸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他閱讀過大量經過翻譯的中國典籍、詩歌、傳說故事。1912年,他給未婚妻寫信時,甚至引用了袁枚的《寒夜》:“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實際上,卡夫卡創作的第一篇小說《一次戰斗紀實》就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以后他又創作了以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往事一頁》《中國長城建造時》《一道圣旨》《中國人來訪》,等等。
余光中先生在《橋跨黃金城》中曾這樣說卡夫卡:“身為猶太種,他成為反猶太的對象。來自德語家庭,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敵視。父親是殷商,他又不見容于無產階級。另一層不快則由于厭恨自己的職業:他在‘勞工意外保險協會一連做了十四年的公務員,也難怪他對官僚制度的荒謬著墨尤多……緊張的家庭生活,強烈的宗教疑問,不斷折磨著他。在《審判》《城堡》《變形記》等作品中,年輕的主角總是遭受父權人物或當局誤解、誤判、虐待,甚至殺害。”
就這樣,在煩惱苦悶中度過了四十年的卡夫卡,于1924年6月因肺結核英年早逝。然而,假如卡夫卡能夠多活幾年,恐怕也難逃二戰對于猶太人的殺戮。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在這一帶殺害了七萬多猶太人。用余光中先生的話說:“這些冤魂在猶太教堂的紀念墻上,每個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他提到的猶太教堂名為克勞森教堂(Klausona Synagogue),位于老城區的Hrbitova環街243號。
回過頭再來看卡夫卡,你會感覺他的面龐仿佛在預言著什么。用余光中先生的話說:“布拉格的迷宮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場噩夢,最后這噩夢卻回過頭來,為這座黃金城加上了桂冠。于是我們隨智者過橋,再過六百年的查理大橋。白鷗飛起,回頭是岸。”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