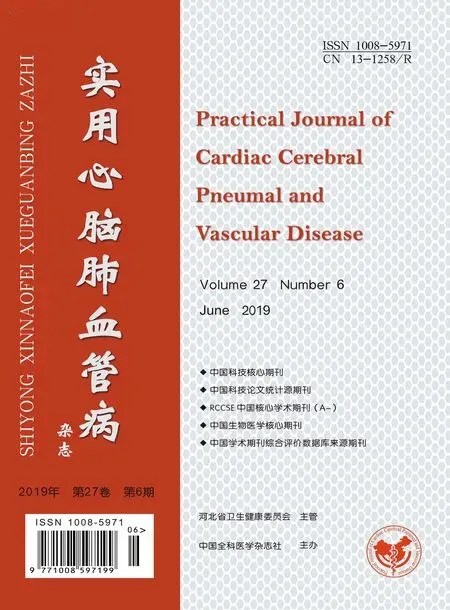超敏心肌肌鈣蛋白I聯合D-二聚體對急性主動脈夾層與急性心肌梗死的鑒別診斷價值
羅常有,王善花,姜華麗,熊賴焱
急性主動脈夾層(AAD)和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兩種急性致命性胸痛性疾病,由于二者均具有胸痛、呼吸困難等相似臨床癥狀,因此AAD 誤診率高達38.96%[1]。AAD 與AMI 的治療方法不同,甚至可能相反,彼此混淆有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因此提高對二者的鑒別診斷水平具有重要臨床意義。超敏心肌肌鈣蛋白I(hs-cTnI)可有效提高早期AMI診斷的靈敏度,但其診斷小面積AMI 的特異度較低,且具有與AMI 相似癥狀的AAD 患者hs-cTnI 水平也存在升高現象;近年研究證實AAD 患者D-二聚體水平明顯升高,可能有助于AAD 與AMI 的鑒別診斷[1]。本研究旨在分析hs-cTnI 聯合D-二聚體對AAD 與AMI 鑒別診斷價值,為提高臨床對二者的鑒別診斷水平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通過病歷檢索系統收集2015年6月—2017年12月在中山大學附屬東華醫院住院的AAD 患者51 例和AMI 患者602 例,其中AAD 經主動脈CT 血管造影(CTA)檢查確診,AMI 經冠狀動脈造影檢查確診,并均排除惡性腫瘤、心房顫動、嚴重肝臟疾病等;后通過仔細分析病歷排除慢性AAD 患者2 例,缺失hs-cTnI 或D-二聚體數據AAD 患者12 例,恢復期AMI 患者38 例,缺失D-二聚體數據的AMI 患者274例,最終共入選病例327 例,其中AAD 患者37 例(AAD 組),非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107 例(NSTEMI 組),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183 例(STEMI 組)。本研究經中山大學附屬東華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1.2 觀察指標 比較3 組患者一般資料、實驗室檢查指標、入院后首次hs-cTnI 及D-二聚體水平,其中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高血壓及糖尿病病史;實驗室檢查指標包括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血肌酐(Scr)、總膽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hs-cTnI 的檢測采用國產RELIA TZ-301 免疫熒光檢測儀,參考范圍<0.15 μg/L;D-二聚體的檢測采用SYSMEX CS-2000i 全自動血凝分析儀,參考范圍<0.55 mg/L。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AS 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q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QR)表示并繪制箱須圖(Box-whisker plot),采用Kruskal-Wallis H 檢驗及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繪制ROC 曲線以分析hs-cTnI、D-二聚體及二者聯合對AAD 與AMI 的鑒別診斷價值,計算曲線下面積(AUC)、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實驗室檢查指標 3 組患者男性比例、年齡,高血壓病史、ALT、Scr、TC、LDL-C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3 組患者糖尿病病史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STEMI 組、STEMI 組患者中有糖尿病病史者所占比例高于AAD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hs-cTnI、D-二聚體水平及二者升高情況 3 組患者hscTnI、D-二聚體水平及二者升高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NSTEMI 組、STEMI 組患者hs-cTnI 水平及其升高發生率高于AAD 組,D-二聚體水平及其升高發生率低于AAD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圖1~2)。
2.3 鑒別診斷價值
2.3.1 hs-cTnI 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AUC 為0.929,最佳截斷值為0.95 μg/L,靈敏度為93.5%,特異度為83.8%,陽性預測值為94.3%,陰性預測值為81.6%(見圖3);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AUC 為0.914,最佳截斷值為0.95 μg/L,靈敏度為84.7%,特異度為83.8%,陽性預測值為96.3%,陰性預測值為52.5%(見圖4)。
2.3.2 D-二聚體 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AUC 為0.977,最佳截斷值為1.20 mg/L,靈敏度為94.6%,特異度為88.8%,陽性預測值為74.4%,陰性預測值為97.9%(見圖5);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AUC 為0.914,最佳截斷值為1.20 mg/L,靈敏度為94.6%,特異度為91.8%,陽性預測值為70.0%,陰性預測值為98.8%(見圖6)。

表1 3 組患者一般資料、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in the three groups
2.3.3 hs-cTnI 聯合D-二聚體hs-cTnI 聯合D-二聚體(hs-cTnI<0.95 μg/L 且D-二聚體>1.20 mg/L)鑒別 斷AAD與NSTEMI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均為100.0%,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別為100.0%、98.6%、93.5%和100.0%。

圖2 3 組患者D-二聚體水平比較的箱須圖Figure 2 Box-whisker plot for comparison of D-dimer in the three groups
2.4 分層分析 87 例Killip 分級Ⅱ~Ⅳ級的AMI 患者中D-二聚體>1.20 mg/L 者20 例(22.99%),203 例Killip 分級Ⅰ級的AMI 患者中D-二聚體>1.20 mg/L 者7 例(3.45%),Killip 分級Ⅱ~Ⅳ級的AMI 患者中D-二聚體>1.20 mg/L 者所占比例高于Killip 分級Ⅰ級的AMI 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7.539,P<0.01);23 例Stanford A 型AAD 患者中hscTnI>0.95 μg/L 者7 例(30.4%),14 例Stanford B 型AAD患者中hs-cTnI>0.95 μg/L 者0 例,Stanford A 型AAD 患者中hs-cTnI>0.95 μg/L 者所占比例高于Stanford B 型AAD 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255,P=0.022)。
3 討論

圖3 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R0C 曲線Figure 3 ROC curv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hs-cTnI between AAD and NSTEMI

圖4 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R0C 曲線Figure 4 ROC curv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hs-cTnI between AAD and STEMI

圖5 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R0C 曲線Figure 5 ROC curv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D-dimer between AAD and NSTEMI

圖6 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R0C 曲線Figure 6 ROC curve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of D-dimer between AAD and STEMI
AMI 指在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基礎上斑塊破裂引發血管痙攣、血小板黏附及聚集、局部血栓形成而造成冠狀動脈血流急劇減少或完全中斷所引起的一組以急性心肌缺血為主要表現的臨床綜合征[2];AAD 主要由內膜撕裂后血液流入內膜中層或內膜中層滋養動脈破裂、血腫形成后壓力過高而造成內膜撕裂所引起,臨床表現復雜多樣[3-4]。研究表明,近10余年來,AMI 發病率和病死率明顯升高,AAD 患者數量出現增多趨勢[5],而由于兩種疾病的臨床癥狀相似但治療方法不同,因此盡早鑒別診斷AAD 與AMI 對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心肌肌鈣蛋白I(cTnI)和心電圖被認為是診斷AMI 的“金標準”,但也有一定局限性:(1)部分NSTEMI患者心電圖無明顯特異性改變;(2)cTnI 升高一般出現在AMI 后2~4 h 內,因此其至少有2 h“窗口空白期”;(3)部分AAD 患者cTnI 水平升高;(4)部分AAD 患者心電圖表現為ST 段抬高。hs-cTnI 是與其骨骼肌亞型相比約有40%的不同源性,是心肌細胞壞死的特異性標志物[6],且目前已被廣泛用于診斷心肌損傷。
D-二聚體是交聯的纖維蛋白降解產物,可反映機體纖溶狀態,是臨床判斷纖溶、正在進行的凝血過程的“指示劑”[7]。從病理生理角度分析,冠狀動脈血栓形成是AMI 急性期最早出現的改變,而D-二聚體水平升高提示血栓形成,因此AMI患者D-二聚體水平明顯升高時間要早于心肌標志物如cTnI等;但受繼發性纖溶等因素的影響,AMI 患者D-二聚體水平變化并不是很明顯,因此D-二聚體并不能單獨作為診斷AMI的標志物[8]。此外,D-二聚體可作為一種非特異性標志物而在多種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中呈高表達,包括重癥感染、惡性腫瘤、肝腎功能不全等[8],因此臨床由于更重視其陰性結果的排除診斷價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水平升高的臨床意義。近年研究表明,D-二聚體水平升高對于無慢性基礎疾病的急診患者急性血栓形成具有重要提示作用[9]。
本研究以hs-cTnI<0.15 μg/L、D-二聚體<0.55 mg/L 為參考范圍,結果顯示NSTEMI 組、STEMI 組患者hs-cTnI 水平及其升高發生率高于AAD 組,D-二聚體水平及其升高發生率低于AAD 組,但21.62%的AAD 患者hs-cTnI 水平升高,因此僅參考hs-cTnI 水平易將AAD 誤診為AMI,而分析AAD 與AMI 患者D-二聚體水平存在差異的可能原因與AMI患者血栓多形成于中小動脈末端、中小動脈直徑較靜脈細、血栓體積較小等有關[8],因此D-二聚體雖不能單獨用于診斷AMI,但有助于鑒別診斷AAD 與AMI[10]及篩查或排除AAD[11-12]。本研究結果還顯示,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AUC 為0.929,最佳截斷值為0.95 μg/L,靈敏度為93.5%,特異度為83.8%,陽性預測值為94.3%,陰性預測值為81.6%,而hs-cTnI 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AUC 為0.914,最佳截斷值為0.95 μg/L,靈敏度為84.7%,特異度為83.8%,陽性預測值為96.3%,陰性預測值為52.5%;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 的AUC 為0.977,最佳截斷值為1.20 mg/L,靈敏度為94.6%,特異度為88.8%,陽性預測值為74.4%,陰性預測值為97.9%,而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AUC 為0.914,最佳截斷值為0.95 μg/L,靈敏度為94.6%,特異度為91.8%,陽性預測值為70.0%,陰性預測值為98.8%;hs-cTnI 聯合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NSTEMI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均為100.0%,而hs-cTnI 聯合D-二聚體鑒別診斷AAD 與STEMI 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分別為100.0%、98.6%、93.5%和100.0%,提示hs-cTnI 聯合D-二聚體對AAD 與AMI 的鑒別診斷價值較高,hs-cTnI<0.95 μg/L 且D-二聚體>1.20 mg/L 時AMI 可能性較小而AAD 可能性非常大,應先行主動脈CTA 檢查,以免臨床倉促溶栓或急診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等錯誤治療而造成嚴重后果。
本研究通過分層分析發現,Killip 分級Ⅱ~Ⅳ級的AMI患者中D-二聚體>1.20 mg/L 者所占比例高于Killip 分級Ⅰ級的AMI 患者,分析其原因可能與Killip 分級Ⅱ~Ⅳ級的AMI患者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有關。楊軍等[13]研究發現,D-二聚體水平升高提示AMI 患者血流動力學異常或微循環功能障礙,有利于篩查出癥狀不典型或癥狀輕微但預后極差的AMI 患者,這對于早期、更積極的救治及改善患者預后等具有重要意義。因此,D-二聚體雖不能作為診斷AMI 的標志物,但由于其與AMI 患者預后可能有關,因此其可作為提示AMI 危險程度的預警信號而幫助急診醫生對AMI 患者的預后進行預測。本研究通過分層分析還發現,Stanford A 型AAD 患者中hscTnI>0.95μg/L 所占比例高于Stanford B 型AAD 患者,分析其原因可能與Stanford A 型AAD 易累及冠狀動脈等有關。因此,臨床發現D-二聚體>1.20 mg/L 且hs-cTnI>0.95μg/L 的急性胸痛患者時,還應注意鑒別Stanford A 型AAD 與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AMI。
綜上所述,hs-cTnI 聯合D-二聚體對AAD 與AMI 的鑒別診斷價值較高,hs-cTnI<0.95 μg/L 且D-二聚體>1.20 mg/L 時AMI 可能性較小而AAD 可能性非常大,但D-二聚體>1.20 mg/L 且hs-cTnI>0.95 μg/L 時應注意鑒別Stanford A 型AAD 與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AMI。由于hs-cTnI、D-二聚體檢查均可在10 min 內完成,因此hs-cTnI 聯合D-二聚體尤其適用于基層醫院對AAD 與AMI 的初步篩查,但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血標本留取時間及留取標準不完全一致、部分患者院前治療內容不詳、未排除院前已應用抗凝治療或溶栓治療者、患者發病至就診時間存在差異等,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仍需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本研究側重于AAD 與AMI的鑒別診斷,其他因素如心房顫動等對D-二聚體這一非特異性指標的影響[8]及AAD 患者D-二聚體表達的時間規律均尚不清楚,研究AAD 患者D-二聚體表達的時間規律及AAD 的相對特異性標志物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有一定關注價值[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