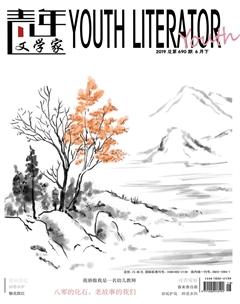“巴掌”下的世俗人生
任靜瑋
摘? 要:商品經濟大潮下出現的新寫實小說,可以劃歸于現實主義大范疇,但是無疑具有了自身獨特之處:以真實的生活刻畫與客觀的情感敘述,表達著對普通人生存環境與生存狀態的終極關懷。蘇童通過“巴掌”串聯人物、表現馬家世俗生活的作品《馴子記》中體現著明顯的“新寫實”特色。
關鍵詞:蘇童;《馴子記》;新寫實;世俗人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8-0-02
在先鋒小說出現的同時或稍后,小說界的另一重要現象即是所謂“新寫實小說”的出現。蘇童作品自1989年的《妻妾成群》開始,先驗性成分明顯減弱,后被納入“新寫實”“新歷史”麾下。新寫實小說的取材和表現領域一般限定于現實時空;而新歷史小說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新寫實小說的一個分支,就其涉及時間范圍而言,取材一般會追溯至清末民初至20世紀中期左右。結合《馴子記》中出現的諸如“薩達姆”“計劃生育政策”“香港剛剛回歸中國”等帶有時代痕跡的信息而言,《馴子記》可以看作是一部“新寫實主義”作品,其中“巴掌”貫穿全文,對父子、夫妻等主要人物關系進行了串聯,真實呈現出香椿樹街上普通人家——馬家人的世俗生活。
《馴子記》發表于《鐘山》雜志1999年第4期“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鐘山》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專欄自1989年第3期開始設立,當期的“卷首語”稱:“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于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1]“新寫實”作為一種創作潮流出現,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不無關系:其創作正是在商品經濟大潮掀起、人們自身生存狀態與社會進步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去揭示中國人在生活困境與幽情愁緒下的生存之累。“新寫實”在蘇童作品《馴子記》中有著較為明顯的體現:真實刻骨的原色生活、零度情感的客觀書寫等。
一、巴掌響亮:真實刻骨的原色生活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迅猛進入現代化,社會急劇趨于世俗化,實惠主義與實用主義盛行,而人們的物質欲求同現實條件之間卻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尖銳矛盾,從而表現出精神的焦慮,《馴子記》中多次出現的“巴掌”背后,即為社會小人物對世俗壓抑生活的本能釋放。
作品視野中心置于香椿樹街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常事。十幾次“巴掌”主要圍繞著主人公“馬大頭”馬駿出現:為人子,他主要是巴掌的受動者,因陪酒員職業、與妻子婚姻關系破裂等緣由多次被父親馬恒大打;為人夫,他主要是巴掌的施動者,最初妻子蔣碧麗的離開就是因打牌誤事遭受了馬駿愛面子、脾氣壞而引發的三個巴掌;作為父親與陪酒員,馬駿也有著多次與巴掌有關的經歷,于王小六、小狗等人他是打人者,于表弟與兒子馬帥他打人未遂、痛苦忍耐……巴掌下的生活似乎重復而無趣,暴力的宣泄背后是人們境遇的困頓與精神的危機。
對日常生活本體地位下的重復敘事是對“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2],但它無疑精確描繪出了普通環境中普通小人物“生存之實”的瑣碎常態——追逐物質利益,滿足心理欲望似乎是世俗生活下人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馴子記》中馬駿辭去鳳鳴樓廚師一職選擇了國際海鮮城陪酒員、蔣碧麗推銷如意發財酒,這些行為何嘗不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與切身實際利益的追求。此外,馬恒大的種種所謂的習慣也是其生活無休止重復的體現,“每天早上他都急著站到自家門前,讓來往的人們看見他的身影”[3],“動用了嗅覺、聽覺、觸覺,多方位的監督馬駿的生活”[4]。而這些習慣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時間走得太快”的時代節奏所引發的焦慮色彩。
“日常生活在重復性思維的慣性作用下主要是日常經驗的呈現,平淡無奇,波瀾不驚。”[5]《馴子記》這樣瑣碎生活的多次重復其實并沒有削減小說的感染力,作品中社會和人生均呈現著一種物欲橫流的駁雜原色。“寫人的生存本真狀態,或曰‘寫人的原生態一直是‘新寫實執著追求的藝術價值。”[6]瑣碎的常態卻恰恰能給人以親切感,極易引發讀者共鳴。因為日常很重要,生活本來如此。
二、冷面敘述:零度情感的客觀書寫
平庸、瑣屑的俗世化原色生活現實的描寫中,縮減了作家主觀表現,以零度敘述呈現出馬家普通生活的原始狀貌,所以讀者似乎無法于作品中直接找尋到蘇童作為敘述者對于香椿樹街人們世俗生活所傳達的情感態度與思想傾向。新寫實中呈現出的“新現實”被認為帶有了濃厚的自然主義傾向:作品缺乏對普通人追求與期望的深度表現,消解了生活的詩意、抹煞了人們對美好理想的追求,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時代面前,以致對現代人的生存狀態與理想追求的表現是極其不深刻的。那么對于《馴子記》中以馬駿為代表的小市民生存狀態的展示,真的消解了人生的社會意義?
事實并非如此,情感零度的“冷面敘述”并不是創作主體作家情感的零度。正所謂真正的冷酷理應表現為對現實的漠視,所以當香椿樹街“巴掌”下的普通小人物出現在蘇童筆下時,無疑代表著作家對于這個物欲橫流的俗世生活有著超乎常人的見解與認識。《馴子記》中的馬駿這一核心人物以反叛者形象存在,“他想干點什么,干點壞事也行,干點別的也行,只要是父親反對的事,干什么都行”[7];也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又始終選擇了忍受父親的數落,挨打時母親幾次出現于他的幻覺中單調重復著“快跑,快跑,快跑”,這種催促是一種逃避俗世的象征,但馬駿不想跑,“世界上那么多人活得不好,要都這么一跑了之,地球就變成月球了”[8],這便是他對生活的態度:無奈而不甘。再看文章最后,馬駿喝了工業酒精兌制的毒酒在急診室所講的遺愿是:“爸爸,從小到大,挨了你那么多巴掌,我要打你,一巴掌,打回你,一巴掌。”[9]他始終有著反抗的意念,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就在父親馬恒大遂其心愿后,揚起的手又放下,“不能打,你是我爸爸”[10]。如此看來馬駿這一形象實是性格極富張力、復雜而豐富的圓形人物,他自始至終忍受著來自于俗世生存的壓抑,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束縛與羈絆,外在的眼光、父親的訓教……但馬駿的結局似乎是“巴掌”下的勝利,最后的死亡證明了他的存在,包含著對其生命的形態與意義的肯定:日常生活是生與死之間的存在,馬駿死亡結局的營造是對不堪的俗世生活堅定抗爭后的一種疲憊解脫的勝利。
紛繁復雜、壓抑感充斥卻又無從宣泄的俗世生活引發了作家對普通小人物生存、發展的同情、關注與思考,蘊含著的也正是蘇童對現實凡人常事濃重的悲憫情懷與人性關懷,這亦是作家對時代與俗世思考的獨特之處。蘇童對于以馬家為代表的灰色小市民生活場景的描寫,有效地對時代進行了簡化,同時也有效地豐富了它:《馴子記》無疑蘊含著作家對俗世中普通生命的思考,其中獨特的生命意識與悲憫關懷賦予了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
蘇童曾經說過:“一切都要從閱讀開始,生活的真相注定是隱秘的、閃爍的,所有文學作品中的現實工程,并不穩定,它就像一個開放的建筑工地,需要作家與讀者共同搭建。”[11]所以,無論對于作家蘇童,抑或是新寫實小說,其中所蘊含的生命意識與人文關懷仍值得所有人去深入探究與不斷深思。
參考文獻:
[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社,2007:295.
[2]金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M].上海:上海文藝社,2011:522.
[3]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44.
[4]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44.
[5]張伯存,盧衍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學轉向與社會轉型研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96.
[6]陳傳才.中國20世紀后20年文學思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202.
[7]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53.
[8]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57.
[9]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71.
[10]蘇童.蘇童作品精編[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272.
[11]華中科技大學中國當代寫作研究中心.邊緣與頹廢——2013春講·蘇童 謝有順卷[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