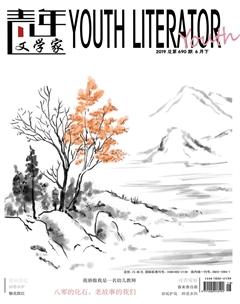從《世說新語·德行》看魏晉士人的道德觀
摘? 要:《世說新語》是我國第一部志人小說,通過記錄漢末魏晉時期士族階層的逸聞軼事,刻畫了漢末到東晉時期士族階層的群像,反映了這一時期士人階層的生活面貌、為人處世及其精神價值取向。在《世說》中,以“德行”作為36個門類的開篇之首,可見德行之重,謂之“德行第一,百行之美”。《世說新語·德行》共47篇,涉及孝道、慎言、清廉、儉約、忠義、敬賢等多個方面,記錄了魏晉時期士人階層為人稱道的言語品行,反映出魏晉時期士人階層的道德觀。
關鍵詞:世說新語;德行;魏晉士人;道德觀念
作者簡介:顧妍(1990-),女,漢族,上海市人,碩士研究生,鄭州西亞斯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對外漢語。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8-0-03
《周禮·地官·師氏》:“敏德以為行本。”漢鄭玄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為四教,又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無不賴此以大以明。”《世說新語·德行》開篇即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以此作為第一則,全篇所記錄言行均為當時魏晉士人所稱贊的自身修養與言行舉止,其言為士人之準則,其行為世人之典范。魏晉時期儒家禮教勢弱漸微,人們的思想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通過記述當時士族階層所推崇的道德品行,反映出具有魏晉時代特征的士人階層的道德觀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百行孝先
古人云“百善孝為先”,《論語》中也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 ,可謂孝矣。”孝,作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歷來被人們稱道,作為評價人物的首要標準。晉人以孝治天下,僅《世說新語·德行》這一門類中,就有十三則寫到孝道,涉及愚孝、生孝、死孝、廉孝、試孝、忠孝等多個方面,如下所記: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所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于是感悟,愛之如己子。(《德行》14)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德行》17)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吏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德行》21)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后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吊省,號踴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凄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后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德行》47)
無論是王祥的愚孝、和嶠的生孝還是王戎的死孝、廉孝,均體現出古人以孝為自身言行準則之首、品鑒他人標準之列,王祥因孝得后母之愛,和嶠因孝得漢武帝之關切,王戎因孝聞名,吳隱之因孝得貴達,皆為孝之善報也。孝之善報之極致,莫過于陳遺“因孝得命”: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后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于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德行》45)
需要說明的是,自古忠孝為立身行事基本準則,《孝經·開宗明義》:“終於 立身。”鄭玄注:“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忠于國君,孝于父母,自古兩難全。在魏晉之前,國大于家,忠大于孝。然而在《世說·德行》中有關孝道的有13則,而有關忠義的卻只有一則,且為忠孝,依舊為孝,可見在魏晉時期孝的地位是高于忠的。在魏晉時期卻形成了“親先于君,孝先于忠”的忠孝觀。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一方面東漢末年,宦官專權導致皇權的削弱,兩次黨錮之禍也使得士人不再傾心政治,君權被進一步削弱;另一方面士族門閥制度形成,唯有宗族興盛個人才能成名做官,因此唯有推崇孝道才能使一個家族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從而使家族立足于亂世之中而不崩。
二、慎言灑脫
魏晉南北朝時可謂是我國歷史上政治最黑暗、社會最混亂的動蕩時期,然而也是在這一時期,由于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動搖,老莊思想的趁勢 興盛,佛教道教的相互影響,士人們思想精神自由,富于智慧,氣度坦然,重視藝術之風,頗有魏晉時代之風貌。亂世之中的士人階層面對動蕩混亂的外部環境,卻依舊能夠處其中而自保,且形成了影響深遠、超然灑脫的“魏晉風度”,不得不說與他們謹言慎行、淡泊名利的處世態度有著密切的關系。位列“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至慎言玄,“未嘗臧否人物”,嵇康“喜怒不形于色”,隱忍于亂世,實乃當時生存之道,修身之德。如第7則: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側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沾,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季方之父為官正直清廉,為世人所稱道,其言行必影響子女,陳季方所言謙虛謹慎,得因于其家教。謹慎低調的處世態度,為當時士人所稱道,他們不再追逐名利,關注社會現實,而是寄情于山水、酒藥與詩樂,“皆以放任為達”,追求自然、自我與自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頗有灑脫超然的生活態度。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斗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德行》41)
“晉人浸淫老莊,沐浴玄風,言行常能有此灑脫現象。”魏晉士人不再一味追求名利,由入世轉為“出世”,由對外部現實的憂慮轉向對內心世界的關照,寄情山水、忠于藝術,既由當時社會政治黑暗的環境所致,又有其自身思想變化而導致追求變化的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出世”并非真出世,士人們雖轉向對自由灑脫生活狀態的追求,但仍舊心系家國安危,其言行雖轉向對個人的追求與重視,然仍有天下關懷,如批判當時的奢侈之風,重視孝道的傳統,對賢人的尊敬與重視,無不表現了魏晉士人依舊心系天下,關注政治的思想情感。其超然灑脫的追求更多的是表現出面對當時政治社會的生活態度,于亂世中的超然灑脫而關注社會,更值得贊頌。
三、清廉儉約
“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古人以節為美,勤儉節約自古就是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貧者,士之常”,名士為官,清廉難得,實屬不易。陳太丘“貧儉無仆役”、周鎮“船小而大漏”、王恭“作人無長物”,均為名士廉儉范例。王戎不僅因孝聞名,而且清廉,其父為官清正,死后義故因其德惠致賻數百萬,王戎一律不收,孝廉實屬難得,可謂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范宣年八歲,后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發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后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裈邪?”范笑而受之。(《德行》38)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外無馀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德行》40)
殷仲堪清廉儉約,不僅自身生活簡樸,而欲率物以育子弟,不以“登枝而捐其本”。清廉儉約作為當時名士賢人的品質之一,實為魏晉士人的道德價值評判的一個標準。為官正直,清廉儉約,造福地方的名士,乃是人們心中的真名士。
自古以來,多有皇室揮霍無度而失江山社稷之事,商朝殷紂王在位后期,居功自傲,建鹿臺,造酒池,懸肉為林,過著奢華荒淫的糜爛生活,間接導致商王朝的敗落。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大興土木,建筑宮殿,其中包括著名的阿房宮,秦二世的過度奢侈浪費的生活,使秦朝走向了末路。漢末的官僚貴族竭力追求奢侈放縱的生活方式,大肆揮霍財富,以滿足自己的私欲,導致了漢朝的滅亡。西晉統一三國之后,王公貴族更是奢侈成風,針對這一社會現象,《世說新語》中就有《汰侈》一門專門講述、諷刺這一時期矯汰奢侈的不良風氣,可見魏晉時期士人們對于奢侈之風的反思與批判。因此,在魏晉士人的道德觀念里,清廉儉約便成為賢人的優良德行之一,也是人物品藻的評價標準之一。
四、性善忠義
魏晉士人生于亂世之中,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里,人們轉向對人自身的關注,故以性命為重,有服五石散之風即反映出人們對生命的渴望與追求,且士人所特有的天下關懷使他們對他人抱有憐憫之心,所謂“仁者愛人”,儒家思想地位雖有所下降,然士人所摒棄的是其名教而非其禮義,“孝慈仁愛”,仍然為士人們所追求額贊揚的優良品性。
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褲,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德行》33)
謝安時值七八歲,尚且有此憐憫之心,可見日后成人必為君子乎。又有庾公效孫叔敖為保他人平安而拒賣馬,亦達也。魏晉時期割據紛爭,戰亂頻仍,社會動蕩不安,明哲保身為學多人所信奉之道。然顧榮贈炙之事雖小而引同坐嗤之,足以見其善良品性。行炙人在動亂中仍以涌泉報以當日滴水之恩,其德亦然。施德與報恩,極為性善與忠義。道義之舉,其貴重在于舍自身而對友忠義,舍己為人,乃是忠義的最高境界。荀巨伯因重視友情而聞名,其重不同尋常,其效亦非平凡,如第9則所記: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并獲全。
荀氏之舉,將自身安危置之度外,生死關頭仍然堅持忠義之氣節,連強盜都有感于其義而行道撤軍,“一郡并獲全”,實乃忠義之神功,可見魏晉人人以忠義為美德而敬之。忠肝義膽,歷來被人們視為是君子、俠義之士的品行,忠義、氣節也是魏晉士人道德觀念中所肯定的德行之一。
五、尊禮敬賢
《世說·德行》開篇即述“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陳仲舉遷任豫章太守時顧不上去官署視察政事而是打聽徐稚所在前去拜訪,陳仲舉被貶謫之后依舊心系禮賢,可謂是“儒者常有道心”。將此作為開篇第一則,并稱其“言為士則,行為世范”,可見禮賢之重。在《世說·德行》篇中有許多賢人因其賢而聞名的故事,無論是黃叔度氣量深廣之難測,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還是荀淑“清識難尚”,鐘皓“至德可師”,均為聞名于后世之賢人。
值得說明的一點是,重賢的另一個表現是與善人交,如管寧淡泊名利與華歆割席分坐,周乘時日不見黃叔度則生鄙吝之心,郭林宗心急造奉高而從容詣叔度,可見晉人重賢而有取舍。
魏晉士人所尊之賢要像陳仲舉一樣“有澄清天下之志”,像黃叔度一樣“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像李元禮一樣“風格秀整,高自標 持,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像王恭一樣清廉、“作人 無長物”,像管寧一樣淡泊名利,像阮籍、嵇康一樣喜怒不形于色。
魏晉時期,儒家傳統思想的地位雖然有所下降,士人們“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再受縛于禮教而追求自然任達的生活狀態,而是轉向對自我價值和人生的關注,然而其中有些禮教依舊為士人們所傳承推崇,如前文中所寫的孝禮、“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等,處于亂世中的士人們依舊以和為貴,如第十則所記,華歆、陳元方兩家皆不失和樂之法則: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里,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又如第39則: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馀 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此則看似與禮教無關,實則關乎婚姻禮法,王獻之臨終依舊認為與郗家之女離婚之事為人生“異同得失”,可見其對傳統婚姻禮法的遵守。
“魏晉士人雖追求個性的解放,做出種種越禮行為,但在他們的心里并不想廢棄禮教,他們還常常以禮之標準評價人。他們不像漢代儒生那樣立足具體經書的闡釋,他們追求的是禮中所含之旨趣,以求達到一種玄遠高深的境界。”可見,魏晉士人的“越名教”并非是拋棄禮教,而是在禮教的基準線之上追求一種放達自然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境界。
六、結語
魏晉時期的道德觀,既對先前的傳統道德有所繼承,又因其時代的特殊性而有所變化,形成了魏晉時期獨特的道德觀,既有傳統的因素又有時代的特色,既有政治的影響,又有思想的獨特。在魏晉這個思想解放、個性張揚的時代,產生了許多聞名于后世的名士,其風度依舊猶存于現世,影響著當代人的道德觀和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