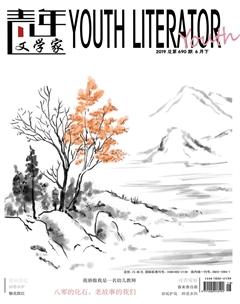從《淮陰侯列傳》看《史記》的“寓論斷于序事”
摘? 要:《史記·淮陰侯列傳》以“寓論斷于序事”的藝術手法通過韓信對劉邦知遇之恩不忘以及劉邦對韓信的猜忌的詳細敘述表明韓信謀反的不合理性,體現了史記的“實錄”精神。
關鍵詞:淮陰侯;謀反;“寓論斷于序事”
作者簡介:孫雅婷(1989.10-),女,漢族,安徽蚌埠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8-0-02
《史記·淮陰侯列傳》的傳主韓信是漢朝的叛將,這是正史中的定論。司馬遷在其《高祖本紀》云: “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 夷三族”,《蕭相國世家》中亦云:“淮陰侯謀反關中, 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然而歷史學家張大可在其《史記研究》中卻謂《淮陰侯列傳》“是一篇滿灑同情淚水的翻案史傳”,如果張大可所言屬實,那司馬遷豈不是自相矛盾?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二十六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于敘事中寓論斷” 就是通過對史實的敘述把自己的理解和評議表達出來,即“寓論斷于序事”。由此可見“寓論斷于序事”是在不便直言之時的委屈婉約的隱晦表達,司馬遷用這種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對“今上之祖”的“非議”,一方面也揭露了史實,不違背自己作為史官的職業操守。此外,“寓論斷于序事”不僅是無奈的自保之舉,其表達方式的含蓄也增添了《史記》的文學色彩,使其享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名。下面本文將以《淮陰侯列傳》為例探析“寓論斷于序事”的表現方式。
一、三矢其志,何來謀叛
仔細研究《淮陰侯列傳》,我們會發現太史公用大量篇幅,不厭其煩地對武涉和蒯通的游說進行描寫。俆喬在《經史辨體》中言《淮陰侯列傳》“前半,敘信將略,后半,詳序齊人蒯通說詞及信答語,以深明信之不反也”。方苞在《望溪集》中曰:“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至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信義,乃謀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之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當是時,韓信破楚有功,立為齊王,聲威正盛,楚國痛失龍且,項羽派盱眙人武涉往說韓信,曰: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由武涉之言可以看出,此時的韓信足以左右時局,可謂“得韓信者得天下”,他已經不需要依附于楚或漢,甚至可以與項羽、劉邦相抗衡。面對三分天下,自立為王的誘惑,韓信卻絲毫不動,對武涉謝曰:
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此時的韓信感念劉邦的知遇之恩,毫無謀反漢王,自立門戶之意,斷然拒絕了武涉的建議。
武涉走后不久,齊人蒯通以面相之術企圖游說韓信,曰:
……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原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慮之。
面對蒯通的勸說,韓信給了相似的回答: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如果說前面武涉和蒯通的游說多少還是為項羽而謀的話, 那么接下來蒯通的游說則鞭辟入里, 幾乎全是為韓信著想了:
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他分析當時的形勢,建議韓信與楚漢一起鼎足天下,以前人張耳和陳馀、文種和范蠡的前車之鑒勸誡韓信,指出其功高震主,終會不容于劉邦,建議韓信與楚漢一起鼎足天下。換來的是韓信的一句:“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韓信雖然有所擔心, 但當數日后蒯通又來相勸時,“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司馬遷用大量篇章詳寫韓信三次謝絕武涉、蒯通的謀反提議,所有這些都與“謀反關中”相矛盾。
項羽死后,鐘離眛投奔韓信,劉邦欲借游云夢逮捕韓信,韓信意識到劉邦的意圖,卻仍然“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后“持其首,謁高祖於陳”,歷經一捕一放后被劉邦降為淮陰候,此后韓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至于后來與陳豨的謀反更是疑云重重,首先,此時的韓信被降為淮陰侯,失去了軍權,他在有能力和劉邦、項羽三足鼎立之時都沒有謀反,又怎會在已無力回天之時貿然造反。其次,相對于對武涉、蒯彤游說韓信的詳細敘述,司馬遷對韓信謀反失敗被斬的經過著墨不多,甚至多有漏洞: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謀反叛國的機密豈會輕易泄露,告密為何如此順利,呂后的縛信、斬信為何如此草率等,無不發人深思。司馬遷不惜運用大量筆墨來描寫武涉、蒯通二人的三次游說,很多游說之詞甚至重復,這顯然不是太史公的敗筆而是作者刻意為之。反復的描寫和說客的對話傳達出韓信對劉邦知遇之恩的感念不忘,對漢室天下的忠貞不二,試問認為“陛下所謂天授, 非人力也”的韓信又怎會在漢室已定之時選擇謀反。司馬遷通過對事件的敘述表明的自己的觀點,還原了歷史的真實,不負“實錄”之名。
二、功高震主,見忌而亡
韓信一生叱咤風雨,“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在楚漢相爭時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方苞言:“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系焉。”(《方望溪先生全集》)前文中已經論述了韓信不可能謀反,那又是什么讓韓信挾如此不世之功而最終被斬而亡。湯諧曾說: “然信一生志愿, 只在封王;既為齊王,愿望已畢, 并無絲毫反念, 而卒以赤族, 故太史公既深責之又重傷之。既深責信之矜功要爵, 自取滅亡; 又重傷漢之蓄意剪除, 激令怨望。因特詳述蒯通說信反漢奇策于前, 更將釋通之罪作結于后, 以見通勸信反猶得無辜, 信本不從通反, 而漢奈何因疑生嫉, 激而罪之至于此極也。”(《歷代名家評<史記>》)
韓信之死究其原因逃不過一句“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多疑猜忌是劉邦公認的性格特點之一,面對擁有卓越軍事才能的韓信,他一方面利用其才華為自己建功立業,另一方面也對其抱有防備之心: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六月,漢王出成皋……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當時是韓信軍功卓著,積威日盛,劉邦恐其威脅到自己的權威,開始對韓信進行打壓,收了他的將印給以虛職。如果說此時劉邦對韓信還是以打壓為主的話,當韓信殺龍且,平齊國,并自請“假王”后,劉邦對韓信的猜忌已經深植于心了,雖然迫于時局封韓信為齊王,但韓信也已成了劉邦的心頭大患,如鯁在喉。所以當項羽一死,劉邦就開始發難: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如此急切的褫奪韓信的軍權赤裸裸的昭示了劉邦對韓信的忌憚,然失去了軍權的韓信并不能令劉邦安心,君臣見起碼的信任蕩然無存,真可謂動輒得咎:
項王亡將鐘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未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 “公非長者!”卒自剄……遂械系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
這一次,韓信用好友的人頭向劉邦示忠,換來一捕一放,雖被貶為淮陰侯,但好歹保住了性命,下一次卻沒有這樣的幸運。在經歷一系列的見疑發難后,韓信終于迎來了死亡的結局。本文之前對韓信謀反被斬也有涉及,已提出司馬遷對這一事件描述的疑點頗多,呂后作為陪漢高祖一路走來的發妻,是具有一定政治鑒別能力的,如果不是早已了解劉邦之意或得到劉邦授權是不會如此貿然的殺害開國功臣的。雖然韓信的被殺劉邦不在場,事情卻照著他的意愿發展。司馬遷通過對這一段不合理的歷史敘述給讀者留下疑問來探尋真相,也把自己的論斷隱藏在敘述中。
韓信被殺后,劉邦回到洛陽,聽到韓信已死“且喜且憐之”,司馬遷用一個“喜”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韓信的死是正合劉邦心意的,也印證了上文中劉邦因猜忌而對韓信的一系列發難。
三、小結
《淮陰侯列傳》是《史記》中的經典篇目,也傾注了司馬遷的無限巧思,他以看似簡單的歷史敘述引起讀者的深思,從而看見隱藏在時局限制下的真實的人物形象,真實的歷史。誠然,韓信的悲劇結局成因是復雜的,與他自身的高功自居性格以及政治敏感的缺失都有關系,但是為上位者忌憚確是導致其悲劇結局的最直接的原因。
參考文獻:
[1](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9.
[2]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3.
[3]張大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4]白壽彝.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