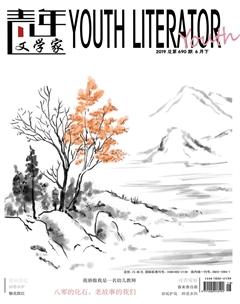試析歐美種族類型電影中的身份敘事
摘? 要:種族話題作為歐美影片中的一大熱門,向來在電影市場占據著一席之地,種族影片常常以討論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黑人等在社會生活中所處生存處境以及個體如何面對和處理社會對其的身份界定作為其內容的中心,近年來,在導演的思考與探索之下,種族題材的電影在內容的挖掘和敘述方式、手法上呈現新的變化。筆者試圖從敘事學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有代表性的歐美種族電影,探討此類影片在身份問題上如何進行敘述和被敘述的。
關鍵詞:種族電影;身份敘述;敘事學
作者簡介:陳義伊(1988-),女,貴州省正安縣人,碩士,貴州商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文學批評、影視美學。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8--02
對于種族題材的影片,繞不開的首要議題之一就是身份,陳永國教授在《身份認同與文學的政治》一文中提出,身份認同包括身份的塑造與身份的敘述,身份的敘述包括自敘述和被敘述,“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黑人等被敘述者要擺脫被塑造身份而真正建構自己的身份,必須首先爭得敘述權,……從被敘述而轉入自我敘述,進而敘述他者,才有希望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1]能夠敘述自己和他人的前提是要成為敘述的主體,而敘述的主體是依靠敘述行為來完成敘述,而敘述行為就包括“誰來敘述?”、“如何敘述”等問題,“誰來敘述”就會涉及敘述聲音的問題,而“如何敘述”則會牽涉敘述視角的問題。
一、敘述聲音
《為奴十二年》,講述了所羅門從一個自由黑人被騙成為奴隸到被搭救最終重獲自由的故事,敘述者不動聲色的隱身于文本之中讓人物、事件自行呈現,觀眾甚至會忘記這個敘述者的存在,敘述者在此主要起著搭建整個故事的框架和支配故事走向的作用;《被解救的姜戈》,隱身的敘述者給我們講述了姜戈這個黑奴如何從被解救走向自我解救的過程;月光男孩的故事敘述者向我們敘述了一個多重邊緣身份的黑人男孩奇倫的成長史;逃出絕命鎮,敘述了一個黑人攝影師到白人女朋友家做客的驚險故事。這幾部影片中的敘述者都是客觀的敘述者,他們盡量充當故事的傳達者,起陳述故事的作用,不在敘述中介入自己的態度。然而這種盡量不介入的態度中依然會可能留有敘述者態度的痕跡,我們可以看出,敘述者在敘述所羅門的故事的時候,并沒有著力的渲染他努力自救和確認自己身份的情緒,而是較為客觀、理性的敘述了整個過程,而同樣,被解救的姜戈也是如此,姜戈解救自我和解救妻子的心路歷程只有他通過回憶妻子和他逃跑后受到懲罰的鏡頭,被分開販賣的鏡頭展現,敘事者和人物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他面對白人牙醫對自己的幫助和利用,呈現怎么樣的心理活動,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姜戈的表情和語言、行為去推測。《撞車》則不同,同樣是不參與故事的敘述者,然而敘述者的態度在故事人物和事件中隨處可見,撞車講述由一起普普通通的撞車事故而引發的對種族歧視問題的關注和探討,敘事采用多主線交錯的結構和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從不同的方向、不同身份的人物身上表現種族沖突的話題,盡管敘述者沒有采取深入某個角色的主觀意念去闡述這個故事,但是敘述的態度已經非常鮮明:把種族問題的根源,簡單粗暴地歸因于現代人由于焦慮和誤會產生的隔膜,因此也把種族的問題的解決,期待于愛與包容。趙毅衡認為,敘述者是敘事文本的創造者,他對于全部信息擁有解釋、選擇、處理和講述的全權,也就是敘述者會因為特定的目的選擇講什么和怎么講,以上的電影的敘述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特點,大部分的電影采取了一個看似不相關的敘述者來敘述,他盡量不露出自己敘述的痕跡和保持敘述態度的“客觀性”,敘述者的身份、態度、和敘述的方式常常會影響故事里人物,敘述者盡量不干預故事,但是也可能減弱了故事人物的力量,而這種看似客觀的敘事態度,意味著人物的身份意識并不能得到強烈的樹立,使得人物沒有擺脫被敘述的身份,他們不能實現自我自由的敘述,依然作為被敘述者存在,因此無論是 《為奴》中 還是《被解救的姜戈》 兩部影片中,即使他們最終獲得了自由和解放,靠的卻是白人群體的相助和解救,而白人牙醫甚至在姜戈能夠蓄積力量自救和確認自己的身份的道路上起了不可忽視的關鍵作用,在身份敘事的問題上,敘述者知道種族問題中的性別、階級問題,卻回避了探討它,或者把問題留給了觀眾,盡管側面的反映了其他黑人的生存狀況,《為奴》 還是把主要的焦點放在所羅門的解救上,如果說所羅門有獲救的權利是基于他所屬的北方州區和階層給予他的自由身份,而南方的黑人卻連獲取自由的“理論”依據也失去,更別提帕西這樣的黑人女奴,他們只能遠望所羅門重獲自由的背影,默默地站成背景。而姜戈的妻子雖然能夠有獲救的好運,但是她也只能是等待解救的命運。
二、敘述視角
所有的敘事學研究都明確一點,敘事聲音不等同于敘事視角,視角研究的是誰看的問題,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視角有感知性視角和認知性視角之分,感知性視角是指信息由人物或敘述者的眼、耳、鼻等感覺器官感知,認知性視角指人物和敘述者的各種意識活動,包括推測、回憶以及對人對事的態度和看法。在一部作品中,誰感知焦點,誰便是視角的承擔者。胡亞敏的敘事學把視角分為: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外聚焦型。內聚焦型的特點是從人物的角度展示其所見所聞,敘述的是人物熟悉的環境,展現人物的內在情緒,而內聚焦的視角能彌補不參與故事的敘事者的缺陷,幫助故事人物更好的作出自我身份的敘述,
《月光男孩》和《逃出絕命鎮》就是采取的這一視角,《月光男孩》中通過奇倫的視角描述了他在成長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困境,表現了他在面對身份困惑時候產生的內心沖突和掙扎,以及明確自己身份認同的心路歷程,影片里有這樣的一幕,毒販胡安,關心和影響奇倫,替代了奇倫缺席的父親位置,并告訴奇倫他名字blue的由來,是因為一個老奶奶告訴他,黑人的皮膚在月光下是藍色的;于是電影切到另一幕,奇倫坐在浴缸里發呆,浴缸被他放滿藍色的消毒水,皮膚是身份的某種隱喻;奇倫因為胡安的話,啟發了對自我膚色和身份的思考,這些感知都是從奇倫自身的視角去感知的。逃出絕命鎮,從主角黑人攝影師克里斯的視角去觀察了在白人女朋友做客的種種怪異,從黑人群體自身的視角去循序漸進地剝開層層謎團,最終揭示了種族平等的和諧現象背后,隱藏著白人對于黑人欲望和控制的真正危機,讓人更能夠感同身受地親身體驗少數族裔面臨的那種抹殺身份的艱難險境。
《相助》是將內聚焦視角運用的最為成功,既通過白人女性斯基特的視角發現了黑人女性發聲的困難:一方面來自白人女性的壓迫,黑人女仆盡心地為白人女性們服務,甚至有的黑人女仆服務了兩代人,然而卻沒有得到的作為“人”的身份的尊重,雖然黑人女仆陪伴和撫養了這些白人女性,然而,他們只被看做這些白人資產階級女性的私人物品,隨意地冷漠處置;黑人女性遭受的另一層壓迫,來自性別的壓迫——黑人男性對黑人女性的壓迫;米妮的丈夫對米妮的虐待并不是透過米妮自身的視角來反映的,而是透過黑人女仆艾比琳和另一位白人女性塞莉婭們去體現的,米妮在給艾比琳講述自己解雇的過程中,艾比琳聽到了電話那頭,米妮丈夫里洛回來以后對米妮的毒打和米妮的慘叫;透過塞琳婭的視角,我們得知米妮的額頭的傷口,知道不是被磕碰的,而是被打的;而黑人女性自身的視角加入,更能真切地反映了他們在面對身份尋找時候內心的糾結和掙扎,斯基特向幾位黑人女仆求助,希望能夠采訪他們的生活,卻遭遇了艾比琳和米妮等的拒絕,同時影片透過他們的視角看到了白人女性世界的偽善,表面上是給予他們平等的待遇的建獨立衛生間的行為,背后是深深的歧視,而所謂的對黑人關注的各種慈善捐助也不過是為了滿足他們虛榮心和維持社交、消遣時間的虛偽目的,于是他們決定拿出勇氣去抗爭這種種族歧視的不公,趙毅衡認為一部優秀的敘述作品,常常能做到的理想的敘述者和敘述角度的配合,他稱之為“敘述方位”,前面列舉的幾部作品,很好地選擇了種族群體作為角心人物的視角,讓觀眾更好地貼近人物,感受他們的內心世界,也能幫助他們在減少敘述者干擾的情況下完成自我敘述,
然而,也有部分影片中,選取了并不理想的“敘事方位”,例如今年榮摘奧斯卡金像獎好評不斷的《綠皮書》,視角選取的卻是白人司機托尼,盡管故事是反映了黑人音樂家唐.雪莉博士和白人平民司機托尼在一段公路旅行中,達成相互的理解、促進彼此成長的故事,然而托尼為主的視角明顯地削弱了唐.雪梨發聲的可能,唐博士對于自己身份的困惑——“我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我甚至也不是男人”的痛苦是透過托尼的視角反映的,他每晚孤獨靠喝著威士忌排解找不到歸屬的孤獨是托尼在感受,在這部影片中,托尼作為角心人物的作用更大,而唐博士更像一個被凝視者、被觀察者,同樣,在《殺死一個知更鳥》這部影片中,采取了律師的女兒,一個白人小女孩的視角去觀察一個因為種族歧視而遭到誤判釀成悲劇的故事,一方面使得這部影片更強化的是兒童教育片的意義,而對于種族歧視問題的深入探討遭到了削弱。
三、結語
敘述聲音決定了怎樣被敘述,而敘述視角的選擇會影響怎么實現自我的敘述,種族類型的影片,核心是挖掘和反映黑人、被殖民者、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況和身份困境的問題,因此選擇角色他們自己成為敘述的主體,并采取以他們為主的內聚焦的視角,更利于展現他們在身份尋找方面的內心變化,促成他們擺脫被敘述的命運,實現敘述自我的可能。
參考文獻;
[1]陳永國. 身份認同與文學的政治[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第31卷.
[2]趙毅衡. 當說者被說[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3]胡亞敏. 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