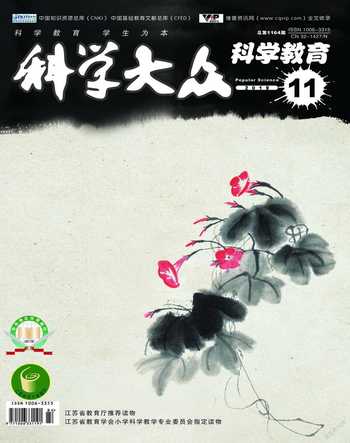如何捕捉文本的“弦外之音”
繆青
摘 要:文本解讀對于初中語文教學來說意義至關重要,而怎樣解讀,探究文本的“弦外之音”,這一直是困擾語文教師的一個難題。真正的文本解讀理應素讀文本、細讀文本、適讀文本,在以學生為中心的基礎上,帶領學生對文本進行適度挖掘與拓寬,這樣才能更好地捕捉到文本的“弦外之音”,把握文本的深層內涵。
關鍵詞:初中語文; 素讀文本; 細讀文本; 適讀文本
中圖分類號:G633.3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6-3315(2019)11-009-001
《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將文本解讀稱之為“通過分析來理解”。文本本是“半成品”,真正、合理的解讀應該是對文本的理解與生成,是一個要求教師不局限于文本表層,去指導學生挖掘文本、充實文本、捕捉文本的“弦外之音”,最終拓寬文本寬度和廣度,將之完善的過程。
它是中學語文閱讀教學中的重中之重,沒有文本解讀,語文課堂就成了空中樓閣、無根浮萍。因此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讓語文回歸文本、重視文本。那么到底怎樣解讀文本,才能夠教導學生正確捕捉文本的“弦外之音”,領悟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內涵?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
一、素讀文本,避免先入為主,陷入“標準答案”的思維定式
所謂素讀文本,是讓教師和學生在不閱讀任何教參、資料的前提下,自己閱讀文本、解構文本,生成對文本的理解和認知。文本解讀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便是針對以往“標準答案”“答案唯一”造成的語文的僵化,強調讀者自身的背景、經驗、能力,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然而現在許多教師過度依賴教參和前人資料,對文本淺嘗輒止,缺乏自我思考和深入的理解,教學中往往照本宣科,以本為本,長此以往惡性循環。筆者也曾犯下過這類錯誤。
在旁聽《皇帝的新裝》公開課時,某老師讓學生用一個字來概括課文的全部內容,標準答案給出的是“騙”字。因此筆者和該老師都認為只能是這一個字,然而,有學生出乎意料回答出了另一個答案——“裝”。騙子為金銀財富裝模作樣欺騙皇帝,大臣為保住自己的地位裝模作樣欺騙君主和同僚,百姓為保住性命和不讓自己顯得太傻裝模作樣欺騙統治者及其他百姓。“裝”字和“騙”字一樣,同樣可以合理并赤裸裸地揭示這個國家所有人虛偽自私的本性,凸顯童言無忌背后誠信的可貴,將文章的主旨引導出來。只是該老師是按照“騙”字設計的課程內容,為了保證課堂的正常進行,只能將這一答案輕描淡寫略過,重新引導出“騙”字。事后評課時為此惋惜不已。
這也給筆者一個警示:語文是豐富多彩的,它不具有數學的“一是一,二是二,一加一只能也只會等于二”這樣冷冰冰的定式思維。一節真正的語文課應該流動而不斷生成。
二、細讀文本,挖掘文字背后的多重含義
之所以要強調細讀,是因為當前初中生所讀的課文大多以抒情類的散文、記敘文為主,這類文章背后,往往蘊藏著沉甸甸的分量,如果只停留于表面,不去細讀,去品味文字背后的多重含義,很容易錯漏大量信息,甚至造成對文本的誤讀。
某語文老師曾在其公開課中舉過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像“妹妹的臉紅得像紅蘋果”一句,如果我們的解讀只局限在妹妹的臉頰很紅潤這層含義上,那么“妹妹的臉紅得像猴屁股”這一句同樣適用。為什么不用后者呢?決定兩句本質上不同的,便是“紅蘋果”和“猴屁股”這兩個比喻帶來的附加含義。“紅蘋果”的香甜可口,賦予了妹妹美好可愛的特點,這是因為作者對于妹妹的喜愛之情,驅使他做出了這樣的比喻。而這層喜愛之情,就是需要我們語文老師帶領學生去捕捉的文本中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語文中其實很少有完全對等的字詞,每個含義相近的字詞背后都帶有不同的表意傾向,并與上下文語境息息相關。我們教學生解讀文本,其實是在教他們體會文字背后的細微差別,為什么這里要用這個詞,而不是另一個詞。這些詞到底好在哪里?
以《濟南的冬天》第三自然段為例,為什么不能把“樹尖上頂著一髻兒白花”中的“頂”字換成“覆蓋”兩字?在教學中我們就要循循善誘,帶領學生挖掘出“頂”這一字的精髓。讓學生領悟到,它除了和“覆蓋”一樣能夠表達雪在樹尖上這層含義外,還能夠突出積雪之小與矮松之挺拔,并引出下文“日本看護婦”的比喻。
文字的多重含義賦予了文本豐富的內涵,使文本解讀這一過程充滿了趣味性,解讀出來的答案更是精彩紛呈、個性十足。這無一不彰顯著語文的魅力。
三、適讀文本,取其精華,避免贅余
之所以要適讀文本,是因為每篇課文,或多或少都涉及章法結構、語言特色等諸多知識點,有些課文的主題和作者情感更是可以多元化解讀。由于課時的限制以及學生理解能力的差異,課堂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個細節都照顧到。這就要求老師在正式上課前務必根據文本內容確定教學重難點,控制延伸量和延伸度,真正以學生為本,制定合理的教學計劃。
語文教學始終離不開對于文本的解讀。但這解讀應該取文本之精華,去文本之贅余。教學中要鼓勵學生發散思維,深入挖掘,領悟精要;但更要適當適度,避免過分發散、牽強附會,更反對為深而深、標新立異、嘩眾取寵。
筆者在上《天凈·沙秋思》一課時,問學生“古道西風瘦馬”這一句中“瘦馬”的意象妙在何處。解讀關鍵應著眼于“瘦”字,用馬的消瘦,寫出詩人旅途中的奔波勞苦,從而暗示詩人凄惻的心境和對家鄉的思念。然而有學生卻這樣解讀:詩人名叫馬致遠,因此“瘦馬”實際上暗指詩人自己,馬致遠就是古道西風這幅畫卷里奔波的老馬。
因姓馬而將詩人和瘦馬這一意象聯系起來,將兩者等同,這便屬于“強讀”的范疇。
為了嘲笑語文對于文本的過分解讀,網上還流行過這樣幾個段子。從魯迅先生的“晚安!”一句中,語文老師可以解讀出“晚”字暗指社會的黑暗,“安”字折射出人民的麻木。“!”表達了魯迅先生對人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感。從“吃飯”兩個字背后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人吃人的狀態,以及對人民吃不了飽飯的反諷,從而表現出魯迅先生憂國憂民的情懷。
從這些調侃可以看出,過分的解讀在將語文學科推向一個尷尬的地位。它使語文課變得可笑又可憎,也極易引發他人對語文這門學科的嘲笑與誤解。
參考文獻:
[1]駱文俊.文本解讀的適度性——以《老王》為例[J]教學月刊·中學版(教學參考),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