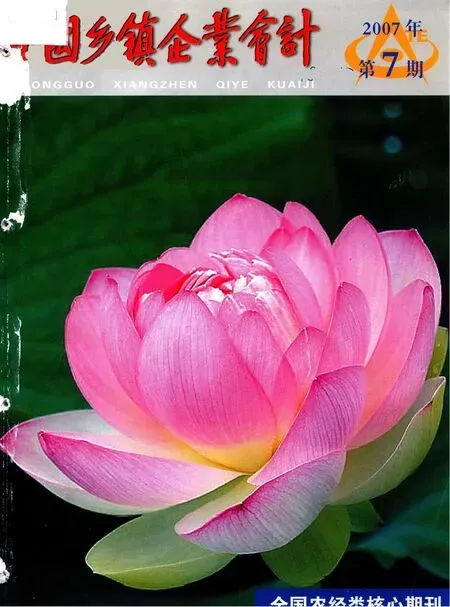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研究
林潤儀 唐 華 鄧縈悅 陳曉妍 劉新月
一、引言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民營高科技企業作為這一產業的領頭羊,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民營高科技企業創新投入中,政府補貼占據了十分重要的部分,并被普遍認為是促進科技型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然而已有研究文獻的樣本鮮少涉及民營高科技行業。因此,以民營高科技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具有的實際影響力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內容。
二、文獻綜述
通過梳理政府補貼、研發費用對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文獻發現,圍繞這一問題的研究呈現出了不同的結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政府補貼促進了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如,Tadahisa(2005)通過對223家日本高科技公司進行研究,發現政府補貼提升了企業研發績效。以德國制造業創新公司為樣本,Hussinge也發現政府補貼使得企業研發投入增加。唐清泉等(2009)在對創新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時發現政府補貼有利于企業研發效率的提升。王歡芳等(2018)發現政府直接補貼和間接補貼能有效促進新興企業R&D投入。
而有的學者認為政府補貼不僅不會促進企業的創新效率,反而會使其創新效率降低。Thomson以25個OECD國家數據為樣本,發現政府補貼無法提高企業研發投入。馮宗憲和王青發現政府投入和技術創新活動效率存在負相關關系。政府補貼干預企業研發,會破壞原有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對2009-2013年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龔立新等(2018)研究發現政府補貼難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效率。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兩者是不相關的。謝偉等(2008)的研究認為政府和企業重視研發會提高創新效率,然而對研發的投入并不會立刻就能在技術創新效率上得到體現。而在潘雄鋒等(2010)對中國工業企業進行的技術創新效率的研究并認為政府補貼對中國工業企業的創新效率影響不大。
綜上所述,國內外各學者基于本研究從多個視角采用了不同研究方法,且得出結論不一。這些已有綜述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角度。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與假設提出
本文根據《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中提到的八大領域,結合滬深A、B股中對證監會行業的劃分,篩選了醫藥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共五個行業中的民營企業作為樣本。剔除財務數據缺失的企業后,本文從Wind數據庫和SooPAT專利搜索網站中人工篩選了符合以上條件的2012-2016年的共計502家上市民營企業的面板數據,采用SFA方法進行模型構建,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檢驗各變量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R&DPa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企業的創新績效,sub表示企業對應時期獲得的政府補貼額,r&de表示企業對應時期獲得的研發費用額,X表示系列的控制變量。
政府補貼一直是推動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對政府補貼有效性的研究是對這一因素價值的真正衡量。研發費用對企業績效的有效性研究有助于衡量研發費用這一因素的真正價。政府補貼和研發費用的交互作用能夠體現出這兩個因素在企業績效方面所體現的真正的價值。在往年學者的研究中,莊婉婷,李芳鳳,李安蘭等得出企業R&D投入在政府補貼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部分通過企業R&D起投入作用的結論;景曼詩,尹夏楠認為政府補貼和研發費用的交互作用對企業績效產生了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交互作用,對企業績效產生了較小程度的負向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政府補貼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假設2:研發費用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
假設3:政府補貼和研發費用的交互作用能夠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
(二)變量解釋
現有文獻常采用專利申請數量作為高科技企業創新活動產出的主要衡量指標,如李磊(2008),也有采用企業的研發費用和研發人員作為投入變量,如學者盧方元、李彥龍(2016)。本文采用企業的研發費用作為投入變量。此外,本文采用了被目前相關研究使用較多的控制變量,如公司規模、財務風險、運營能力及償債能力等,并挑選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指標,以對假設進行更深層次的論證。各變量的詳細定義,見表1。

表1主要變量的定義
(三)回歸分析
1.描述性統計。表2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變量的中位數和均值較為接近,表明樣本呈正態分布。同時對主要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負相關且不顯著;研發費用與企業創新績效正相關且在1%統計意義上顯著,說明研發費用對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明顯;總的來講,增加政府補貼并不能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

表2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2.實證回歸結果。表3顯示,單獨的政府補貼與企業的創新績效呈負相關且不顯著,而在其他因素影響下政府補貼與企業的創新績效呈負相關也不顯著。因此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不顯著,假設1未得到支持。這與前面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有些不同,于是我們考慮到整個數據樣本可能存在部分相關的關系。我們進一步分析各行業研發費用和企業創新績效,得出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研發費用與企業的創新績效最相關,這也印證了這一行業制造價值、科技含量、斥資投入高的特點;其次是以技術創新為發展原動力的醫藥制造業;最后是儀器儀表制造業,印證了此行業創新不足、“空心化”產業鏈不完善、穩定性不強等缺點。
結果表明,研發費用和政府補貼的交互項的系數不顯著,也即在不同研發費用的作用下,對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不顯著這一結果沒有實質影響,交互作用對企業績效產生了小程度的負向影響。再次證明假設1未得到支持,這說明政府補貼難以有效促進企業的創新績效,同時也推翻了假設3。根據以往文獻研究分析,政府補貼的無效可能主要是由于補貼過于統一,缺乏針對性;研發費用的無效是由于樣本中的企業有比較多的新創企業,或投入還未得到對應的創新產出,有一定的滯后成分;政府補貼和研發費用交互的無效主要是由于企業沒有將政府補貼用于研發投入,反而是用于維持經營獲利或填補報表的虧損漏洞。

表3政府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回歸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民營高科技上市企業進行數據分析,以企業的專利數量衡量企業的創新能力,探究政府補貼和企業研究費用是否對企業創新績效關系起積極作用。研究結果發現,政府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無顯著促進作用,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對企業創新績效未起顯著的積極作用,政府補貼和研發費用的交互作用對企業創新績效也未起顯著的促進作用。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完善補貼對象的選擇條件機制。政府應有針對性地進行補貼。根據不同企業在創新績效上的不同貢獻,相應進行同比的補貼(撥款、減稅等);第二,加強對政府補貼流向的監督。政府應出臺相關監督政策,使企業對補貼流向的信息進行披露,確保政府補貼最大程度地作用于企業的創新績效;第三,完善民營高科技企業的融資體制。包括增強對向中小高科技企業發放貸款的銀行的補貼力度;加快對科創板和注冊制融合方案的完善、試行和推廣步伐等。第四,企業應優化內部管理控制流程。對于將大部分政府補助用于填補運營虧損的企業,在投入研發費用時會更加謹慎,對研發活動進行嚴格的控制,從而降低創新產品的產出和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