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白薯和烀白薯
肖復興
在老北京,冬天里賣烤白薯永遠是一景。它確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了,便宜,又熱乎,常常屬于窮學生、打工族、小職員一類的人。他們手里拿著一塊烤白薯,既暖和了胃,也烤熱了手,迎著寒風走就有了勁兒。記得老舍先生在《駱駝祥子》里,寫到這種烤白薯,說是餓得跟癟臭蟲似的祥子一樣的窮人,和瘦得出了棱的狗,愛在賣烤白薯的攤子旁邊轉悠,那是為了吃點兒更便宜的皮和須子。
民國時,徐霞村先生寫《北平的巷頭小吃》,提到他吃烤白薯的情景。想那時他當然不會淪落到祥子的地步,他寫他吃烤白薯的味道時,才會那樣興奮甚至有點兒夸張地用了“肥、透、甜”三個字,真的是很傳神,特別是前兩個字,我是從來沒有聽說過誰會用“肥”和“透”來形容烤白薯的。
但還有一種白薯的吃法,今天已經見不著了,便是煮白薯。在街頭支起一口大鐵鍋,里面放上水,把洗干凈的白薯放進去煮,一直煮到把開水耗干。白薯里吸進了水分,非常的軟,甚至綿綿得成了一攤稀泥。白薯皮在滾開的水里浸泡,猶如貴妃出浴一般,已經被煮成一層紙一樣薄,呈明艷的朱紅色,渾身透亮,像穿著透視裝,里面的白薯肉,都能夠絲絲看得清清爽爽。
煮白薯的皮,遠比烤白薯的皮要漂亮,誘人。仿佛白薯經過水煮之后脫胎換骨一樣,就像眼下經過美容后的漂亮姐兒,須刮目相看。水對于白薯,似乎比火對于白薯要更適合,更能相得益彰,讓白薯從里到外的那樣可人。煮白薯的皮,有點兒像葡萄皮,包著里面的肉簡直就成了一兜蜜,一碰就破。因此,吃這種白薯,一定得用手心托著吃。大冬天站在街頭,小心翼翼地托著這樣一塊白薯,嘬起小嘴,嘬里面軟稀稀的白薯肉,那勁頭兒,只有和吃喝了蜜似的凍柿子有一拼。
老北京人又管煮白薯叫“烀白薯”。這個“烀”字是地地道道的北方詞兒,好像是專門為白薯的這種吃法量身訂制的。烀白薯對白薯的選擇,和烤白薯的選擇有區別,一定不能要那種干瓤的,要選麥茬兒白薯,或是做種子用的白薯秧子。老北京話講:處暑收薯,那時候的白薯是麥茬兒白薯,是早薯,收麥子后不久就可以收,這種白薯個兒小,瘦溜兒,皮薄,瓤兒軟,好煮,也甜。白薯秧子,是用來做種子用的,在老白薯上長出一截兒來,就掐下來埋在地里。這種白薯,也是個兒細,肉嫩,開鍋就熟。
當然,這兩種白薯,都便宜。烀白薯這玩意兒,是窮人吃的,比烤白薯還要便宜。我小時候,正趕上節糧度荒,每月糧食定量。家里有我和弟弟正長身體的半大小子,月月糧食不夠吃。只靠父親一人上班,日子過得拮據,不可能像院里有錢的人家去買議價糧或高價
點心吃。就去買白薯,回家烀著吃。那時候,入秋到冬天,糧店里常常會進很多白薯,要用糧票買,每斤糧票可以買五斤白薯。但是,每一次糧店里進白薯了,都會排隊排好多人,都是像我家一樣,提著筐,拿著麻袋,都希望買到白薯,回家烀著吃,可以飽一時的肚子。烀白薯,便是那時平民百姓的家常便飯,常常是一院子里,家家都飄出烀白薯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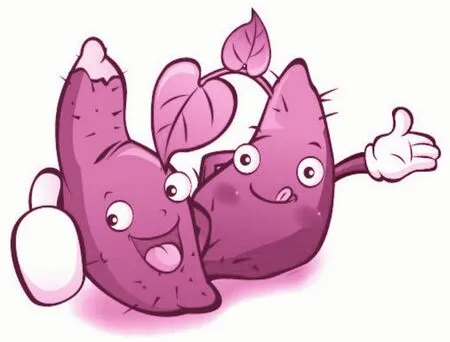
以前,賣烤白薯的一般吆喝:栗子味兒的,熱乎的!以當令的栗子相比附,無疑是高抬自己,再好的烤白薯,也是吃不出栗子味兒的。烀白薯,沒有這樣的攀龍附鳳,只好吆喝:帶蜜嘎巴兒的,軟乎的!他們吆喝的這個“蜜嘎巴兒”,指的是被水耗干掛在白薯皮上的那一層糖稀,對那些平常日子里連糖塊都難得吃到的孩子們來說,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
懂行的老北京人,最愛吃鍋底這種帶蜜嘎巴兒的烀白薯。這的確是烀白薯的上品。那樣的白薯因鍋底的水燒干讓白薯皮也被燒糊,便像熬糖一樣,把白薯肉里面的糖分也熬了出來。其肉便爛如泥,甜如蜜,常常會在白薯皮上掛一層黏糊糊的糖稀,結著嘎巴兒;吃起來,是鍋里其他白薯都沒有的味道,可以說是一鍋白薯濃縮的精華。一鍋白薯里就那么幾塊有嘎巴兒的,便有好這一口的人站在寒風中,程門立雪般專門等候著,一直等到一鍋白薯賣到尾聲,那幾塊鍋底的白薯終于水落石出般出現為止。民國有竹枝詞專門詠嘆:“應知味美惟鍋底,飽啖殘余未算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