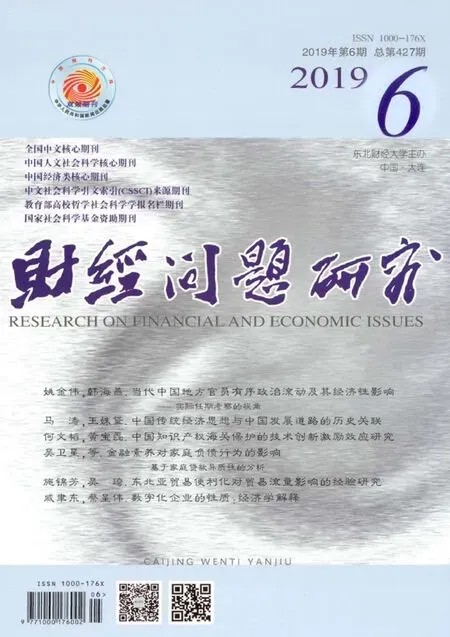專用資產投資與角色外利他行為:人情的作用
張 闖,殷丹丹
(東北財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問題的提出
營銷渠道中企業對自己發揮渠道功能的認知和其他成員對于它發揮渠道功能的角色預設(Prescription)稱為這一企業的角色定位或角色集(Role Set)[1]。合同約定或渠道成員間的共識和行為規范都有可能構成角色預設,因而在渠道中處于某一特定位置的企業,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能被其他企業所預見。企業之間的交易會由于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而出現許多合同約定之外的情況,一些企業會出于與合作伙伴建立長期而穩定的合作關系的目的,不僅履行合同約定的責任和義務,而且還愿意超出其角色預設主動作出有利于對方的行為,這種行為被稱為組織間的角色外利他行為(Interorganizational Extra-Role Altruism Behavior)[2]。
角色外利他行為有助于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帶來的經營風險,提高己方的聲譽、合作雙方的經營效率與績效[3-4]。此前,學術界主要關注組織內部員工、群體的角色外利他行為。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組織間的角色外利他行為,但相對于渠道成員角色內行為而言,渠道成員的角色外利他行為得到的關注較少[4]。圍繞這一問題,現有研究發現,企業間合作的氛圍、采購策略、轉換成本、合同的詳盡程度[4]、合同包容性、程序公平、組織間信任[3]、情感性承諾、規范性承諾[5]、企業間共享的價值觀念[6]、依賴、分配公平[7]、關系規范[8]等因素對角色外利他行為有促進作用,而算計性承諾則會抑制合作企業的角色外利他行為[5]。在作用結果方面,現有研究主要探討了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對雙方績效的影響機制,認為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有利于提高合作伙伴的關系利益[4]、渠道績效[3]以及本企業績效[8]。同時,它也能夠有效抑制供應商的投機行為,促進供應商針對合作關系投入交易專有資產[9]。這些研究雖然有助于學者了解跨組織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前因和影響后果,指導企業制定渠道策略,促進合作企業的角色外利他行為,提高合作雙方的企業績效,但仍有一些關鍵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
根據渠道關系研究的政治經濟經典分析框架[10],渠道關系包括經濟與社會和政治兩個維度,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對渠道成員的行為與渠道關系的作用結果產生影響。現有文獻雖然探討了諸多渠道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要素,但卻并未將上述兩個維度同時納入研究框架,從而留下了有待彌補的理論缺口。本文以渠道關系政治經濟分析框架為基礎,遵循渠道行為理論研究的基本范式,分別從交易成本理論和中國本土社會心理學理論兩個視角出發,關注渠道成員專用資產投資以及渠道成員之間的人情要素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以拓展和深化現有研究文獻。
首先,在渠道關系的經濟維度,本文關注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的作用。專用資產投資指的是企業針對某一特定交易伙伴或交易關系所作出的高度專業化的持久性投資[11]。經銷商投入的專用資產是否會促進其對供應商實施角色外利他行為?現有文獻對這一問題并沒有給出充分的回答。Mo等[12]研究了知識性專用資產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認為以知識為基礎的專用資產投資對角色外利他行為會有促進作用,但實證研究結果并沒有支持這一假設。根據交易成本理論,專用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類,知識性專用資產有別于設備、工具這類有形資產,它具有低持久性和更快速失去價值的特性。因此,在營銷渠道情境中,只考慮無形資產投資的影響是不全面的,有必要綜合考慮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這兩方面專用資產投資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效果。本文綜合考量了有形和無形的專用資產投資對渠道成員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這將會深化和拓展現有研究。
其次,渠道成員的行為還會受到若干社會要素,尤其是渠道關系所在文化情境的社會要素的影響,而現有文獻對這一問題還缺少足夠的關注。在中國這樣一個情理社會中,跨組織的私人關系被認為是影響渠道行為的一個關鍵因素。王勇[9]雖然探討了跨組織人際關系對渠道成員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但卻是將跨組織人際關系作為一個整體變量來進行研究。私人關系是由不同要素構成的文化現象,是一個復雜的和多維的構念,所以有必要將其作為一個多維構念,細致探討不同維度的不同作用。人情是中國社會中私人關系的一個核心要素[13],一些研究認為可以將其作為中國社會中企業間交易的關系治理機制[14],但其對渠道成員角色外利他行為的作用還沒有得到關注。通過關注人情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將會深化和拓展有關私人關系對角色外利他行為影響的研究文獻。
最后,現有研究缺乏對渠道關系中經濟與社會文化要素對渠道成員角色外利他行為交互影響的關注。本文以供應商和經銷商構成的渠道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營銷渠道政治經濟分析框架為基礎,將渠道關系的經濟與社會要素同時納入研究框架,并進一步探討了二者交互作用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在Stern和Reve[10]的營銷渠道政治經濟比較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更為完整的渠道角色外利他行為影響要素的研究框架,彌補了現有理論缺口,豐富了渠道角色外利他行為的理論研究。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角色外利他行為
Katz[15]提出“基于角色的業績與創造性、自發行為的區別”,指出超出明確角色要求的自主、自發行為頗具重要性,“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ERB)的概念由此誕生。Katz和Kahn[16]又區分了角色內行為(In-Role Behavior)與自發行為(Spontaneous Behavior)的不同,指出組織的有效運作以及組織效能的提升不僅需要員工完成自己的工作內容,還需要作出一定的角色外行為。Bateman和Organ[17]根據Katz[15]的觀點,將這種自發行為定義為“公民行為”(Citizenship Behavior),認為公民行為是沒有正式工作說明但為組織所需要的行為。Organ[18]正式提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能夠促進組織功能的有效性且未被報酬體系所明確和直接規定的一種員工自覺、自愿行為。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Van Dyne和Lepine[19]將角色外行為定義為自由的、超出角色期望的、對組織有益或者希望對組織有益的行為。一般情況下,如不做特別說明,角色外行為指建設性的或積極的角色外行為[19],即角色外利他行為。
Wuyts[4]認為,角色外利他行為同樣也會發生在跨組織層面,并提出“企業間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Autry等[2]將這一概念細化,指出企業間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利他、容忍、忠誠、服從、責任心和進步等方面。在渠道中,組織間角色外利他行為特指企業超出正式(合同約定)或非正式(渠道成員間的共識和規范)的角色定位或角色預設,自覺自愿地幫助渠道合作伙伴解決問題的行為[2-4]。角色外利他行為在渠道合作中普遍存在,如經銷商主動為一家供應商提供好的展位,對本企業員工進行專門的針對該供應商產品的培訓等。
角色外利他行為與基于關系規范(Relational Norms)的關系行為有重疊部分但不完全相同。關系行為要求雙方互惠互利。如果一方違反了關系規范會遭到譴責,同時影響雙方關系的進一步發展。角色外利他行為是一方超出對方期望的善意行為,主觀意愿是有利于對方的,這并不是企業基于角色定位或職責要求而作出的行為。如果企業不作為并不會受到譴責或法律制裁,主動做出角色外利他行為的企業可能得到隱形回報,如對方對己方更高程度的信任、承諾或同樣作出角色外利他行為[2-4]。
近年來,學術界已經意識到組織間角色外利他行為對組織的重要性,主要探討了其前因和后果。在前因方面,學者們主要討論了治理機制和交易特征等因素的影響作用。Li[3]從國際營銷渠道中戰略層次研究角色外行為,認為合同詳盡性、信任和程序公平均可以促進組織間角色外利他行為。張闖等[8]認為合同詳盡性和信任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也是顯著正向的。王勇等[20]發現合同詳盡性和合同監督通過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促進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Mo等[12]以IT專業服務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以知識為基礎的專用資產投資會導致不同的行為取向。如果企業感知到被供應商排除在渠道圈子之外(Out-of-the-Channel-Loop Perceptions),知識性專用資產投資對機會主義行為和角色外利他行為的正向影響作用都會增強。同時,企業的成就導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在其中起到不同的調節作用。此外,現有研究還發現,供應商與經銷商雙方的合作氛圍、經銷商的多方采購策略、供應商的轉換成本[4]、企業間的共享價值觀[6]、情感性承諾和規范性承諾[5]以及依賴和公平[20]均會顯著影響渠道成員角色外行為。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指導企業制定渠道管理策略,促進合作企業角色外利他行為,進而提高合作雙方的企業績效。
在角色外利他行為后果方面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通過建模和實證檢驗探究角色外利他行為對渠道績效和渠道效率的影響。Wuyts[4]指出供應商采取角色外利他行為會提高經銷商的關系利益。Li[3]發現角色外利他行為可以促進合作關系質量和渠道績效。張闖等[8]認為經銷商實施角色外利他行為還會提升其自身績效。這些研究進一步明確了角色外利他行為在渠道合作中的重要意義,為研究其前因提供了必要和重要依據。
(二)專用資產投資與角色外利他行為
“專用資產投資”的概念源于交易成本理論,指企業針對某一特定交易伙伴或交易關系所作出的高度專業化持久性投資。它具有更大的創造價值能力,能夠為渠道成員帶來更多收益,但在特定交易關系外卻會失去價值或大幅度貶值,使投資方遭受巨大的沉沒成本[11]。專用資產通常包括專門的設備和設施以及專門的知識和經驗等,在供應商—經銷商關系中可能會體現為人力、物料和地點等。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專用資產投資會影響渠道成員的行為。一方面,專項投資會增加企業的轉換成本,使該企業被鎖定在這一關系中。交易關系一旦終止,它的沉沒成本以及由專用資產產生的將來收益都將失去,且資產專用性越強,在其他用途上的價值越低,這就提高了轉換合作者的成本和關系退出壁壘。此時,投資者會形成自我實施的單邊協議,產生持續交易的自我約束。為了不使已投入的專用資產因合作中斷而遭受損失,投資方會盡力維持交易關系,從而也更愿意在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采取更為靈活的解決辦法。經銷商對專用資產投資十分謹慎,一旦投資被鎖定在關系中,因而期望進一步維持交易關系,愿意主動維護渠道關系,作出有利于對方的積極行為,如角色外利他行為,來保護專用資產投資,避免已投入的專用資產遭受損失。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1:經銷商針對其供應商投入的專用資產越多,就越傾向于針對該供應商從事角色外利他行為。
(三)人情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
私人關系也稱人際關系,指的是在現實社會的活動中,通過交往而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心理關系(包括認知、情感)和相應的行為表現,它被認為是雙方基于互惠互利的一種友誼關系或社會聯系。在營銷渠道中,私人關系是一個關鍵的基礎性變量。在考察中國的營銷渠道行為時就不能忽視私人關系的作用,否則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或解釋中國營銷渠道中渠道成員的行為。
私人關系的內涵非常豐富,盡管目前學者們對私人關系的定義取得了一致意見,但在實證研究操作中對私人關系的概念化和測量則呈現出高度的差異性。相關研究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采用社會資本觀點將私人關系定義為商業聯系和政治聯系。二是從中國本土視角出發,這里又有兩種不同的操作方式,一種是將人情、面子、感情和信任等要素作為私人關系的維度將其作為一個二階變量;另一種是將私人關系看做是一個單維變量,從整體上測量。從西方理論視角出發,用社會資本理論來定義和操作私人關系會帶來水土不服;而將私人關系作為單維變量則無法區分不同構成要素的作用,也會造成大量信息損失,無法理解私人關系中的豐富內涵。因此,從中國本土文化角度來研究營銷渠道中私人關系作用可以最大可能地還原其在中國文化中的作用。與此同時,關注私人關系的不同構成維度(如人情、感情和面子等)可以更為深刻地揭示私人關系的作用機制。
人情被認為是關系的核心維度之一[13]。它是人的相處之道,同時還是人際交往的一種工具,是人與人在社會交易過程中饋贈給對方的一種資源,凝聚著互惠的規則和長期互利的愿景。人情是中國社會中人際交往中人們應當遵循的一種社會規范,即人情法則。雖然在研究中國營銷渠道關系的文獻中常常提及人情,但卻少有研究實證檢驗人情的作用[21-14]。筆者尚未發現檢驗人情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直接影響,以及對專用資產投資與角色外利他行為關系調節作用的文獻。人情是人的相處之道,學者們一般將人情分為同情和互惠兩個方面[13],這兩個方面都會促進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
首先,同情可以促進交易雙方更多地從對方角度思考問題,努力理解對方的期望和目標。在中國社會中,知曉人情的人更會換位思考,從而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投其所好、避其所惡[13]。反之,對別人的不幸毫無同情心,不愿意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的人會被認為不懂人情,沒有人情味兒。在渠道關系中,如果一方能很好地理解合作伙伴的價值觀念、目標和戰略,并且愿意在對方需要的時候給予幫助,這樣的企業也被稱為是通曉人情的。這樣的企業更愿意站在對方角度理解其目標和戰略選擇,從而主動調整己方的行為,與渠道伙伴保持一致。因此,如果經銷商一方是通曉人情的,它會主動作出有利于對方的行為。當一方遇到困難時,另一方會基于同情和對未來獲得回報甚至超額回報的良好預期,作出超出自身角色預設的行為,幫助其渡過難關。
其次,作為企業間交易關系的一個維度,互惠反映了交易關系中的人情法則。在中國社會中,欠了對方人情要在適當時候還人情,如果該還人情的時候沒有還,雙方關系會因此受到負面影響,甚至交惡[13]。企業間在進行交易往來時也遵循著這種人情法則,如果交易雙方互惠程度較高,那么雙方更愿意遵循平等的、同步化的補償交易[21]。因此,在渠道關系中,供應商與經銷商間存在著高水平的人情往來,雙方就會更愿意為了保持和提升合作關系而為對方提供幫助。當經銷商認為供應商實力雄厚或擁有其所需要的重要資源時,經銷商會通過“送人情”的方式努力去維持和發展雙方關系,主動作出有利于對方的事情。人情會降低經銷商與供應商合作過程中過于看重自身損益的功利趨向,增強他與供應商之間互惠和合作的意愿,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促進作用主要是基于雙方的利益交換長期而言是對等的。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2:渠道關系中的人情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人情的調節作用
人情除了對角色外利他行為有直接影響外,還對專用資產投資與角色外利他行為的關系產生調節作用,即專用資產投資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可能有賴于關系中人情的作用。
在擁有較高水平人情交換的渠道關系中,雙方合作的意愿都很高,此時經銷商投入專用資產是基于與合作伙伴的一種互惠的期望。經銷商愿意給予供應商更多的幫助,實施更多的角色外利他行為,相信供應商會在未來以某種形式(如不利用經銷商的專用資產做投機行為)反饋回來,這就加強了經銷商對角色外利他行為可能帶來維護自己沉沒成本的效果的期望。相反,當企業感覺雙方間人情淡漠、互惠程度低時,平等以及回報的預期變得不再那么重要,交易關系中的一方即使采取角色外利他行為也可能不會得到對方的積極回應。此時即便經銷商已經投入專用資產,也會因為對方對合作的低意愿而不愿意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只是做好合同規定內的事情。由此,筆者提出以下假設:
H3:經銷商與供應商的人情往來越密切,越會增加由專用資產投資帶來的角色外利他行為。
本文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其中,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人情為前因變量,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為結果變量。此外,人情還調節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與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分析
(一)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文以品牌潔具經銷商對供應商的角色外利他行為為研究對象,從經銷商一方收集數據,研究品牌潔具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在以代理渠道為主的潔具渠道模式中,制造商一般不允許經銷商代理其他品牌,并會統一制定分銷政策。
數據收集采取面對面訪談形式,訪問對象包括大連市場上的潔具經銷商的老板、經理、店長和采購經理等熟悉情況的管理人員。一共發出175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158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0.29%。其中,股份制企業約占38%,外資企業約占27%,還包括一些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合資企業等。抽樣調查的經銷商與其合作伙伴間的合作年限在2—5年的企業占總體的44%,約有28%超過5年,24%在1—2年之間,其余合作不到1年。
(二)問卷與變量測量
本文的調查問卷有5頁,大概需要15—20分鐘完成。為了提升受訪者的響應率和數據質量,筆者為受訪者提供了一份價值10元左右的小禮品。在導語部分,筆者用黑體字注明答題要求,量表均來自前人研究中使用過的成熟量表。對于英文量表,筆者采用翻譯和回翻的程序,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根據研究對象具體情況對其作了相應的修改。問卷均使用5點李克特量表形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人情的測量題項來自于Barnes等[22],包含6個題項;專用資產投資的測量題項來自于Ping[23],包含5個題項;組織間角色外利他行為的測量題項來自于Wuyts[4],包含4個題項。
本文同時控制了一些可能會對結果產生影響的變量。第一,控制了渠道關系中的依賴總量和相對依賴。供應商依賴和經銷商依賴量表來自Palmatier等[24]的量表,均包含3個題項。本文用供應商依賴和經銷商依賴之和衡量企業間總依賴水平,用經銷商依賴減去供應商依賴的差衡量經銷商相對依賴水平。第二,控制了渠道關系中的合作氛圍,本文采用的量表來自Palmatier等[24]的量表,包含3個題項。第三,控制了企業間合作年限,用經銷商與合作企業合作年限來測量。
(三)量表信度與效度檢驗
本文應用基于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技術的Smart PLS3.0軟件進行分析,應用該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是PLS對樣本規模和分布具有較低的要求,根據樣本量10倍于輸入路徑的準則,本研究的樣本量符合此要求。二是PLS 結合了主成分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的技術優點,尤其適用于理論知識比較缺乏以及以預測應用為目的的研究情境。由于針對人情影響機制的研究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理論根據尚不完善,因而本文適用PLS方法。
應用SmartPLS進行分析,通過Cronbach系數檢驗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數據顯示,本文所用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超過了0.700,均高于0.500的最低可接受水平。同時,各變量的組合信度(CR)都大于0.700,說明量表內部一致性較高,具有較高的信度。效度方面,所有變量的因子載荷均超過0.500的最低可接受水平,變量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均大于0.500,說明變量具有較好的聚斂效度。判別效度指判斷一個概念與另一個概念的差異程度,通過比較AVE值的平方根,看它是否大于其他潛變量的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如果是大于關系,則表明判別效度存在,也即變量間存在明顯差異。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
注:*表示 p<0.001。
表2是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從表2可以看出,對角線上的數字為各變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對角線下該變量與其他變量相關系數的絕對值,說明變量間具有良好的判別效度。

表2 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下同。
(四)回歸結果分析

在調節效應檢驗模型中,本文首先對自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然后再構造交叉項,以避免多重共線性影響。為了檢驗人情的調節作用,本文依次將依賴總量、相對依賴、合作年限、合作氛圍,專用資產投資,人情,專用資產投資×人情放入模型(1)、模型(2)、模型(4)和模型(5),角色外利他行為為因變量。上述模型的F值均顯著不為0。同時,在模型(2)、模型(4)和模型(5)中,專用資產投資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專用資產投資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型(5)中,專用資產投資×人情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人情對專用資產投資與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起負向調節作用,這與H3相反。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經銷商會將角色外利他行為作為保護其專用資產投資的一種機制,即通過采取角色外利他行為來維護合作關系。當合作關系中的人情交換處于高水平時,人情為經銷商專用資產提供了一種保護機制,即關系雙方都會本著長期導向來對待對方。此時,經銷商會認為其針對合作伙伴的投入是有保障的,它所承擔的風險(沉沒成本)更小。經銷商對專用資產投資可能遭受損失的擔心被削弱了,從而其被迫作出利他行為的動機也就被削弱了。即在高水平的人情關系中,角色外利他行為可能被內化為人情法則的一部分,尤其是當經銷商與供應商處于長期導向的關系中時更是如此。因此,經銷商出于保護專用資產而采取的角色外利他行為也就減少了。

表3 專用資產投資、人情和角色外利他行為回歸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研究結論及啟示
本文以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研究對象,探討了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人情與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和人情均對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人情負向調節經銷商專用資產投資與經銷商角色外利他行為的關系。本文的研究結論可以為企業的渠道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第一,人情在中國商業社會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營銷渠道中,企業在進行交易時除了有商業交易外,還有人情交換,前者是商業性的,后者是社會性的。企業管理者應遵循人情法則,鼓勵邊界人員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密切的人情往來,促進角色外利他行為,也有利于渠道關系的穩定。第二,經銷商對合作伙伴投入專用資產后應主動作出角色外利他行為以獲得更多的回報。此時,雙方員工間密切的人情往來會弱化上述關系,企業管理者應適時進行人員調動,避免人情帶來的負面影響。總之,企業在處理渠道關系時需要平衡專用資產投資與人情之間的關系,促進雙方長久合作關系的發展。
(二)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進:第一,本文使用的是單邊截面調查數據,僅從經銷商方面測量了相關變量,這可能會對研究結論帶來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同時從經銷商和供應商收集配對數據,以避免同源偏差的影響,或者收集縱向數據,對人情與角色外利他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第二,根據復合治理理論,渠道關系中往往同時存在多種治理機制影響渠道成員的行為和渠道績效,不同治理機制之間存在不同的相互作用機制。本文專用資產投資是正式的,人情是非正式的,二者的交互作用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也可能會受到若干情境要素的影響。未來的研究可將更多的情境要素納入分析框架,進一步檢驗專用資產投入與人情交互作用對角色外利他行為的影響。第三,本文仍將角色外利他行為作為一個整體變量來研究,渠道關系中的角色外利他行為可能存在多種類型,有必要對重要的、具體的渠道角色外利他行為展開研究。第四,本文只考察了私人關系中的人情要素,而沒有考慮其他關鍵要素,如感情、面子和信任等。還需進一步挖掘和測量其他可代表中國文化的有價值的變量,以更好地拓展和深化渠道治理的本土化研究,指導渠道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