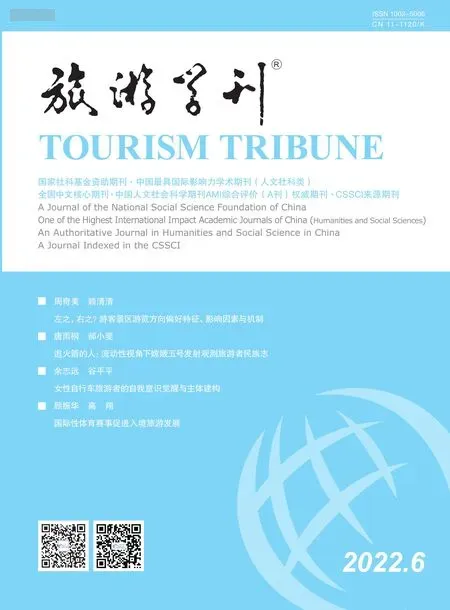大眾旅游現象研究綜述與詮釋
董培海 李慶雷 李偉
[摘 要]MacCannell開創的旅游現代性研究范式,通過對大眾旅游現象的關注,極大地推動了旅游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然而,這一研究范式在賦予旅游現象和旅游研究普遍性意義的同時,很大程度上又忽視了對大眾旅游之外其他旅游現象和行為的描述與關注。旅游被視為一種均質的現象,由此也導致了旅游現象的社會學研究失去了應有的學術張力和想象力。該研究以旅游現代性研究為切入點,在綜述國內外大眾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剖析大眾旅游的概念、特征,并對大眾旅游的發生及發展予以探討,以期通過對大眾旅游的闡釋,以之為透鏡,拓寬旅游現象認知的視野,推動旅游現代性研究范式的擴展,進而對旅游基礎理論的研究有所啟示。
[關鍵詞]大眾旅游;旅游吸引物泛化;娛樂;大眾旅游趨向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2-5006(2019)06-0135-10
Doi: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6.017
引 言
20世紀60-70年代,Boorstin和MacCannell關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爭論受到廣泛關注,成為社會學領域關于旅游研究的最大熱點。在這場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學術爭鳴中,MacCannell無疑占據了上風,面對勢如破竹的大眾旅游現象,Boorstin對于“旅行藝術的失落”(the lost art of travel)和旅游是“偽事件”(pseudo-events)的感嘆更像是一種無病呻吟于歷史變遷的哀婉情調。對于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現象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MacCannell嘗試從現代性的背景下來理解旅游,將旅游視為現代性背景下的一種朝圣。他的研究激起了英語世界對于旅游社會學的深入關注,進而從大眾旅游現象的關注中,開辟了旅游研究的新范式。細數20世紀70年代以來旅游社會學和旅游人類學的繁榮與理論原創,莫不與其旅游現代性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一研究范式也主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旅游社會學20余年的發展。在社會學中,旅游成為了現代人的一種隱喻(metaphor),而追求“前現代世界”(pre-modern world)的差異性被認為是現代性治愈的一種手段。正如Aramberri所說:“要將當今的大眾旅游與其之前的形式區別開來,一個‘現代的前綴不可或缺,因為在今天大眾旅游與現代性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然而,旅游現代性分析范式在賦予旅游現象和旅游研究普遍性意義的同時,卻又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大眾旅游之外其他旅游現象和行為的描述和關注。旅游被視為一種均質的現象,由此也導致了旅游現象的社會學研究失去了應有的學術張力和想象力,理論研究止步不前。繼20世紀90年代初Urry的旅游凝視(tourist gaze)理論之后,旅游社會學乃至整個旅游學研究再無重大的理論原創。
回顧國外旅游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西方旅游社會文化研究的話語體系中,對于旅游現象的認識和研究一直存在精英旅游(elite travel)和大眾旅游(mass tourism)兩種不同維度。不管是Gray對漫游癖( wanderlust)旅游和享受癖(sunlust)旅游,Cohen對非制度化旅游和制度化旅游,Urry對浪漫主義凝視旅游(romantic gaze at tourism)和集體凝視旅游( collective gaze at tourism)的區分,還是王寧旅游“真實性”研究中對客觀主義真實( objectiveauthenticity)和存在主義真實(existentialauthenticity)的探討,相關研究莫不如此。現代大眾旅游的成功之處在于其通過產業化和制度化的安排,滿足了現代人對于天堂的追求與想像,使旅游成為一種全球的愿景和深刻影響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力量。毫無疑問,大眾旅游已經成為旅游研究中最為宏大和值得關注的一種現象和事實。然而,對于大眾旅游現象的研究和關注亦不能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在紛繁復雜的旅游現象世界中,朝圣旅游(pilgrim tourism)、背包客旅游(backpackingtourism)、黑色旅游(black tourism)、靈性旅游( spiritual tourism)、志愿者旅游(volunteer tourism)、善行旅游(good tourism)、扶貧旅游(pro-poor tourism)等均不能簡單地納入大眾旅游的范疇。
問題意識是從事旅游學術研究的基礎,是旅游學術創造活動的精、氣、魂之所在,是旅游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的一種知性、理性,更是一種悟性。問題意識源于理論與經驗之間的張力,旅游學術研究的深化不僅高度依賴于旅游基礎理論層面的探索和創新,同時也離不開對錯綜復雜的各種旅游現象的深描和解釋,二者唇齒相依。本研究在綜合國內外大眾旅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剖析大眾旅游的概念、特征,并對大眾旅游的發生與發展進行簡要梳理,研究聚焦于大眾旅游現象的探討又不完全囿于此,而希冀于通過對大眾旅游的闡釋,以之為透鏡,拓寬旅游現象認知的視野,進而能對旅游基礎理論的研究有所裨益。
1 何為大眾旅游
1.1 大眾旅游釋義
在各種旅游學術研究乃至普通的報刊和新聞媒體宣傳中,大眾旅游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匯。但是,在中外、不同學科、不同語境下使用大眾旅游,其范疇所指卻有所差別。從嚴謹的學術層面對大眾旅游的探討,要追溯至歷史學家Boorstin在1962年出版的《鏡像:美國偽事件導覽》(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一書中,在“旅行者到旅游者:旅行藝術的失落”一章,面對“如日中天”的大眾旅游發展勢頭,Boorstin將大眾旅游( the mass)稱為是旅游部門所組織的一種消費形式( governed by the agents of tourism),在大眾旅游中,旅游者與景觀之間處于一種隔離狀態。對于Boorstin所描述的大眾旅游的組織化(organized)特征,以色列社會學家Cohen用“環境泡”(environmentalbubble)的概念來予以形象的概括,“旅游者在導游、空調大巴、飯店集團、旅行社的安排下,透過自己熟悉的環境去觀察和體驗他者的地方與文化。旅游被打包后以標準化的方式來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和出售”。Nunez和Aramberri都與Boorstin持相同的觀點,他們將大眾旅游看作是與精英旅游(行)(elite tourism/ elite travel)相對的一種旅游形式。另外一些研究者則認為,大眾旅游是一種傳統的( conventional)旅游形式,其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影響,必將為新的(new)、可替代(alternative)的旅游形式所取代。然而,正如Mustonen所調侃的:“研究者都在強調要重新尋找大眾旅游的替代,卻很少有人對其進行清晰的界定”。相較而言,在這些研究者中,Poon對大眾旅游的界定可能是最為系統和全面的,他認為“大眾旅游是以固定的價格、標準化的服務、大批量銷售給大眾顧客的包價旅游”,大眾旅游以大眾化(mass)、標準化(standardized)、包價(packaged)為特征。此外,還有一部分研究者從“mass”的字面意義,即人口數量特征上來解讀“大眾旅游”。Boissevain和Selwyn就認為大量旅游者去旅游目的地度假,這種穩定的游客流動現象就是大眾旅游。Youell認為大眾旅游是出于閑暇和商務目的而產生的大規模的客流。英國社會學家Sharply通過綜合前人的研究,認為可以從3個層面來理解大眾旅游:
(1)大眾旅游是一種獨特的被制造、營銷和出售的旅游產品類型。
(2)大眾旅游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而大眾旅游者是指那些追求在一些人看來屬于最低級旅游共同點的人。
(3)大眾旅游是指與特權階層的少數人相對的,生活在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中的大眾所能享受的旅游。在Sharply看來,大眾旅游不僅是一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同時也是一種表征為大規模人口移動的地理現象。
相較而言,國內學者對大眾旅游的概念解析則非常薄弱。張凌云在綜合考察了國外大眾旅游相關研究成果后,提出“大眾旅游是指由于環境和條件的改善以及休閑需求的增加所產生的大規模的旅游客流”。王興斌說:“大眾旅游就是大眾都去旅游”。在國內旅游學術研究語境中,提及大眾旅游強調的往往是“人數”的概念。這不禁會讓我們質疑:“多少人或多大規模比重”的旅游才能稱之為“大眾旅游”?在西方學術研究中與中文語義“大眾”對應的有“popular”和“mass”兩種表達,且鮮有研究者將其等同于“數”的概念,而更多地強調其“質”的特征。Defleur和Rockeach在《大眾傳播學理論》一書界定“大眾社會”時就強調:“大眾社會的概念不等同于數量上的大型社會,大眾社會指的是個人同社會秩序的關系”。Gasset也說:“不能把大眾簡單理解或主要理解為勞動階級,大眾是平均的人(the average man)”。大眾旅游作為現代性背景下席卷全球的一種“社會事實”,涉及了規模空前的人口流動,然而,這只能作為大眾旅游的表象形式,過度強調大眾旅游的人口特征,無疑是簡單而粗暴的,人口數量本身并不能為大眾旅游提供一種衡量和描述的尺度,無益于增進大眾旅游現象的認識和研究。
1.2 大眾旅游的面相
事實上,“大眾”一詞在西方研究的話語體系中本身即“不受待見”。Le Bon把大眾稱為是一群“烏合之眾”,Moscovici則以“群氓”稱之,Riesman把大眾看作是“孤獨的人群”。國外旅游研究者對大眾旅游的理解同樣充斥著貶義,基于對大眾旅游的不同界定,我們可以將其大致區分為兩類: 一類以Poon對大眾旅游的定義為基礎,研究者多為地理學、經濟學和環境科學背景,他們從宏觀產業層面強調大眾旅游所帶來的諸如旅游活動組織的無序化、社區發展不平衡以及環境破壞等消極影響,強調大眾旅游亟須以新的旅游形式替代,在他們看來,替代性旅游、生態旅游、軟旅游(softtourism)、負責任旅游與綠色旅游作為可持續旅游的重要形式無疑是更佳的選擇。與此同時,鑒于志愿者旅游、扶貧旅游、善行旅游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普世價值,它們也成為了大眾旅游的詬病者們所倡導的旅游方式。
另一類研究則繼承和延續了Boorstin對大眾旅游的看法,基于社會學和文化學的視角,他們以旅游者體驗為切入點,從微觀層面剖析大眾旅游的局限性。在他們的研究中,大眾旅游往往與膚淺、低俗、狂熱與無約束相聯系。如,Culler將現代大眾旅游者稱為“符號大軍”,他們對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的意義不求甚解,而僅僅滿足于旅游符號的表面滑行。Ritzer和Liska將大眾旅游稱為“迪斯尼化的旅游”(McDisneyization tourism),旅游者被分類、組群然后打包,集中運送到目的地,一切都被預先安排好并像工業產品一樣在流水線上不斷生產。Urry也說大眾旅游就是一個收集照片、收集符號的過程,旅游凝視就是某特定景點意義符號的生產與消費。
由于認知角度的不同,提及大眾旅游的時間緣起,研究者之間也存在較大分異。Poon認為大眾旅游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Boissevain和Selwyn認為大眾旅游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工業化國家,Graburn認為大眾旅游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30]83,Sharply說大眾旅游是20世紀晚期的特征,Urry則認為大眾旅游起源于19世紀歐洲的溫泉療養和海濱度假。大家的觀點莫衷一是,具體到各個國家的大眾旅游起源就更是眾口莫辯。學科立場和學術視角的不同,導致了研究者們對大眾旅游的認識始終存在一定差異,然而從眾說紛紜的前人研究中,采用歸納的邏輯,求同存異,我們也可以總結出大眾旅游在以下5個方面的共性特征和表現:
(1)人口特征。現代大眾旅游涉及歷史空前的人員流動,正如Nash強調的:“正是鑒于涉及的人口數量上的絕對規模優勢,研究者們傾向于將現代的大眾旅游看作是所有旅游形式的雛形(as a modelfor all tourism)”。大眾旅游與人口的數量和階層結構密切相關,其消極效應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空間集聚關聯在一起。
(2)技術特征。技術的發展不僅為現代大眾旅游提供了重要的通行條件,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使人們得以從工作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并開展常態化的旅游。
(3)產業特征。大眾旅游通過對旅游吸引物、飯店、交通要素等的組織,將旅游以“包價”(package)的、標準化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從而提供物美價廉、安全可靠的旅游產品和服務,使旅游由特定階層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變成普通大眾所共享的生活經驗。
(4)社會結構特征。工業革命不僅促進了中產階層的壯大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伴隨著工業化所帶來的異化、失范和工作條件的程式化,生態環境的劣質化,人際關系的淡漠化等,更是成為人們對現代性的存在條件下不滿與怨恨的社會原因。大眾旅游成為現代性所固有的結構性“好惡交織”的反映與體現。
(5)娛樂特征。現代大眾旅游是以觀光為基礎的休閑娛樂,大眾旅游者是追求快樂而旅行的人。休閑、娛樂是大眾旅游區別于許多“前旅游”(pre-tourism)和新興旅游形式的一種重要特質。
2 大眾旅游的源起
對于大眾旅游的源起,研究者們一般會溯及生產力的提高、交通技術的進步、假日制度的改革以及Cook所推動的產業化等因素,而很少從社會文化的視角來審視大眾旅游的發生機制。即使有,也往往落入MacCannell旅游現代性的分析框架中。不管是王寧“旅游是現代性好惡交織的反應與體現”,Urry將旅游看作是現代社會的地位標志(themarker of status),還是Rojek把旅游看作是人們在現代性條件下的“解脫方式”(ways of escape)和彌補現代性所帶來的失落感(a sense of lost)的產物。相關解釋均顯得過于概括和宏觀,對于大眾旅游的源起有必要從社會文化變遷和旅游行為本體意義的更加具體的層面來展開探討。以觀光為基礎的休閑、娛樂是大眾旅游的核心標志之一,觀光( sightseeing/trip)、休閑(leisure)和娛樂(recreation)也一度成為了“旅游”的代名詞。《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旅游定義為“以娛樂為目的的旅行”,而“旅游者”是“以娛樂為目的而旅行的人”。但是,早期的旅游(或旅行)與觀光和娛樂之間卻聯系甚微,到了大眾旅游階段這一狀況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2.1 “大眾旅游”與旅游吸引物的泛化
Urry的“旅游凝視”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旅游社會學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成果,在Urry看來,旅游者所有的感覺器官中,眼睛無疑是最為重要的。Urry說:“通過考慮典型的游客凝視的客體,人們可以利用這些客體去理解那些與它們形成反差的更為廣闊的社會中的種種要素”。與Urry不同的是,在另一篇更早且同樣被廣為引用的研究文獻中,Adler在追溯了觀光(sightseeing)的起源后發現:在17世紀以前,旅游(travel)最先被視為一種藝術,其為歐洲的精英份子們所實踐,旅游更多的是出于獲取知識和增長見聞的目的。在旅行前需要大量閱讀、搜集信息,并學習他國的語言,在旅游活動中,相較于視覺上的審美和愉悅,增長見聞和知識獲取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18世紀這一情況發生了深刻變化,Adler認為要理解這場變革就必須還原到歐洲的文化變遷語境中,即“知覺的視覺化”過程(the visualization of perception)。
爬梳歷史,在18-19世紀之交,對于歐洲文化變遷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于浪漫主義思潮( romanticism)。這場肇始于18世紀中后期英國文壇的反新古典主義文學運動,在19世紀席卷歐洲,影響遍及文學、藝術、哲學等各個領域。在旅游研究中,功績卓著的旅游社會學研究者,UITy、Frow、Sharply、王寧等都一致強調了這場文化思潮運動對于風景觀光(sightseeing)的影響。如果說文藝復興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助催了人們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為現代旅游提供了全球性的基礎。那么,浪漫主義運動則進一步推波助瀾,作為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其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理想。浪漫主義關于自我的擴張,藝術的自足,生活世界的詩化和審美化,進一步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原則。在這場運動的影響下,風景旅游(scenic tourism)開始出現,對美麗和壯觀的體味更加私人化、更富激情,旅游知覺走向視覺化。18世紀末之前被認為是充滿荒涼、丑陋、恐懼的阿爾卑斯山被旅游者浪漫化,轉變為充滿景色、形象和新鮮空氣的地方。昔日被看作是惡魔和盜匪藏身的森林,成為了充滿魅力的吸引物。在英國鄉村,對于湖區的看法,也從毫無吸引力、充滿危險之地變成了一個彌漫著祥和、鄉村氣息,雖貧窮但幸福得一塵不染之地。各種自然景觀成為了旅游凝視的對象。在19世紀的發展中,一方面,浪漫主義以懷舊的心理惦念著“質樸”的過去,并進一步孕育著對民間生活和民族傳統的濃烈興趣。另一方面,隨著東方學的興起,全球敞視主義( panpticon)被塞進西歐人的旅游包里,在全世界昂首闊步,升華為旅游熱。到了19世紀后半葉的
歐洲,百貨商店也成為了空間常設化的博物館,各大城市競相舉行的博覽會成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與此同時,Cook所推動的鐵路旅游不僅消除了旅行帶來的不便與危險,而且結構性的改變了人們對于風景的知覺,風景得以向著更為遙遠的地方延伸。印刷技術的進步更是賦予了人們沒有去過的地方一種想象的被照片所截取的美,起到了風景名勝旅游的大眾化效果。景觀和旅游體驗被進一步視覺化,旅游吸引物在全球范圍內被建構,其結果正如同MacCannell筆下所描述的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巴黎旅游那樣,游客被帶領游覽下水道、陳尸所、屠宰場、政府印刷局、造幣場、證券交易所以及正在開庭的高級法院。在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旅游景觀成為沒有邊界的范疇,而旅游景觀的建構和營造的過程也成為了大眾旅游市場不斷擴張,大眾旅游現象不斷普及的過程。
2.2 大眾旅游與娛樂
Boorstin在對旅行者(traveler)和旅游者(tourist)進行比較時強調:旅行者是積極投身工作的人(anactlve man at work),而旅游者則是追求娛樂和觀光的人(a person makes a pleasure trip)。在他看來,大眾旅游者是那些借助于大眾媒介的宣傳和產業的組織,以開展定點的拍照、娛樂、觀光和消費的一群人。Aniculaese在研究美國休閑旅游發展時提出:“在產業革命前,人們外出旅行無外乎兩種原因,貧窮者(the poor)為了獲得物質上的自由(material freedom).而富有的貴族則通過旅游來豐富知識和學養以標示他們的社會地位”。Urry在追溯了漫長的人類旅游史后,也認為:19世紀以前,上層階級以外的人,很少會出于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而去旅行,去觀看各種事物,出于與工作或生意無關的原因去旅行是現代大眾旅游的主要特征”。“旅游”的詞源學考證也能支持他們的觀點。旅游對應的兩種基本表達中,“travel”與“travail'原本是同一個詞,本身即表示辛苦、勞動、痛苦。“旅游”的另一表達詞根“tour”則源于拉丁語的“tornare”和希臘語的“tornos”,其含義是車床或圓圈,圍繞一個中心點或軸的運動,意指按照圓形軌跡的運動。根據Haulot的觀點,“tour”一詞起源于圣經的《民數記》,與探索、旅程和探險等概念相呼應,這一過程充滿了各種艱辛和苦楚。直到《簡明牛津英語詞典》于1800年首次發布了“tourist”一詞后,“旅游”(tour)才用以特指以愉悅或文化為目的而旅行的人。
大眾旅游階段,旅游得以與娛樂之間建立起了普遍的關聯。如果追溯對后世影響較為深遠的幾種“旅游”形式,可以發現它們與娛樂之間關聯甚少。例如,節事旅游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奧林匹亞是古希臘最為流行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公元前776年舉辦的首屆運動會就吸引了成千上萬來自希臘和其他國家的參觀者,但是古希臘人并不將休閑視為放松和調整,而是將它看作通過教育、運動和音樂達到自我提升的方式,拜訪圣人和參加節慶都是希臘生活的一部分,而追求愉悅的旅行并不常見。朝圣(pilgrim)可能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種自愿旅游形式,以至于有學者甚至認為現代旅游源于朝圣。早在3世紀時基督教徒就前往伯利恒( Bethlehem)參觀,10世紀后,這種跨國旅游的人數開始大量增加,然而,朝圣的旅程總是充滿艱辛,它是一種苦修的方式。教育旅行(the Grand Tour)作為16世紀到19世紀早期歐洲貴族最重要的跨國旅游形式,其目的也是在于幫助年輕貴族實現完整的教育,只是到了19世紀,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教育旅行才從教育走向觀光和娛樂。從19世紀開始,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社會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開始發生分化,時間變成一種資源,并被分割成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與此同時,旅游作為一種逐漸為大家所熟知和喜歡的休閑活動也從社會生活中分化出來,旅游的地點與工作、家庭的地點同步發生分化。“旅游”被視為一種“另類”的生活,它為身處現代性背景下的人們提供了一種“逃逸”(avoid)和“再造”(recreat)機制,正如Pieper所說:“辛勞工作,歡樂收割,假日就是可以免除像奴隸般工作的日子”。各種各樣的旅游形式也越來越多地與娛樂、享受聯系到了一起。
3 大眾旅游的趨向
作為旅游現代性研究范式的發起者,在2001年出版的《東道主與游客》(Hosts and Guests)(第三版)一書中,MacCannell感嘆道:“人們在地球表面任何兩點之間旅行時的體驗越來越相似,隨著旅游業本身將人們的旅游體驗以及旅游目的地變得同質化,這一過程是否將最終使得人們的旅行動機消失”? Cohen也認為,目的地“地域性”的散失,后現代情形下來自不同意義領域的體驗同質化,以及仿真技術的進步將對旅游作為一種獨特的活動形式構成威脅,可能導致旅游的終結。這是否意味
著大眾旅游將在其到達歷史的最輝煌時刻走向滅亡?誠然,如果僅僅將旅游等同于大眾旅游,即傳統意義上的以尋求差異性為目的的娛樂和觀光,那么對于大眾旅游最終發展趨向的預測難免陷入悲觀。問題的關鍵卻在于旅游現象并不是“均質”的,一方面,大眾旅游僅僅只是諸多旅游形式中的一種。朝圣、探險、修學等旅游形式多元并生,它們在現代性及后現代性的語境下與大眾旅游互動共生、不斷演化,呈現為新的旅游形式和現象。另一方面,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背景下,大眾旅游本身也正不斷發生著變化。Mowforth和Munt曾具體描述過這種變化:旅游產品需求由福特主義走向后福特主義(fordist to post-fordist);現代性走向后現代性;包價旅游(packaged tourism)走向個性化旅游(individual tourism)以及旅游的社會、文化和生態責任意識日益凸顯。Uriely和Urry則傾向于用“后現代”來形容當前旅游的新變化。在Uriely看來,后現代旅游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虛擬后現代性”(simulational postmodernity),其傾向于追求超真實的旅游體驗(hyperreal experiences).另一種是“另類的后現代”(other postmodernity),其有別于傳統旅游形式而強調可替代( alternative)、真實( real)、生態的(ecological)和負責任(responsible)這樣一些概念。
相較而言,Urry對后現代旅游的描述則更加具體,他認為“后現代旅游”的結構特征是“去差異”(de-differentiation),其表現正如Turner和Ash在The Golden Hordes -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人們在尋求永遠新鮮的旅游目的地的過程中,建立起的只是一套酒店和旅游景觀,平庸乏味,缺少反差,對奇異性和差異性的追求卻以缺少奇異性和差異性的始終如一而告終”。后現代旅游的另一個特征是玩樂,后現代旅游者在大量的選擇中感知變化和快樂,他們不受高雅文化的約束,以無止境的追求快樂為原則,用快樂的心態對待一切。Sharply則認為,在后現代旅游中,旅游消費也發生了變化,由于消費者的支配角色的不斷強化,對于個性化旅游產品的需求增加,生產和消費的關系變得無關緊要,消費被視為夢想的實現,對愉悅體驗的追尋以及逃離日常文化和社會的刻板與結構方式。這種變化導致了Campbell“想象的享樂主義”(imaginative bedonism)中所描述的:“幻想和期盼成了消費的重要過程,人們并不從產品和他們實際購買和選擇的使用中尋求滿足,相反,滿足源于期盼,源于一種想象愉悅的追求過程”。與此同時,大眾旅游的審美特征也正悄然發生變化。快樂哲學和快活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人們的旅游審美需求也開始不再超脫,逐步遠離靜觀和無功利,趨向以休閑為中心的體驗和參與。旅游走向全民化、普及化和生活化,褪下獲取知識、陶冶性情、實現價值的神圣外衣,而走向放松身心、懷鄉念親,追求歡娛的世俗體驗。審美目的世俗化、審美標準模糊化、審美情趣符號化和審美意識多元化成為了當下日常生活審美文化的顯性表達方式。以此來看,Aramberri對于大眾旅游發展的評價或許更顯客觀:“現在宣告大眾旅游的死亡顯然為時過早,現代大眾旅游的壽命應該更持久”。
事實上,如果對旅游的本質稍加審視,“大眾旅游終結論”無疑是顯得過于悲觀和武斷了。旅游作為一種異地追求身心自由的體驗,是合乎人性的一種存在,是人的天性的一種反映。作為一種理想性、創造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人生而具有擺脫本能決定其行為而追逐自由的天性。旅游中的求新、求異、求體驗,在本質上正是人類對有限生存時空所產生的生命期待和生命本能的內在沖動,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基本需要,旅游許諾給人們一段悠閑的時間,擺脫工作、物質和心靈的羈絆,在理想中度過,實現日常生活的回歸和精神短暫超越。旅游是使人達到詩意的棲居不可或缺的生命維度。既然自由是人的生命本能,那大眾旅游就永遠不會消失。
4 結束語
事實上,討論“大眾旅游”而又緘口不言“何為旅游”,這多少顯得有些牽強。然而,一旦溯及“旅游”,又不得不陷入旅游的概念爭議和旅游史的討論窠臼,類似的研究在國內外旅游學術積累中早已“汗牛充棟”,當然也莫衷一是。本研究試圖擱置這些爭議,而從大眾旅游現象的表征及其發展進行直觀的歸納和剖析,以期能進一步窺視旅游現象的多元特征及本質屬性。旅游社會學是通過建立旅游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而得以從學科邊緣走向中心的,對于大眾旅游現象的關注是旅游社會學研究獲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關鍵所在。然而,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之后,當我們重新回顧MacCannell所建立的旅游現代性研究范式會發現,它雖然極具概括性,卻將旅游活動的“參數”設計過于狹窄,“對工作/休閑(旅游)簡單的二分導致了一些嚴格意
義上來說既非旅游又非工作的特定旅游形式被忽略”。Kuhn說只有當科學家發現研究對象的一些或者全部組成部分無法相協調時,他們才會著手于尋找其他替代的解釋或更佳的理解方式。旅游現象從來就不是均質的。
一方面,朝圣、教育旅行以及Cohen筆下的漂泊者(drifier)、探索者(explorer)穿越歷史,在新時期以宗教旅游、修學旅游、探險旅游等面目出現,在現代性背景下,它們可能摻雜了一些大眾旅游的觀光、娛樂性,但在審美、組織形式和行為動機與特征方面仍有別于大眾旅游。
另一方面,誠如Urry所言,工作與休閑相分離是大眾旅游的主要特征,新時期我們看到的卻是旅游(包括大眾旅游)越來越多地走向與工作、生活相融合。作為普遍存在的背包客、探險旅游、靈性旅游和黑色旅游等,有時看來不僅不是享受,甚至帶有一種自我折磨的特征。作為新興的志愿者旅游、善行旅游、扶貧旅游等形式也不能歸人大眾旅游的行列和旅游現代性的研究框架。
長期以來,我國旅游學術研究主要是對歐美發達國家學術話語體系的單向輸入和模仿。對于大眾旅游的研究同樣如此,無論是改革開放后對入境旅游的關注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旅游研究,國內旅游學界的研究重心一直聚焦于大眾旅游,旅游相關學科的知識譜系構建也多以大眾旅游為主體。由于國內旅游經濟發展的實踐需要,研究者的視角也表現出了極強的經濟學學科偏向特征。相較而言,對于大眾旅游之外的其他旅游現象的研究則往往散落于生態旅游、體育旅游、背包旅游等現象的研究之中,且對“非大眾旅游現象”的關注也主要聚焦于經濟學、管理學和地理學等應用性極強的學科,而較少從社會學、哲學、文學等角度去進行闡釋。
從長遠來看,這樣一種狀態并無益于增進國內旅游現象研究和旅游學科發展。相較于歐美發達國家,我國旅游業起步相對較晚,目前仍處于大眾旅游市場規模急劇擴張的階段,且正經歷著一場歷史性的變革。旅游者動機多元化、旅游資訊技術化、旅游吸引物無邊界化以及旅游體驗定制化等一系列的變化正深刻地影響著旅游發展的方方面面。2018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更是明確指出我國的旅游發展要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優質旅游發展階段”,并提出了深化供給側改革、推進全域旅游、綠色旅游、鄉村旅游、旅游扶貧,開發海陸空旅游新業態等系列舉措。面對著這樣一場規模空前的變革,國內大眾旅游必將隨之發生變化,對此,國內旅游研究是否也應該同步給予更多關注和思考,并嘗試訴諸理論的探討和創造,以探索適合于我國旅游產業發展實踐和特色的旅游理論,在實現對西方大眾旅游傳統研究范式(尤其是旅游現代性研究范式)借鑒和反思的基礎上,構筑一個專屬于我們自己的旅游學術研究話語平臺和體系?這無疑是非常迫切且令人期待的。
A Summa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MaSS TOUriSm
DONG Peihai1,2,LI Qingleil,LI Wdi3
(1.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aoshan University,Baoshan 678800,China;
3.International College,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odern tourism created by Dean MacCannell, which was brought forwarddue to the atten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mass touris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tourism sociology. Although this paradigm gives full scope to tourism phenomenon and tourismresearch, it ignores the description of other tourism phenomena and behaviors beyond mass tourism. Infact, pilgrimage, backpacking tourism, black tourism, spiritual tourism, volunteer tourism, good tourismand pro-poor tourism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discussion of mass tourism. Due to multiple research onmass tourism, tourism is regarded as a homogeneous phenomenon,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a properacademic tension and imagination regarding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study of modern touris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ss tourism inChina and abroad, and it analys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 frnally arguing that we can'tsimply equate mass tourism with the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hat large-scale population flow is only themanifestation of mass tourism. The phenomenon of mass tourism needs to be understood consideringfive aspects, namely, popul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ocial struct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progress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the reform of holiday syste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moted by Cook,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e, the origin of mass tour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ansion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tourism. The Romantic Movement at the turn of the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enic tourism. Natural landscapes, traditions,historical heritage, museums, department stores and other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ocations had becometourist attractions. Since the 19m centu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s pursuit for knowledgebegan to weaken and became more popular, and a univer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entertainment" had been establishe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ha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mass tourism.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the trend of mass tourism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outthat mass tourism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forms of tourism, and other forms, such as pilgrimage,exploration and drifting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heseforms of tourism interact with mass tourism and evolve continuously, presenting new forms and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t the same time, som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aestheticcharacteristics of mass tourism. Travel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 sacred significanceof acquiring knowledge, edifying sentiment and realizing value has been weakened, while the secularexperience of relaxing one's body and mind and interest in entertainment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estudy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in the future will not go to extinction, since tourism isa reflec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tourism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ispaper appeals to Chinese researcher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me new changes in tourism, to activelyexplore and create theories, to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modern tourism research paradigm, and toexplore tourism theor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mass tourism; the generaliza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 recreation; trend of mass tou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