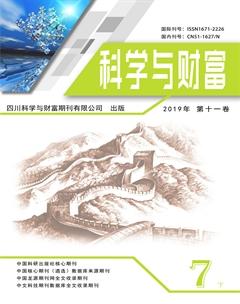關于“以房養老”政策中國化的文獻綜述
一、引言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2.41億人,占總人口的17.3%;65周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1.58億人,占總人口的11.4%。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到2035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4.09億人,占總人口的32.2%;到2050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4.79億人,占總人口的44.0%。由此可見,我國是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加之養老保障機制不健全、“四二一”家庭大量涌現以及“空巢化”現象不斷加劇,僅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和現行的養老保障機制是難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危機的。
二、“以房養老”中國化歷程
(一)“以房養老”引入及定義
“以房養老”全稱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是一項商業養老保險產品,面向的是60歲及以上老年群體,其資格條件是那些擁有房屋完全產權的老年人,具體做法是將其房產抵押給保險公司,老年人繼續擁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經抵押權人同意的處置權,其受益是按約定條件老年人領取養老金直至身故,在老人身故后,保險公司獲得抵押房產處置權,處置所得將優先用于償付養老保險相關費用。
章萍(2014)指出,從本質上講“以房養老”政策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終身年金保險相結合的創新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其首先是保險公司提供的一種商品或服務,是老年人將自己擁有的房屋實物資產通過市場交易的途徑置換為養老經濟資產以滿足老年生活所需,實現自我養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是由于其以房產作為支付手段的遠期金融商品,由于房產只有在老人身故后才可以處置,產品交易流程復雜,期限較長,較一般的現貨商品具有更大風險性。
(二)“以房養老”在中國的發展
胡江濤和曾祥瑞(1997)最早將反向抵押貸款的定義引入中國,介紹美國反向抵押貸款的構成要素、產品需求、風險防范。時任中房集團董事長孟曉蘇(2002)最早提出開發反向抵押貸款產品。柴效武(2004)更為通俗的闡釋反向抵押貸款,即“以房養老”,并與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洪娜、盛壘(2014)指出西方社會的養老體系以家庭養老、居家養老、機構養老3種模式為主,同時還根據老人的年齡、收入和健康水平,制定各種個性化、特色化的新型養老方式。其中,“以房養老”最受歡迎,也相對成熟。
三、“以房養老”可行性分析
鄭秉文(2018)提出“以房養老”政策可以為有條件的老年人提供一個新的財務計劃選項和一個額外的退休金解決方案。不但能使老人繼續自給自足過有尊嚴的生活,也可以減輕年輕人的養老負擔以及政府的社會福利負擔。馬征(2017)認為這種將贍養老人包含的資金成本體現為家庭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的金融關系,在相關養老政策中具有較強的獨立性,是一種新的嘗試。
(一)退休人員的生活來源
鄭秉文(2018)指出我國退休人口的主要生活來源有三大支柱,第1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第2支柱是企業年金,但其參與人數只有2300多萬人;第3支柱是稅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和養老目標基金,但其試點剛剛起步。趙立志(2014)調研發現老年人退休金較少,家庭的主要資產為房產,我國是家庭自有住房擁有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達到了87%,這也致使老年人淪為“現金上的窮人,房產上的富翁”。如何通過反向抵押貸款,提升房屋的變現性成為一個迫切的課題。
(二)傳統家庭養老功能的喪失
另一方面,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和政府養老保障水平低催生了“以房養老”需求欲望。在“421”家庭模式下,老年人空巢化趨勢明顯,“少子老齡化”的嚴峻態勢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受到嚴重的削弱。我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多數子女居住和就業地離父母居住地較遠,且其對獨立生活有較高要求,自立門戶比例逐年增大,居民對“核心家庭”意識的接受度越來越高,這為“以房養老”的實施提供了可行性(朱鯤鵬、張曉偉,2015)。
(三)我國的市場環境
范英麗、睢黨臣(2012)指出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推行以房養老制度更具備有利條件:①我國的房屋自有率高,使得較多老年人適用此方案;②城市房產價值較高,跌價風險相對較小,金融機構承擔負凈值的風險也較低,使他們意愿進行以房養老服務;③傳統價值觀下老年人不愿意搬去陌生地方居住(如養老院),此方案不但可以提供老年人在自己住宅老去,且還可以以房屋價值抵押后取得資金來支付日常及醫療支出等需求;④以房養老制度的推行對國家、老人、相關行業、年輕人都有益處。陳鵬軍(2013)建議在住房反向抵押推向全國之后,應在適當時機將政策支持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將住房反向抵押納入社會保險體系并為其制定擔保政策是促使抵押市場迅速發展的根本措施,住房反向抵押作為居家養老的重要措施,應將其納入我國養老服務體系。
不過在“以房養老”實施試點的四年里,成果并不盡如人意,北京、上海、南京等地2003年后曾不同程度嘗試過“以房養老”,但由于細化的可行性配套措施跟不上,最終都無疾而終。王新(2014)提出“以房養老”如能將這部分“死錢”激活用作補充養老金,對做大養老產業將是一個強有力的支撐。
四、結論與展望
“以房養老政策”剛出臺之時,有部分人質疑此舉是政府在推卸養老責任。但事實上,“以房養老”是一種自愿行為,屬于個性化、高端化的市場化養老模式,范子文(2012)強調其可作為差異化養老需求的補充,它不能也不會替代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的核心作用。
在住房反向抵押試點擴大到全國范圍之際,鄭秉文(2018)也坦言“以房養老”作為一項小眾產品在推向全國之后,其基本格局在較長時期內難有根本改變,即使是發展較為成熟的美國,住房反向抵押的市場占比都不是很大,規模有限。但是中國市場基數較大,其潛在市場也不可小覷,應當滿足這部分人的需求。隱性市場變為顯性需求要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應仔細分析其需求端和供給端存在的問題,適時推出適當的政策支持,以滿足這部分消費者的社會需求,為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的形成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鄭秉文. 以房養老的前景分析與政策建議——寫在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推向全國之際[J]. 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20(06):2+7-14.
[2]章萍. “以房養老”產品市場培育的有效路徑研究[J]. 經濟體制改革, 2014(6):126-129.
[3]馬征. 政策過程理論視角下“以房養老”推行困境的原因分析[J].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 2018(3).
[4]金曉彤,崔宏靜. 亞洲國家“以房養老”模式的經驗與借鑒———以日本和新加坡反向住房抵押貸款為例[J].亞太經濟,2014,(1).
[5]鮑家偉.“以房養老”的國際經驗及建議[J].宏觀經濟管理,2012,(3).
作者簡介:
姜帆(1995-)男,漢,山西省忻州市,碩士,山西財經大學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