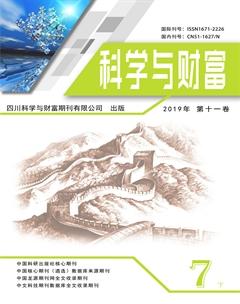“毒樹之果”在我國適用的路徑分析
摘 要:自從1997年全面依法治國的方略的提出,我國開始大力發(fā)展法治建設(shè),并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穩(wěn)步邁進。盡管我國已經(jīng)進行了數(shù)十年的法治建設(shè),但近些年來不斷涌現(xiàn)的冤假錯案,還是十分讓民眾和法學界人士心寒。深層剖析趙作海案等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一例外地可以看到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式暴力取證的身影,這不僅會讓民眾喪失對于我國司法的信心,更是破壞了司法正義,不利于法治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因此,2012年我國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確立了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由于立法中對“毒樹之果”規(guī)則的缺失,導致理論界對于其概念,取舍產(chǎn)生巨大分歧,不僅影響了法官在司法實踐中的判斷,更是使其難以發(fā)揮最大效用。下面本文將從概念的厘清出發(fā),結(jié)合我國目前的理論爭議,提出對于其在我國確立的不成熟建議。
關(guān)鍵詞:毒樹之果;概念;理論爭議;立法建議
一.“毒樹之果”概念厘清
毒樹之果是由“毒樹”和“毒果”兩部分組成的。其中“毒樹”是指辦案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來獲得的證據(jù),即非法證據(jù),理應根據(jù)非法證據(jù)規(guī)則予以排除;而“毒果”,從表面上來解釋,為毒樹上所結(jié)的果實,指根據(jù)毒樹收集來的毒果,即根據(jù)非法證據(jù)派生出來的其他證據(jù)。這也就體現(xiàn)了“毒樹之果”是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派生規(guī)則。
(一)狹義說
狹義說中的“毒樹”表現(xiàn)為非法言詞證據(jù),指偵查人員通過暴力、威脅等手段獲取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而“毒果”指的是通過取得的非法證據(jù),再次采用合法亦或是非法手段進而取得的一系列的書證、物證等證據(jù),而衍生的證據(jù)就是我們所說的“毒樹之果”。
(二)廣義說
廣義說的學者認為“毒樹之果”的“毒樹”不僅僅局限于非法言詞證據(jù),“毒果”也不局限于通過非法言詞證據(jù)所獲得的的書證、物證等。
由于毒樹之果原則是從美國傳來的舶來品,應當根據(jù)我國具體的國情來作出有利于我國法治建設(shè)的含義解釋。筆者認為廣義說更符合其本義,也更有利于司法實踐的開展。但在現(xiàn)實中,我國學者所探討的很少涉及以非法物證、書證或其其他違法行為所衍生的證據(jù),是十分狹隘的。
二.“毒樹之果”規(guī)則在我國的理論爭議
目前,對于非法證據(jù)應當予以排除,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中,都已經(jīng)達成高度一致,但對于其延伸規(guī)則——“毒樹之果”規(guī)則的取舍問題的觀點卻是大相徑庭:
(一)否定說:“砍樹棄果”
堅持否定說是美國的“毒樹之果”原則一直所堅持的觀點,認為程序正義優(yōu)先于實體正義,而支持否定說的學者又大致可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完全否定的觀點,認為無論證據(jù)是否客觀真實,只要違反了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取得的證據(jù),都應該完全排除非法證據(jù)以及非法證據(jù)派生出的證據(jù)。筆者認為,此觀點雖然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懲治犯罪人的機會,但是卻從將通過刑訊逼供等暴力手段取證的行為從根本上扼殺,更有益于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quán)。而另一種觀點,稍微緩和一些,主張考慮例外情形,而不是完全否定。比如,污染中斷,獨立來源,必然發(fā)現(xiàn),善意以及“稀釋”或“清洗污染”等例外情形。
(二)肯定說:“砍樹食果”
堅持肯定說的國家,以英國為代表,更加傾向于實體正義,更有利于對被害人權(quán)益的保障。而持此態(tài)度的學者又可以大致分成三派。
第一種完全肯定,認為只要經(jīng)查證屬實有證明力,就可予以采信;第二種為線索說,有,將其作為線索使用,按照合法程序重新查證,從而使得非法證據(jù)合法化;第三種為區(qū)別說將其按照言詞和實物分類,對于言詞形式的“毒樹之果”,無論是否客觀存在,都不具有證據(jù)能力。而對于實物形式的,只要該實物類“毒樹之果”經(jīng)合法程序查證屬實,則可以在案件中采用。
(三)折衷說
在探討“毒樹之果”的取舍問題,單純地全部肯定或者否定,雖然難以適應現(xiàn)實司法實踐中紛繁復雜的情況,但是有利于司法的穩(wěn)定性。“毒樹之果”的理論最早是通過判例確立的,而我國屬于成文法國家,不能過于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quán),理應在立法中明確。而一些學者認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若是影響力大的疑難案件,適用“毒樹之果”,而其他情況,一律予以排除。但是如何定義影響力大的疑難案件呢?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搖擺不定的理論建構(gòu),只會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quán),不利于實現(xiàn)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統(tǒng)一。
三.“毒樹之果”在我國適用的建議
(一) 明確排除“毒樹之果”的適用
從法教義學的觀點來看,我國刑訴法關(guān)于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文字表述,應當認為間接源于違法行為的證據(jù)也要予以排除,即“毒樹之果”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同樣適用。因為只要違法行為與取得的證據(jù)之間存在著因果關(guān)系,則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都應當予以排除。而我國對于“毒樹之果”原則的排除沒有明確規(guī)定,易造成理論界與司法實踐的觀點分歧,難以發(fā)揮其最大效用。
(二) 增強執(zhí)法透明度,提高執(zhí)法能力,嚴格限制執(zhí)法程序
針對執(zhí)法過程的不合程序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限制,一是外在限制,例如嚴格執(zhí)行錄音錄像制度。根據(jù)刑訴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中規(guī)定:“應當進行錄音或錄像的案件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此條款規(guī)定,符合規(guī)定的犯罪嫌疑人每次被訊問時都要進行錄音或者錄像。二是以法律的形式予以限制,完善對訊問人員,偵察機關(guān)等人員的違法行為的懲戒制度,健全責任問責追究制度。
(三) 建立庭前審查制度
我國現(xiàn)行立法沒有專門的庭前審查制度。所有證據(jù)一律進入庭審,由審判長一并裁斷。這使得一些非法證據(jù)以及“毒樹之果”,和其他不符合關(guān)聯(lián)性,真實性的證據(jù),容易對審判員造成一定潛在的影響。因此,筆者主張在我國設(shè)立證據(jù)庭前審查制度,對證據(jù)進行庭前審查,將法律規(guī)定應予排除證據(jù)提前排除,不僅可以提高審判的效率,更是有利于使案件的處理更加公平。
四.總結(jié)
即使我國在立法中確立了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但若未將 “毒樹之果”規(guī)則明確規(guī)定在法律中,是難以發(fā)揮其效用的。因此,在汲取美國毒樹之果規(guī)則的實踐經(jīng)驗基礎(chǔ)上,應當結(jié)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科學立法,而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在立法中明確,執(zhí)法上嚴格要求,和司法上的程序創(chuàng)新等舉措綜合運用,使得訴訟案件在處理時更加公平和公正,更好地達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統(tǒng)一,減少冤假錯案,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
參考文獻:
[1]易延友. 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立法表述與意義空間——《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J]. 當代法學, 2017(1).
[2]李學寬.論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jù)的效力[J].政法論壇.2002(1):72
[3]雷洋. 正義的代價[D]. 2011.
[4]汪海燕. 論美國毒樹之果原則--兼論對我國刑事證據(jù)立法的啟示[J]. 比較法研究, 2002(1):65-74.
[5]易延友. 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的立法表述與意義空間——《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J]. 當代法學, 2017(1).
[6]王吉春, 王詩然. "毒樹之果"排除規(guī)則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的激活路徑[J]. 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 2016, 26(3).
[7]汪海燕. 論美國毒樹之果原則--兼論對我國刑事證據(jù)立法的啟示[J]. 比較法研究, 2002(1):65-74.
作者簡介:
單江沛,女,漢,河北衡水人,河北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