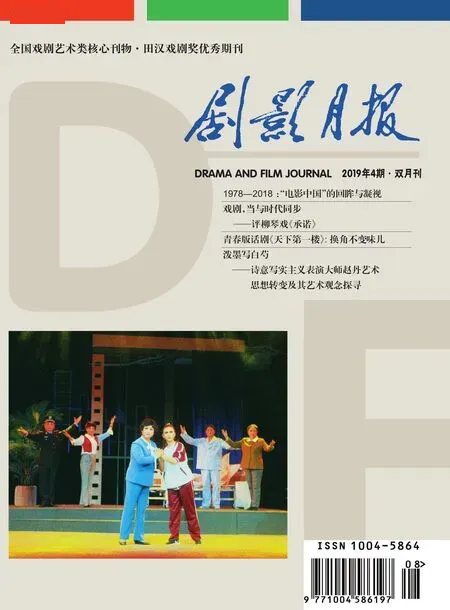石揮電影《我這一輩子》重讀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對私營傳媒的管理政策相對寬松,政府“在多個方面對奄奄一息的私營電影予以扶植”[1],電影創作享受著國家多種優惠政府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此大背景之下,文華電影公司的重要影人石揮,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將對時代的憧憬和對電影的熱愛融為一體,創作了影片《我這一輩子》。本文從影片鏡頭及人物塑造入手,具體探究石揮電影的內涵及藝術創作風格。
電影《我這一輩子》改編自老舍的同名小說,講述了舊中國黑暗社會中一個老北京巡警的一生,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是石揮的代表作品。重讀影片,我們體會到一代電影大師對老舍小說的再創作,以及在歷史背景下對舊中國階級壓迫的深刻揭露,弘揚了電影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影片傳遞著的“希望”內涵,貫穿于老巡警坎坷的一生,在悲愴中演繹希望是影片的主旨,也是影片的整體基調。
一.對比鏡頭的運用
電影運用了大量對比鏡頭真實地反映現實,刻畫矛盾。敘事開端利用隱喻蒙太奇對北京城內的古建筑進行對比。鏡頭伴隨主人公旁白運動,這段鏡頭里,我們一覽北京城下的名勝古跡:“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紅墻琉璃瓦……自然風光的展現美不勝收,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著白塔的影子,營造出一片祥和之感。”隨之一轉“西太后把練海軍的錢蓋了頤和園,萬壽山……這是三百六十萬銀銅造的銅亭,老百姓的血汗啊,長廊一共是兩百七十六間,這也不知道得多少錢,天壇,這是皇上祭天用的,多大的工程啊,北海,白塔,多美啊……”旁白與畫面結合使北京城內紅墻琉璃瓦的宮廷建筑與破壁殘垣的街頭巷尾形成強烈對比,極具諷刺意味。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不僅引出主人公刻畫了故事背景,也為隨后從荒涼街道引出老巡警埋下伏筆,暗喻他就是北京城破壁殘垣里的一份子。倒敘介入故事開端后,鏡頭又將老巡警巡邏達志橋處理平民爭執的威風與辮子兵兵變時只能躲在別家看其燒殺擄掠的手足無措做對比,含蓄地交待了人物性格和身處這片土地上的小人物的社會地位,對其后所受不公待遇埋下伏筆。
鏡頭還將階級社會的貧富差距運用對比蒙太奇來展現:拉車的窮人跑破了鞋子感嘆“日子怎么過!”秦大人的姨太卻逛遍全城才買到一雙勉強心儀的鞋子;秦大人花五十塊只為買一瓶香水,窮人為治病卻不得不將自己的孩子以三十元賣掉。富裕的秦大人與北京胡同口平民百姓的生活在鏡頭轉場下形成鮮明對比,揭露了舊社會對老百姓生活剝削,引導觀眾更加直觀的感受舊社會存在的矛盾與沖突,凸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象。老巡警是這些不公的見證者,眼看著辮子兵殺人放火,鄰居家兒子小鎖被辮子兵砍死束手無策,他懵懂地被人告知一個拿著六塊錢大洋的臭腳巡不值得去送命,慢慢地對于生活中的不公從叫囂到不聞不問,最后變得麻木不堪,他淪為了這個時代的“階下囚”。只是沒有想到,這還不是最壞的結局。日本人搜尋慰安婦到自家門口時,老巡警無力阻攔,眼睜睜看著兒媳婦被人搶走,面對親家撕心裂肺的懇求,只能給自己一個耳光。同樣,面對兒子質問如何心甘情愿做著秦大人的走狗,他也只能聲嘶力竭地喊道“你要走走你的,等你打了勝仗回來,你把你這漢奸爸爸槍斃了,你要不走你呆在家里頭,讓我這個漢奸爸爸養著你!”。“‘我’的這一番話能夠代表當時一些底層民眾的真實想法,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但生活還得繼續,而這種不反抗的亡國奴心態也正是影片所要批判的”[2]。對沉默過往的平靜忍受終于被輪回打破,沒人為他吶喊做主。那些原以為沉默就可以逃避的過往,全都被生活加倍還給了他。
除此之外政治形勢更迭不斷形成對下層平民的壓迫也是影片展現的主要內容之一,影片利用心理蒙太奇來展現這一時期人物內在的精神世界。勤勤懇懇工作換來升職加薪的老巡警因秦大人一句安排小舅子胡理上位的話而被削官降職,無處說理。后來為日本人翻譯的漢奸胡理為自己辯解在北京抗戰時干了不少地下工作反而獲得了更高的職位。電影通過這一鏡頭刻畫了胡理兩面三刀的形象,這種自然而然的對比式手法使觀眾真真切切地體會到老巡警內心的苦不堪言。面對這個“吃人”的封建舊社會,老巡警將所有的不公化為沉默,沉淀在心中,等待時機破土而出。即使沒有切身經歷,我們也為之憤恨,為封建統治階級下老百姓的苦不堪言而憤恨。“盼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老巡警在經歷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對這個時代唯一的總結。然而悲劇還不算完,老巡警迎來年過半百的六十歲之余,替挨打的鄰居求情使漢奸想起了他逃走的兒子海福是共產黨的事情,警察局長將老巡警捆綁在椅子上,使用了老虎凳,灌涼水等一系列酷刑拷問,老巡警哀叫連連,不禁發出哀求“我今年六十歲的人了,你要還是個人……”面對哀嚎警察局長沒有半分同情,直至將老巡警打昏。這一殘暴的行為描繪了老巡警的心理基礎,表明了舊社會里傳統道德觀念已全然不在,剩下的只有顛倒黑白的世界。在遭受了警察局局長非人般待遇后,老巡警爆發了,這也是他唯一一次爆發。老巡警在監獄吶喊著:“共和平等自由,說的好聽沒一個拉人屎的,受苦的都是我們老百姓,這十幾年來的心血全給了國家,如今落個家破人亡的,這叫共和?民主?平等啊?我六十多歲的人了如今讓我受他媽的這份罪……這是他媽勝利了這是?這叫民主啊?自由啊?廉恥啊?我操他親娘的祖奶奶!”沉默中的爆發暗示著人物自身的對立上升到極端,與之前老巡警的一再忍讓形成對比,表現出舊社會的壓迫使得人物在命運面前顯得無比渺小。除了吶喊,再沒有半點行動反擊,多么可悲。
二.人物塑造
《我這一輩子》在闡述背景時,刻意將舊社會黑暗進行放大,同時借助“老巡警”這一人物形象延伸出“希望”的主題。電影在進行創作改編時導演加入了自身對原著的理解,通過改編和增添新人物加深主題。電影增設了一個關鍵性人物——申先生,申先生是共產黨員,他領導學生運動,秘密進行革命工作,最終死在國民黨監獄中。他的死傳遞了革命精神,埋下了光明的線索。也成為喚醒“我”不做亡國奴的意識起源。面對老巡警的爆發申先生解釋道:“你給這些漢奸,官僚做了一輩子的走狗,當奴才的,還有什么好下場嗎?”解釋了盡管老巡警安分守己,但時代如此,所謂抱怨也不過是自我的選擇。他又說:“現在不一樣了,老百姓們要自己當權了,你要給自己站崗了,這些年我干的就是這個。皮破了有肉,肉爛了有骨頭,骨頭斷了還有筋連著,想想海福他們在外邊替我們打仗,咱們這點苦還算得了什么呢?”經歷了全城通緝,與惡勢力作斗爭,直到最后獻身于革命,申先生就像革命的種子。鏡頭通過這一場景埋伏了人物的覺醒,暗喻唯有奮起反抗,才能改變這個社會。同時石揮將希望包含于鏡頭敘事之中,革命需要流血流汗,解放過程盡管漫長曲折,犧牲絕不是無謂,美好的未來就在不遠的將來。申遠的身上傳遞了抗爭的主題,他是第一批為革命獻身的人,是老巡警敢想而不敢做的延伸,他身上懷揣著光明點,傳達著救贖。悲到極致便是希望,申先生的話在絕望死水中泛起了希望的漣漪,重新給了老巡警希望,他開始期盼著,期盼著兒子海福帶領著軍隊大勝歸來,期盼著能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盡管被迫淪為舊時代的階下奴,被悲愴的宿命吞噬了生活的全部,但每位覺醒者的微薄之力都在悄然的改變著這個時代。石揮在創作時雖沒有在主人公身上明確表現抗爭的主題,卻借助老巡警兒子海福來傳達這樣一種寓意:海福是祖國的希望,民族的未來,是革命走向勝利的標志。他不愿如父親一般茍且的過活,決然選擇與這個壓迫他的黑暗社會作斗爭,不再沉默,證明了新青年正在建立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新社會。申先生引導海福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海福在電影中不再是一個為溫飽而送命的小人物,而是一個敢于反抗的熱血青年,是在黨的引導下成長起來的英勇戰士[3]。
三.希望的主題
“影片中沒有窮人的幸福生活,而是代之以疾病、死亡、動亂與饑餓。小說中‘我’因妻子與自己的師哥私奔,覺得沒臉再做裱糊匠,因此當了巡警;在電影里卻是因為“我”所在的鋪子關了門,‘我’失業了又找不到別的營生才做了巡警。師哥這一人物被去掉了,‘我’的妻子也由漂亮輕佻變為正面人物——她就像人們想象中的勞動婦女一樣勤勞樸實,長得也不好看,最后死于貧窮和疾病。”[4]這樣改編旨在突出社會問題意識,將歷史背景的刻畫通過老巡警的經歷展現,角色取源于百姓,苦難和不公在其身上的經歷使得舊社會對于尋常百姓家的迫害顯得尤其突出,展現了舊社會老百姓面對時代的無能為力,拉近人物與觀眾的距離。這一人物形象時也曾反復懷疑自己的一生為何充滿苦嘆,卻始終愿意相信每次革命也許會帶來不一樣的生活。面對學生們奮起反抗不做亡國奴,他矛盾地說道:“我也不是那個沒有良心的人,我也想和你們一起游行去,但我當這份差,混這口飯吃……”。時代的喧囂,讓老巡警變得逆來順受。選擇生活的他又不完全甘心屈服于這個時代,于是他用自己巡警的身份,盡微薄之力保護著這群學生,保護著申先生。面對學生們的勇往直前告誡學生兵來的消息;面對賞金捉拿申先生的巨額誘惑選擇掩護他走。他相信,學生和申先生是新時代的代表,新希望的傳遞。影片中主人公看似沒有直接與命運抗爭,卻間接孕育了新革命思想的頓悟。不允許兒子海福離開落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結果,還是放手讓他去革命,這是人物自身從思想到行動轉變的過程。“石揮以嶄新的藝術創作面貌和風格,塑造了一個飽經生活憂患的老巡警的形象,既是一個人一生道路的凄慘縮影,又是社會,歷史變遷與升降沉浮的標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