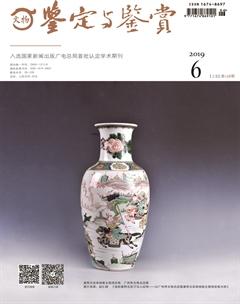銀雀山漢墓竹簡書法藝術研究
梁青
摘 要: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2號漢墓出土了不同書體的先秦竹書,以《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等為主要內容的竹、木簡牘7500余枚,解決了關于西漢書體的種種猜測,填補了西漢時期在書法史上的空白。銀雀山漢簡書體堪稱竹簡書體的精華,可謂秦漢時期隸書的典范,被書法家稱為古今漢字分水嶺,在古文字研究和書法藝術史上都占在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堪稱竹簡之珍寶。
關鍵詞:西漢;竹簡;書法藝術
1972年4月,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2號漢墓出土了不同書體的先秦竹書,以《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守法守令》等為主要內容的竹、木簡牘7500余枚,解決了關于西漢書體的種種猜測,填補了西漢時期在書法史上的空白。并證實了《孫子兵法》與失傳了1700多年的《孫臏兵法》同墓出土,解開了歷史上“孫武、孫臏其人有無、其書真偽”的千古之謎。這批竹簡代表了我國古代兵學的最高成就,被列為新中國建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建國5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大發現之一,20世紀(100年)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一。2013年《國家人文歷史》評選中國九大“鎮國之寶”,文獻書簡、銀雀山西漢《兵法》竹簡成功入選,為孫武、孫臏正名。專家汝企和點評,《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著作,其作者孫武是春秋時期的軍事家,有“兵圣”的美譽,他留下來的唯一著作——《孫子兵法》,不但成為其后中國歷代研習兵法者必讀之書,而且較早就有十余種文字的譯本發行海外,在世界上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從1號墓出土了三銖錢和半兩錢而無五銖錢來判斷,墓葬年代上限不會早于三銖錢始行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會晚于五銖錢始行武帝元五年(前118)。從2號墓出土竹簡《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和半兩錢來判斷,墓葬年代上限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根據以上分析,兩座漢墓應為漢武帝統治時期的西漢早期墓葬。這批竹簡書體應屬于早期隸書,很可能是在漢文帝、景帝到武帝初期這段時間內抄寫成的。根據1號、2號墓是漢武帝初年的墓葬推斷,竹簡成書應在這之前,也就是漢文帝、景帝時期,或還應更早。
銀雀山漢簡根據長短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銀雀山1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竹簡分長簡和短簡。長簡兵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晏子》《六韜》《尉繚子》《管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證和論兵文章等先秦古籍及陰陽、時令、占候、相狗、作醬等雜書。簡的長度為27.6厘米,寬0.5~0.9厘米,厚0.1~0.2厘米。按漢尺23厘米為1尺計算,應屬1尺2寸簡,又稱為“尺二簡”或“尺書”。從竹簡上留下的編繩痕跡看,分三道編繩,簡中部一道,兩邊各一道,上、下各留出1~2厘米的天頭地角。竹簡是先用繩編聯成冊后,又用毛筆蘸墨寫成。每簡寫一行,每行字數不等,一般在35個字左右,多的有40余字,少的僅幾個字。
第二類是銀雀山1號西漢墓中出土的《天地八風客主五音之居》占卜類雜書。簡的長度為18厘米左右,寬度為0.5厘米左右。按漢初尺度折算應為“8寸簡”,只有兩道編繩,兩端各留2厘米的天頭和地角。大致將全簡分為三等分,篇文頂行,不留頭。
第三類是銀雀山2號西漢墓出土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共計32枚。簡的長度為69厘米,寬度為1厘米,厚度為0.2厘米,按漢尺應為“三尺簡”,用三道繩連綴,此類簡應為最長簡。若按當時禮制:國家典籍寫在最長簡上,歷譜屬皇歷,所以就寫在最長簡上了。另外,諸子百家的書寫在“尺二簡”上,民間雜書寫在最短簡上。銀雀山漢簡的尺寸是比較符合禮制規定的,但其他地方出土竹簡不完全按禮制,也有打破傳統的現象。
銀雀山簡書的篇題,有的寫在篇首第一簡簡背,或單獨寫在第一簡上,有的寫在篇尾,有些短篇的篇題寫在第一簡簡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只有篇尾篇題而無簡背篇題。1號漢墓出土一些抄列竹書篇題的木牘,大部分已殘缺,完整只有一塊,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庫法、王兵、市法、守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個篇題,中間有殘存的系繩,木牘或許是捆在簡冊外面的題鑒。
從銀雀山1、2號西漢墓竹簡看出,竹簡書發展到漢代已經達到成熟時期,不如早期簡書粗糙、寬大。竹簡制作工序從刮削、殺青、尺度、編連、書寫、收卷等工藝成熟細致。由于長期在泥土中浸泡,又受其他隨葬品的擠壓,竹簡已散亂,表面呈深褐色,字跡清晰可見,字體清整古樸、自然圓潤、隨意流暢、秀勁飄逸。在簡牘隸書未發現之前,從秦到西漢的隸書一直是個謎,曾經有“西漢無隸書”之說。自從近代大量西漢簡牘隸書的發現,這一時期的隸書墨跡昭然于世。銀雀山1號西漢墓竹簡從書體上來看,可能不是出自一個人之手,因為書體與行款也不盡一致,其書法已經呈現出帶有波磔的筆畫特征,接近東漢時期的隸書碑刻。
從書體藝術上看,漢簡字體可分為三類,每一類中又包含著各種不同的字型。
第一類是以《六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為代表的縱勢漢隸,它是一種篆書向隸書演變時期過渡性字體,承襲了秦隸的風格。結構或取縱勢,或取橫勢,由繁趨簡,用筆有明顯的提、按、挑、捺筆等變化,整個字體左高右低,個別偏旁和部首的寫法仍然與篆書的筆法相同,但多數字體已經打破了篆書象形化的結構,圓轉對稱定型化的線條逐漸減少,更多的則出現了隸書的特征。一簡寫下來或流暢飄逸,或瀟灑自然,字體的大小、撇捺的粗重及字間的疏密錯落有致,且氣勢連貫,表現了一種古樸自然之美感。
第二類是以《晏子》和《孫臏兵法》部分篇章為代表的橫勢漢隸,字的結體特點是點畫姿態大量增多,書體以方折為主,字體態勢漸漸由篆書的縱勢向橫勢方向轉化,并趨于扁平,方塊字、扁方塊字的態勢已基本形成。在用筆上,筆畫伸縮有致,橫畫呈微波,有的顯露出蠶頭燕尾、一波三折;豎畫取直,橫折一般呈方折,豎折一般是連筆圓轉。左右結構的字,一般左邊比右邊要寫得小;上下結構的字,一般上邊要比下邊小;撇磔處以弧線與夸張見長。整體飄逸秀美,襯托出行款;字距間的字勢起伏,字的整體結構工整地呈右上仰斜趨勢,宏觀上給人一種美的享受。
第三類書體形式是以《孫子兵法》《尉繚子》的某些篇章為主,表現出字體態勢與書寫手法完全不同,整體結構既不規整,也不似草率;字體態勢縱橫交錯,橫、豎、轉折都保持圓轉的態勢,橫畫一般平直無微波,豎畫多短斜,書寫較圓滑流利,字的整體結構不規整地呈右下傾斜趨勢。
隸書產生于戰國末年,極盛于東漢時期。戰國時期是文字大發展、大變革時期,在文字發展史上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啟秦篆和隸書,基本上保存了當時通行字體的本來面目。秦簡是用古隸書體寫的,字形略大,文字的用筆已減少了盤屈,打破了篆書對稱端莊的格調。秦統一后,實行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輪”的措施,促進了地域文化的互相匯聚和融洽,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為漢隸、草、楷、行等字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漢正是我國文字由篆書轉變為隸書的過渡時期,簡文雖為隸書,但仍保留了篆書的風格,字體呈橫勢,它將小篆線條的圓轉變為方折;用筆出現提按輕重、撇磔分張的變化,為楷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西漢時期隸書以拙樸勝,多見于簡帛木牘,書法形態更接近于古隸;東漢隸書成熟,橫畫蠶頭燕尾、一波三折,結體工整規范是字體的顯著特點,就其書體而言,楚簡基本是用篆體書寫的。漢代簡牘的整體字形更趨于方形或扁方形,用筆有輕重徐疾的痕跡,某些橫畫已具有了蠶頭燕尾的雛形,改變了古隸無波的狀況,運筆左施右突,能收能放,表現了古樸的美感。
銀雀山漢簡書體堪稱竹簡書體的精華,書體表現出由古文字階段向今漢字階段改革、發展、演變的過程,可謂秦漢時期隸書的典范,被書法家稱為古今漢字的分水嶺,在古文字研究和書法藝術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堪稱竹簡之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