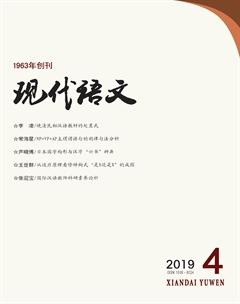包山楚簡《疋獄》84簡補(bǔ)釋
黃雪嫚



摘? 要:摘? 要:包山楚簡是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包山二號墓中的一批竹簡,新見字遠(yuǎn)超此前出土的楚簡,使得楚系文字總量激增,為楚系文字的進(jìn)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很多學(xué)者都對《疋獄》84號簡字進(jìn)行過考釋,結(jié)論并不一致。通過對包山楚簡“余”旁系列字形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豎筆穿透”比“橫畫上曲”更具有說服力,這兩個字中間豎筆明顯是穿透的。同時,根據(jù)對戰(zhàn)國時期其他楚簡中的“余”系列字和“宗”系列字的分析結(jié)果,可以推斷,這兩個字形的右半部分應(yīng)釋為“余”。因此,包山楚簡《疋獄》84號簡的姓氏疑難字應(yīng)釋為“徐”(或“?”),而非“”。
關(guān)鍵詞:包山楚簡;《疋獄》;徐
一、引言
包山楚簡,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荊門市包山二號戰(zhàn)國楚墓,計有278枚竹簡和1枚竹牘。包山楚簡新見字遠(yuǎn)超此前出土的楚簡,使得楚系文字總量激增,為楚系文字的進(jìn)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包山楚簡按照內(nèi)容可以分為文書簡、卜筮祭禱簡、遣策三大類,其中,文書簡又可分為有篇題的文書簡和無篇題的文書簡兩種,《疋獄》可歸入有篇題的文書簡一類。《疋獄》即記獄,是關(guān)于起訴的簡要記錄。《疋獄》類竹簡共23枚,即從80號到102號,本文要討論的第84號簡就屬于《疋獄》類。
有關(guān)第84號簡的內(nèi)容,經(jīng)過學(xué)者們的共同討論,絕大部分都有了確定的釋文,其簡文如下:
荊夷之月己醜之日,盧人之州人陳德訟聲夫人之人□漸、□未、謂殺其兄臣。正義強(qiáng)職之。秀期為李。
上面“□漸、□未”中的“□”字,就是本文重點(diǎn)探討的問題。對于此字,張守中、巫雪如、許全勝、白于藍(lán)、劉信芳、李家浩、朱曉雪[1](P78)等學(xué)者都做過考釋。學(xué)者們一致認(rèn)為,此字應(yīng)為姓氏字,不過,在具體釋讀時,產(chǎn)生了一定分歧。白于藍(lán)、李家浩將此字釋作“?(徐)”,其他學(xué)者認(rèn)為應(yīng)該釋為“”。由此可知,84號簡中該姓氏疑難字的主要分歧點(diǎn)是在于:除去“邑”字旁,另外部分是“余”,還是“宗”?下面將通過對包山楚簡所出現(xiàn)的帶有“余”旁的字與其他楚簡中有“余”旁的字的形體進(jìn)行對比,并參以楚地出土的徐國器物銘文,來說明本文將此字形釋作“?(徐)”的原因。
二、包山楚簡之內(nèi)證
通過考察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2](P14)、李圃《古文字詁林》[3](P665)與湯余惠《戰(zhàn)國文字編》[4](P57)等相關(guān)文獻(xiàn),發(fā)現(xiàn)包山楚簡中涉及到“余”字字形的字共有26個。具體如表1所示:
觀察以上諸列字形,可以看出,包山楚簡中“余”字的寫法并不嚴(yán)格統(tǒng)一,但其基本特征還是有跡可循的。李守奎先生(2010)認(rèn)為,在出土的楚文獻(xiàn)中,“余”字與“宗”字有兩個顯著的區(qū)別特征:一是豎筆穿透,二是中間橫畫上曲[5]。就表1來看,第一個特點(diǎn)是很明顯的,26個“余”旁字形中,“豎筆穿透”的有24個,只有兩個字形豎筆沒有穿透。不過,第二個特點(diǎn)“中間橫畫上曲”就不具有典型性,在26個字形中,“橫畫上曲”的只有5個。就此而言,“中間橫畫上曲”似乎不能作為判斷“余”字的一個可靠標(biāo)準(zhǔn),起碼在包山楚簡中的情況是這樣。
再考察《包山楚簡文字編》《古文字詁林》與《戰(zhàn)國文字編》等相關(guān)文獻(xiàn),發(fā)現(xiàn)包山楚簡中涉及到“宗”字字形的字只有一個,即72號簡的。值得注意的是,學(xué)界對此字的釋讀也有分歧。這一姓氏用字過去大多釋為“”,白于藍(lán)從林澐說改釋為“?”,但并沒有得到大家的普遍認(rèn)同。李守奎(2010)也認(rèn)為,該字應(yīng)釋為“?”,理由是楚文字中“余”“宗”二字形近易混,“余”字的豎畫常常不穿透,只有橫筆上曲還保留著①。不過,根據(jù)上文對包山楚簡中所涉及到的“余”旁系列字形的統(tǒng)計分析,可以得知,“豎筆穿透”這一特征顯然比“橫畫上曲”更具有說服力。因此,李先生的這一觀點(diǎn)值得商榷。
在84號簡中出現(xiàn)的姓氏疑難字的具體字形如下:
三、戰(zhàn)國時期其他楚簡之輔證
通過考察張守中等《郭店楚簡文字編》[6](P12)、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編》[7](P70)、張新俊等《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8](P32)、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9](P44-45)、《古文字詁林》與《戰(zhàn)國文字編》等相關(guān)文獻(xiàn),發(fā)現(xiàn)除包山楚簡外的其他戰(zhàn)國楚簡中“余”字的字形共有40個。具體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上海博物館所藏楚國竹書中含有大量的“余”字,再加上新蔡葛陵楚簡和郭店楚簡中的“余”字,我們可以通過它們來大致推斷戰(zhàn)國楚簡中“余”字的字形特點(diǎn)。
在表2的40個“余”字中,除去三個字形漫漶不清的,其余37個均比較清晰。其中,“余”字形下面再加斜筆,或左曳或右曳,或加“口”等飾符的有31個;不加飾符的有6個。在31個加飾符的“余”字中,中間豎筆沒有穿透的有5個,即(上博三·中弓5·6)、(上博三·彭祖6·22)、(上博五·姑成家父9·54)、(上博三·彭祖3·10)、(上博三·彭祖5·21)。在6個不加飾符的“余”字中,只有(上博三·中弓5·6)的豎筆是沒有穿透的。也就是說,在較為清晰的37個“余”字中,中間豎筆沒有穿透的僅有6例,只占總數(shù)的16%。這與李守奎(2010)所說的“‘余字的豎筆常常不穿透”的情況并不相符。值得注意的是,中間豎筆沒有穿透的“余”字均出自上海博物館所藏楚國竹書,其中,字形下面無任何飾符且中間豎筆不穿透的,只有1例,這在其他楚簡中從未出現(xiàn)過①。通過以上的字形對比,我們認(rèn)為,一般情況下,楚簡中“余”字字形的中間豎筆是穿透的;就沒有豎筆穿透的“余”字而言,可能如李守奎所推測的那樣,因?yàn)椤坝唷薄白凇倍值男误w太近,所以就在“余”字下增加一斜筆,或左曳或右曳。
關(guān)于“余”字字形中間橫畫是否上曲這一問題,從表2可以看出,在40個“余”字中,除去5個無法辨認(rèn)其中間橫畫外,其他35個“余”字中只有兩例是平直的,而且這兩例下面還有飾符。就此而言,這里所得出的結(jié)論與李守奎(2010)對楚國出土文獻(xiàn)中“余”與“宗”的有關(guān)分析較為符合,卻與上文對包山楚簡“‘豎筆穿透這一特征顯然比‘橫畫上曲更具有說服力”的判斷并不完全一致。不過,這也只能說明李先生對于出土楚國文獻(xiàn)中“余”“宗”的整體判斷比較可靠,至于《疋獄》84號簡“余”字的中間橫畫問題,還需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我們認(rèn)為,其他戰(zhàn)國楚簡中的相關(guān)字形特征,實(shí)際上只能作為判斷包山楚簡字形的參考證據(jù),而不能作為確證。因?yàn)槌喌那闆r十分復(fù)雜,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楚簡書寫情況并不完全相同,有時甚至區(qū)別很大。劉紹剛《楚簡書法概論》從書體類型的角度對楚簡進(jìn)行了深入分析,他認(rèn)為:1.曾侯乙簡符合戰(zhàn)國早期書法的特征,形體修長;2.包山楚簡書寫草率,和天星觀楚簡、楚帛書一樣,開啟了行草書的用筆;3.郭店楚簡受晉系書法風(fēng)格影響,繼承了晉系青銅器銘文中富于裝飾味道、字形趨于整飾的筆法;4.上博簡中的《孔子詩論》和《周易》簡皆書寫規(guī)范,起筆、收筆很在意,有藏鋒、回鋒的意味,形體扁平[10]。可以說,無論是從包山楚簡“余”旁系列的分析來看,還是從戰(zhàn)國時期其他楚簡“余”字的分析來看,“余”字都具有“豎筆穿透”的顯著特征。將這一特征應(yīng)用于《疋獄》84簡中的“”“”,也可以判斷二字的右邊部分應(yīng)釋為“余”。
筆者再次考察了《郭店楚簡文字編》《望山楚簡文字編》《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古文字詁林》與《戰(zhàn)國文字編》,發(fā)現(xiàn)在上述文獻(xiàn)中,僅《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中有“宗”字出現(xiàn)[9](P373),其他楚簡文字編中均不見記錄。在上海博物館所藏楚國竹書中,“宗”字字形共有11個。具體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上博簡五·兢建內(nèi)之2號簡的字形較為模糊,其余楚簡中的“宗”字字形均可辨認(rèn)。在這10個“宗”字字形中,其中有3個中間豎筆是穿透的,有2個中間橫畫是上曲的。由此可知,楚簡中“宗”字的字形一般是中間豎筆畫不穿透,中間橫畫平直。不過,這些特點(diǎn)也都是相對而言的,并非一成不變的。
四、從出土徐國資料中看“徐”之歷史
有關(guān)徐國的歷史,宋人修撰的《新唐書·帝相世系表》曾有簡要的敘述:“徐氏出自嬴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復(fù)封其子宗為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禹,為吳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對徐國的歷史事實(shí),很多當(dāng)代學(xué)者都進(jìn)行過詳細(xì)的考證與系統(tǒng)的論述,這里不再贅述。大體上說,在春秋時期,徐國正處于由盛轉(zhuǎn)衰乃至滅亡的階段。這一時期,大國爭霸,戰(zhàn)爭頻仍,徐國在楚國、齊國、吳國三個大國的夾縫中勉強(qiáng)存活。春秋初年,徐國在與齊國交好的同時,也受到齊國和楚國的壓迫。春秋中后期,在吳、楚兩國中間也是進(jìn)退維谷,在公元前512年,被吳國所滅。據(jù)《左傳·昭公三十年》記載:“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zhí)鐘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發(fā),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從現(xiàn)有的地方史料和考古資料來看,徐國被吳國滅亡后,徐人曾向不同的地方逃亡,其中徐國國君章禹率領(lǐng)群臣和百姓投奔楚國,楚王將其安置于楚地,即現(xiàn)在的江西北部一帶。下面就結(jié)合在楚地出土的徐國器物,對亡國后徐人在楚地的活動情況進(jìn)行一些介紹。
總的來說,迄今為止尚未發(fā)現(xiàn)一座完整的、可以確知為徐國的墓葬。可以確定為徐國的青銅器有十幾件,但多為傳世品,真正考古發(fā)掘的十分有限。即使是科學(xué)發(fā)掘的徐器很多也不出于徐國本土,而是散見于山西、江西、湖北、浙江、江蘇等省。據(jù)統(tǒng)計,在江西高安曾出土鍴、鐘、鐸等9件徐器;在江西靖安縣水口鄉(xiāng)出土輿盤、爐盤、枓3件徐器;在湖北襄陽曾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等。
可以看出,曾作為徐人安置地的江西北部是徐器出土的集中地。在江西高安出土的9件徐國器物中,有一件的銘文是“徐王屯之鍴”,另一件的銘文是“徐王義楚擇余吉金自作祭徐”[12](P68)。在江西靖安縣水口鄉(xiāng)出土的3件徐國器物中,兩件有銘文,輿盤的銘文為“徐王義楚,擇其吉金,自作輿盤”,爐盤的銘文是“雁(偃)君之孫徐令者旨型,擇其吉金,自作爐盤”[13]。據(jù)史籍記載,徐王屯右、徐王義楚都曾被楚國所執(zhí);再結(jié)合出青銅銘文,可以推知,徐國滅亡后,徐人曾長期在今江西高安、靖安一帶活動。除了地下的出土資料,我們還可以從一些歷史文獻(xiàn)史及地方史料中找到相關(guān)的蛛絲馬跡。比如《漢書·地理志》有“豫章郡余汗縣之北有余水”的記載,“余”“徐”二字古為通假字,這一材料也間接說明了此地在漢代以前就已有了徐人的蹤跡。晉代張華《博物志》曾提到:“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這位徐神可能也與徐人遷居此地有一定關(guān)系。南昌《大塘徐氏族譜》更是明確記載:“徐子章羽為吳所滅,偃王子孫遂遷入江西……世為南昌著姓。”這也從側(cè)面說明了徐國滅亡后,的確是有一部分徐人逃亡到了江西,并在這里長期生存。
另外一處徐器出土的集中地是在湖北襄陽、荊州一帶。1973年,在湖北省襄陽縣余崗大隊發(fā)掘了一批春秋至戰(zhàn)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大批器物,其中有一件斷為六截的劍,上面刻有銘文曰:“徐王義楚之元子羽擇其吉金自作用劍。”[14]羽,即徐王義楚的嫡長子章禹,也就是投奔楚國的亡國之君。在荊州江陵也曾出土徐國銅器“沇兒鐘”[12]。清人周懋琦、劉瀚《荊南萃古編》收錄有“王孫遺者鐘”,作者說該器“得之宜都山中”,即今天湖北宜都一帶,郭沫若先生認(rèn)為這是一件徐國銅器,這一觀點(diǎn)也得到學(xué)界認(rèn)可。值得重視的是,還有一件徐器“沇兒镈”,據(jù)清人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云:“器出荊州”,也就是包山楚簡的出土地附近。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徐國被吳國滅亡之后,許多徐人在國君章禹(羽)帶領(lǐng)下投奔楚國,并在楚地繁衍生息,這一點(diǎn)也為楚地所出土的徐國銅器所證明。
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況下,戰(zhàn)國時期楚簡中“余”和“宗”字形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為:“余”字字形的中間豎筆是穿透的,而“宗”字字形的中間豎筆不穿透;“余”字中間橫畫上曲,而“宗”字中間橫畫平直。這一結(jié)論與李守奎的看法實(shí)際上是一致的。具體到包山楚簡來說,通過對包山楚簡“余”旁系列字形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橫畫上曲”這一特征的表現(xiàn)并不明顯,也就是說,“豎筆穿透”比“橫畫上曲”更具有說服力。《疋獄》84號簡中出現(xiàn)的姓氏疑難字“”“”,中間豎筆明顯是穿透的,而且其兩邊支撐與中間橫畫的間架關(guān)系,與第145號反“”(“舍”)、第137號反“”(“”)的字形基本相同。同時,根據(jù)對戰(zhàn)國時期其他楚簡中的“余”系列字和“宗”系列字的分析結(jié)果,可以推斷,這兩個字形的右半部分應(yīng)釋為“余”。從相關(guān)史料的記載與楚地出土的徐國銅器及其銘文中,可以推知徐人在徐國滅亡后,曾長期在楚地活動。綜合以上因素,我們認(rèn)為包山楚簡《疋獄》84號簡的姓氏疑難字應(yīng)釋為“徐”(或“?”),而非“”。值得一說的,還有包山楚簡72號簡的“”字,大多數(shù)學(xué)者將這一姓氏用字釋為“”,白于藍(lán)從林澐說改釋為“?”,李守奎也主張釋為“?”。不過,依據(jù)本文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此字應(yīng)釋作“”。
參考文獻(xiàn):
[1]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2]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3]李圃.古文字詁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4]湯余惠.戰(zhàn)國文字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5]李守奎.出土楚文獻(xiàn)姓氏用字異寫現(xiàn)象初探[J].中國文字博物館,2010,(2).
[6]張守中,郝建文,張小滄.郭店楚簡文字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7]程燕.望山楚簡文字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7.
[8]張新俊,張勝波.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M].成都:巴蜀書社,2008.
[9]李守奎,曲冰,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0]劉紹剛.楚簡書法概論[A].湖北省書畫研究會,華中師范大學(xué)楚學(xué)研究所編.全國楚簡帛書法藝術(shù)研討會暨作品展·論文集[C].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11]李修松.徐夷遷徙考[J].歷史研究.1996,(4).
[12]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7.
[13]江西省歷史博物館,靖安縣文化館.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國銅器[J].文物,1980,(3).
[14]沈湘芳.襄陽出土徐王義楚元子劍[J].江漢考古,1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