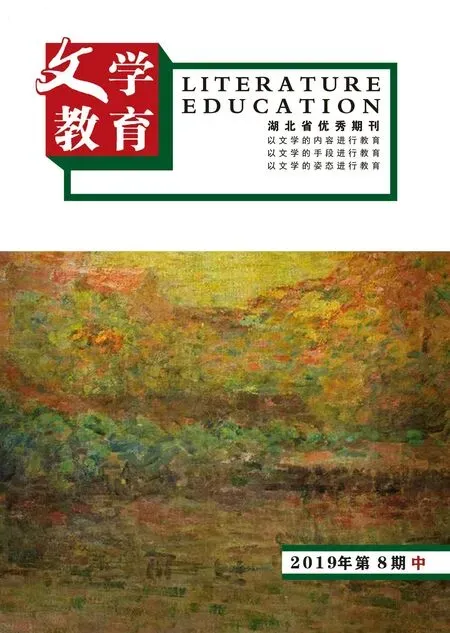文本細讀在地方本科院校教學中的實踐價值
沈春鵬
伴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網絡已經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當然也影響著我們的閱讀方式,從傳統的紙質圖書閱讀轉向了電子圖書閱讀。借助新媒體技術閱讀方式大面積普及,其優點是不言而喻的,方便了圖書資源的尋找,而且閱讀時間、地點不受限制,但是其缺點也頗為明顯,于是“淺顯化閱讀”、“碎片化閱讀”等一系列問題也應時而生。這些新的閱讀方式對不同人群產生的影響當然也是各不相同,對于非文學專業或者非文字工作者而言,他們的文學閱讀動機主要以怡情悅性為主,所以不必求其深刻性和全面性。而對于專門從事文學學習和研究的人,深度閱讀則是非常必要的。各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作為培養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字工作者的搖籃,文本閱讀一直是各門課程較為重視的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切實有效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閱讀效率以及閱讀深度,作者結合多年的教學經驗,從實際出發嘗試探討地方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學類課程細讀問題,以期重視和落實文本細讀的重要地位,并對學生細讀文本的方式給予指導。
一.地方本科院校學生閱讀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一)數字化閱讀的雙面性
筆者針對我院大學生閱讀現狀共發放問卷300份,收回問卷共計295份,回收有效率達98%。此次問卷調查所選擇的調查樣本中,男生共125名,占比41.6%,女生共175名,占比58.4%;參與調查的大一到大四學生各75名,分別占比25%,選取相同的人數是方便所得數據的比較。

由圖1-1可以看出,大學生進行閱讀以手機為主要載體,這與手機使用在大學生的完全普及,以及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密切相關。我國第十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結果顯示,2017年,中國人均電子書的閱讀量達到10.1本,數字閱讀用戶量持續上漲,總人數已接近4億。其中,青年數字閱讀用戶占比超7成。數字化閱讀方式在拓展閱讀渠道,提升閱讀興趣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想象。
第一,弱化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在閱讀書目選擇原因一題,76%的同學選擇網絡推薦。任何一個編者推薦一本圖書的時候,總會融入主觀因素,這些主管因素對于獨立思考能力還未完善的大學生而言,很容易成為先入為主的固定觀念。同時,通過數字化設備閱讀,讀者在遇到閱讀障礙的時候,不愿意主動深入探究,反而轉向網絡查找。
第二,部分學生出現隨意性的淺顯閱讀。對于當代大學生而言,微信、微博、各類APP等幾乎演變為生活必需要,盡管這些途徑都可以幫助閱讀,但從根本上看這些方便移動的電子設備,使學生貌似一直處于隨時可閱讀的狀態,造成這種閱讀模式的原因有很多種,比如閱讀地點的隨意性,文本選擇的簡易型,閱讀設備自身的問題等等。
就閱讀地點,筆者針對調查問卷做了統計,如圖1-2所示,學生多選擇在宿舍閱讀。在訪談的過程中,筆者了解到學生做作業或者復習的時候多會選擇自習室,而閱讀則會選宿舍,原因主要集中在氣氛輕松,可隨意活動,認為閱讀不需要安靜的場所等。眾所周知,宿舍主要的作用并非提供學習的場所,學生在宿舍閱讀很容易中斷,這種間歇性的、不完全的閱讀方式必然會嚴重沖擊著學生探究思維能力的形成,導致學生無法深入的理解知識內容和形成系統化的知識結構。就閱讀內容的選擇而言,近6成的學生閱讀內容選擇是隨機的,隨機選擇的結果就是偏愛篇幅短小的或者娛樂性較強的書目。

(二)學生閱讀能力有待提高
2016年,《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全民閱讀推廣工作將進入重點推進階段,建設“學校以閱讀為教育主軸,國民以閱讀為生活方式,城市以閱讀為文化形象和氣質,國家以全民閱讀事業激發國民文化凝聚力、國家軟實力的國度”,已成為國家全民閱讀推廣的努力方向與目標。[1]
作為內蒙古自治區西部唯一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如何結合閱讀活動的推進,更好傳承與保護民族文化、為民族地區培養人才、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是每一個高校老師的時代使命。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學生與其他高校相比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少數民族同學在上大學之前,主要受本民族文化影響較深,所以上大學后,需要花費較長一段時間適應和其他民族同學相處。而且少數民族同學漢語水平參差不齊,筆者所在學校很多專業招收了蒙古族學生,專門開設一個班級,筆者在授課過程中,注意到有的蒙古族學生閱讀漢語作品毫無障礙,有的學生只會說簡單的詞匯,稍微復雜一點便不能理解,比如講《邶風·靜女》時,個別同學不能理解“搔首”一詞。所以需要提高其閱讀能力。
(三)地方本科院校在轉型發展過程的舉措
自2015年10月以來,教育部發布《關于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國家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將會有一半以上的地方院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同時,在《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中強調“要建立以提高實踐能力為引領的人才培養流程,構建‘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作為一所處于轉型發展中的地方性高校,在人才培養模式上發生了改變,如從傳統的2.5+1模式,3.5+1模式改為2+1模式,3+1的人才培養模式,提升實踐環節的比重,課下學生閱讀就是一一項重要的實踐環節。所以筆者就把讀書筆記作為學生考核的一項組成部分,從而促進了閱讀能力的提高。
二.地方本科院提高學生文本細讀能力的必要性
筆者在授課及與學生的日常溝通中發現,學生并非完全沒有閱讀的興趣,而是找不到正確理解作品靈魂深處的鑰匙。總是淺嘗輒止,走馬觀花,久而久之,喪失了閱讀興趣,學生在分析作品的時候,慣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這個批評方法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也容易導致泛泛閱讀,缺少對字詞句的深入體驗。通過文本細讀提升文字感受能力、把握能力和分析能力,一方面增強了職業對于文學活動的研究必須得兼顧四者才可能獲取一個比較全面客觀的結論。[2]
第一,理論聯系實際
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的目的是培養應用型人才,以培養應用能力為目標,有利于科學合理的知識構建和能力體系;課程內容與職業需要對接,教學過程與職業規劃對接;以產教融合為紐帶,從而實現專業與產業對接,我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的人才主要從事教師、公務員和其他事業單位的文員工作,這些工作都需要有深厚的閱讀功底。筆者在課堂上曾留過閱讀法國作家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作為課后作業,在討論的時候,當問到學生有沒有注意到小狐貍對儀式的解釋,近五成的同學表示不記得,注意到的同學也沒有深入思考。而仔細品味小狐貍對儀式的解釋“它就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他時刻不同。”可以喚醒我們內心被平凡生活掩蓋的珍貴感,“文學語言遠非僅僅用來指稱或說明什么,它還有表現情意的一面”。[3]在實踐課堂,筆者曾選三年級上冊語文第五課《鋪滿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作為分析對象,學生基本都可以注意到金色、落葉、明朗等詞語。卻普遍忽視了“它們排列得并不規則,甚至有些凌亂,然而,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一句中的“更”字。平日,以整潔為美的教育貫穿于小學生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個彰顯凌亂之美“更”字別有一番韻味。由此可見,培養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文本細讀能力的必要性,只有將文本細讀法貫穿于文學史課、理論課以及語言的始終,學生只有讀懂了作品,才愿意主動了解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思潮以及各類詞語的使用。
第二,因材施教
結合所授課程及班級的基本狀況,制定相應的指導方法。比如對于專科班學生而言,他們在校時間較短,多數同學將來主要從事小學教育或是幼兒教育,所以主要引導他們細讀字詞,品味文章中字詞的獨特性,注意文章的語境。“引導學生設身處地去感受體驗,重視對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體感知與把握,注意作品內涵的多義性和模糊性,鼓勵學生積極地、富有創意地建構文本意義”。[4]在閱讀文本的選擇上,可以將教材課文作為分析對象。如古代文學史課程在講到杜牧的時候,可以讓學生細讀三年級上冊的《山行》作為范文,第一學期也正值金秋時節,結合生活語境,通過互文解讀,可更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感和把握文本的深層意蘊。而本科生無論在將來的職業規劃,還是,培養目標與專科生都有差異,所以在閱讀對象的選擇上勢必要擴大,在實踐課堂上范文選擇應以初高中文本為主要對象。除了對字詞的重視,加大審美素養的提升。在具體方法上,可以借鑒王卓慈教師的觀點“教師通過文木細讀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從文學作品的閱讀中上升到理論思考,再運用相應的文學理論對作品進行剖析和評論”、“從而使其能夠對接觸到的文學作品有更深層次的理解。”[5]朱立元先生認為個體閱讀“從原有的期待視界前結構出發,在與作品召喚結構的具體接觸、碰撞中,通過語符-意象思維的作用,調動讀者感性經驗積累和想象力,對作品空白與不確定性行‘具體化’與重建,達到意象意境意義的初步感性總合在此基礎上,介入主體反思,設定具體的‘問答邏輯’,通過辯證的‘對話’深入作品的內層,理性地把握并闡釋作品的底蘊,最終達到讀者視界與作品視界的溝通與交融。”[6]
第三,加大雙語教師的培養,切實提高學生對文本細讀的能力
民族地區地方本科院校,教師和少數民族同學有效溝通是大家都較為關注的一個話題。我院自2012年升本以來,除了蒙古語言文學系,其他系部也陸續招了部分以蒙語授課的考生,這些學生漢語水平參差不齊。來到大學之后,部分教師們主要以漢語授課,所以在深入分析文本時顯得尤為困難。筆者認為,解決這個矛盾,首先可以鼓勵蒙古族同學多參加社團,通過課外活動來提高漢語表達能力。其次,加大雙語教師的引進,雙語教師無論在日常學生工作,還是授課都有獨特的優勢。尤為關鍵的是要加強自身教師隊伍建設,可以有意識的培養雙語教師,選取有意愿學習蒙語的教師,以青年教師為主要培養對象。雖然學習一門語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千里之行,積于跬步。教師掌握了少數民族語言,可以引導學生地分析作品,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小結
文本是“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系的一個極其復雜的組合體”,[7]文本細讀是學生感知文字,品味意境,提升審美能力的重要途徑,這一閱讀過程伴隨著學生積極思考和審美情感主動投入,對培養學生的良好閱讀習慣和分析文本的能力頗有益處。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通過文本細讀,讓學生切身體會到文詞之美,以此激發閱讀興趣,從而提升自身和職業素養,而作為高校教師結合自身所授課程特點,積極探索文本細讀的應用方法是一項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