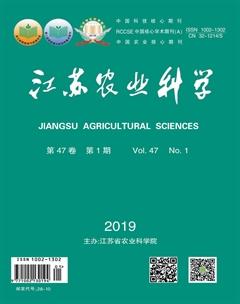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構建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鄭宇 王哲 鄭純
摘要:隨著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以及人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逐步增強,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進行合理的生態補償從而提升發展質量是人們一直以來追求的目標。公益林強大的正外部性產生的價值難以準確地進行經濟衡量,因此在梳理我國公益林生態補償現狀與問題的同時,應結合國外先例的經驗總結,最大程度地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架構,劃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責界限,形成公益林生態補償造血機能與自我發展機制。
關鍵詞: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完善;凈化空氣;涵養水源
中圖分類號: F307.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9)01-0326-04
眾所周知,公益林具有凈化空氣、涵養水源、保持水土以及提供生物多樣性等功能,這些準公共生態服務難以通過市場機制體現經濟價值。因此,有必要制定和實施公益林生態服務補償制度,促進公益林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國外公益林生態補償起步較早,補償模式主要有2種:一是政府參與模式,包括建立生態補償基金、設立生態補償稅、不同區域轉移支付以及擴展到不同流域合作補償等[1]。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政府財政轉移與主導,由于政府機構實施范圍廣、政策目的多樣化,具有核算以及支付方式規范統一、快速便捷等特點,但是效率較低也造成了生態環境不同程度的二次損害[2-5]。二是市場參與模式,包括建立綠色償付制度、生態配額市場配置、統一建立生態標簽體系、設立排放許可證交易和國際碳匯交易[6]。該模式的主要特點為生態服務使用者或受益者付費體現出自覺性,并且利用中介機構管理運作,實施范圍集中,目的明確,補償方式多樣化,補償效率較高[7-8]。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是一種生態資源環境價值“市場經濟化”的公共制度約束安排,通過對公益林生態利益的二次分配,建立了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之間的矛盾協調機制[9],這些生態補償的實踐由于法律規范健全、政府支付能力較強、產權制度完善、市場機制成熟、多方主體參與等內外部因素完善而取得了一定成效[10]。
目前國內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生態補償機制3個階段的界定分別為前期財政扶持的輸血階段、中期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階段、最后的利用市場造血階段[11-12]。其次是對于生態資源評估方法的探究,潛在的生態價值估算以及通過修復已破壞的生態植被的資金投入核算[13],此外還有補償資金來源等問題。有學者指出,補償模式的設計應與生態服務的公共物品屬性相結合[14-15],但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補償的一個或幾個方面,對補償機制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影響卻較少涉及[16]。受害者和受益者地域不同等問題,加劇了補償資金具體核算的復雜性,加上生態林補償標準制度尚未成熟[17],也缺失法律法規營造良好的外部協助環境。從以上文獻可以得出,國外研究主要是主體角度和制度角度,并著重于具體的案例分析。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機制和外部影響因素,以及宏觀政策方向。鑒于此,本文在整理我國公益林補償現狀的基礎上,學習和借鑒國外公益林補償措施的經驗,為探索建立中國特色公益林補償模式提供政策建議。
1 公益林生態補償的起源與發展
生態補償的理論基礎為公益林生態系統具有正外部性,公益林生態補償是彌補公益林隱性價值,同時糾正公益林生態系統的掠奪性開發,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是維護公益林生態系統正常運行的關鍵一環。生態補償的實施可以追溯至1976年德國開始的Engriffs regelung生態補償政策,之后1986年美國開始實施零凈損失政策,對促進生態環境補償起到了示范作用。
我國的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制度于2004年正式建立,補助標準為每年75元/hm2。2010年起,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提高到每年150元/hm2。國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不變,補償基金用于公益林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以及森林資源建檔、森林防火、林業有害生物防治、補植、撫育和其他相關支出。集體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基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集體管護支出為每年 48.75元/hm2,其中,用于管護人員勞務報酬和依法規定的政策性社會保險41.25元,用于公益林防火、林業有害生物防治、公益林監測、檔案建設、培訓、設施維護等項目支出7.5元;集體經濟組織農民的經濟補償支出每年97.5元/hm2。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基金補償農民為每年 138.75元/hm2。2013年,中央財政進一步將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提高到每年225元/hm2。2015年,提高國有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至每年90元/hm2。
近年來,我國提出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著重強調全面落實生態文明建設,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美麗中國,也是對仍處于淺層保護制度的公益林及其發展方向升級的指引。
2 公益林補償問題
毫無疑問,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制度自建立以來取得了明顯成效,為公益林面積增加起到了助推作用,但與此同時,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在實際運行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2.1 公益林補償標準偏低,公益林所有者未能獲得應有的收益
目前,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為每年225元/hm2,雖然補償標準逐漸提高,但整體而言仍然偏低,不能充分體現公益林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林農因公益林政策約束產生的經濟損失無法得到彌補,收入受到了較大的影響,也打擊了林農管護公益林的積極性。
此外,雖然政策明確了補償資金的用途及分配,各地也規定了補償資金中落實到公益林所有者的最低額,但具體的補償資金分配使用,包括公益林所有者獲得的份額以及公共管護費用、管護人員經費與比例在各地都不盡相同,公共管護及其他支出擠占補償資金的現象較為突出。
2.2 公益林補償預算及動態調整機制不完善
現行的公益林補償采用靜態預算,按照社會發展規劃、資源狀況、績效評價、生態政策、財力狀況和不同權重制定補貼金額,缺乏對經濟形勢以及社會發展現狀的動態考慮。
另一方面,公益林區劃時以生態特征為首要考量標準,忽略了對林地經濟價值差異的判斷。在實踐中,將產出水平較低和交通不便區域的次生林劃為公益林,對農戶的影響較小,農戶通過公益林補償可以彌補經濟損失,因而公益林建設的阻力較小。而成熟期的人工造林劃為公益林對農戶收入影響較大,反對意見多且相應的阻力也較大。同時,從公益林的生態屬性看,樹種結構合理、林分質量高的林地具有較高的生態價值,應該給予更多的補償,但在實踐中采取的一刀切的補償方式,降低了林農管護林地的積極性。中央和各級地方財政雖然逐年加大對森林撫育等公益林提質增效方面建設資金的投入,但仍然不足。
2.3 公益林補償資金來源單一
目前公益林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包括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的分攤,以及貸款、外資、自籌經費等渠道。其中主要依靠國家財政預算,貸款和利用外資處于起步階段,占比較小,補償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多元化的補償機制還沒有形成。籌集資金的方式也缺少市場化運作,導致補償范圍狹窄、補償水平低下以及補償方式和標準過于單一。
2.4 公益林經營利用的限制凸顯了補償機制的不足
和商品林相比,公益林的特殊性使得它缺乏流轉和抵押權力,難以獲得金融資金支持,同時,公益林的禁伐要求也嚴重影響了林農對財產的處分權。雖然禁伐政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突破,但不能解決財產變現和融資等實際問題,實際偏低的公益林補償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與商品林價值變現能力的差距,林農要求提高公益林補償資金與財政壓力的矛盾越發明顯。
3 公益林生態補償制度的國際經驗
國外的生態補償側重于2個方面:一是補償主體的甄別。通過對補償區域的環境壓力和補償者的環境目標偏好研究,區別對待不同行為主體,優化選取補償區域,提高補償效益。二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計算過程中更加注重補償差異性、社會經濟條件、補償意愿等的差異,提供的補償標準較準確地接近農戶的機會成本,符合受償意愿,降低了補償之后繼續破壞的可能性,為后續提供良好生態服務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3.1 法律制定方面
美國、德國、日本3個國家均是通過完善的森林法律體系來構建生態補償制度基本框架,采用基本法與單行立法并行的形式確定具體的補償方式、原則、范圍與實施條件,制度較為科學與完備,創造了良好的法律制度環境。
美國1985年開始的農業法案中確立了土地休耕還林保護計劃,此后,在歷次的農業法案中均明確了這一制度體系,政府對保護生態環境所放棄的耕種和被迫承擔的機會成本進行相應補償。以簽訂合同登記注冊的土地數量為準,用近些年的土地租金向農民支付租金,并分擔農民轉換生產方式過程中約50%的成本,一般合同期為10~15年。補償金完全由政府提供,在項目實施中遵循農戶自愿的原則。
德國通過《聯邦森林法》《土地整理法》和《建筑法典》確立了穩定森林面積、統一生態補償標準及維護生物多樣性于一體的森林生態補償制度框架。根據當地生態系統特點,依據森林的防護功能及游憩功能,維護和營造森林;對更變土地利用性質、采伐等做出詳細的規定,改善森林狀況、所有制結構及林道等生產基礎。
日本是亞洲實施森林生態補償最早也是世界上森林資源發達的國家之一,維護良好森林生態資源主要受益于其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確定財政補貼與金融扶持政策調控結合的補償規制,最大程度地調動了農戶保護森林生態的積極性。
3.2 補償計算方面
有關核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方法頗有爭論,將其作為生態補償標準,目前條件尚未具備,但對生態系統價值認識具有重要的意義。機會成本法是被普遍認為的可行性較高的補償方法。Macmillan等在蘇格蘭的調研結果說明,新造林生態補償標準設定與新造林地的生態服務功能的大小沒有關系,而是與新造林地的機會成本密切相關[18]。當然,確定機會成本是建立生態補償標準的難點,土地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土地覆被植被、土壤質量好壞、坡度大小、氣候變化、道路布設等因素影響,因此機會成本隨著土地的社會和自然經濟條件不同而發生巨大變化[19]。
Wǜnscher等認為,缺乏考慮地區自然資源差異性的補償必然會導致經濟補償效益的損失,所以選取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毀林帶來的風險因素以及提供生態服務的各項成本等指標來研究生態補償效益的高低,按照成本的空間差異來配置補償資金,補償效益會有所改善[20]。
此外,條件價值法是目前補償現有公共物品和生態服務價值公認的方法之一,由Davis在1963年首次建立并應用,是通過問卷詢問引導受訪者說出支付意愿或受償意愿的具體貨幣數額,進而得到公共物品補償價值的方法[21]。
3.3 支付方式方面
巴西各州收取流轉稅,規定25%分配給州政府之下的政府承擔,其中市政府稅收任務的75%按照城市占據州的總ICMS份額確定,剩下的25%按照人口數量、自然地理和經濟因素來分配,1990年開始納入生態環境因素,具體計算流程為:收集每個城市的自然保護區信息,同時根據流域保護和保護區面積計算生態補償指標,最后公布分配結果并進行效果評估。
日本在充分考慮補償主體和客體不同利益訴求的前提下確定補償金額,政府作為補償主體時,明確說明政府與地方之間嚴格按照4 ∶ 1的配比進行補償配套跟進,切實完成地方政府的主體補償責任。國家僅進行有限的補償,其他部分由具體的地區受益者來承擔。
Koh提出生態補償措施除了與污染者支付原則相關,還建議開發者支付原則作為更全面的原則,著重分析最少化破壞,補充定量和定性生態評估方法,開發者籌集補償池確保土地供應有戰略規劃,并維護國家社會安全穩定[1]。
加拿大在實踐中以生產能力的無凈損失為出發點,進行生態補償確定棲息地補償金額,使用棲息地分布和魚類種群的基線調查,實現生態棲息地的恢復。Scruton等不僅僅把單一的森林生態價值考慮在內,還涉及森林生態系統動植物多樣性的價值核算,這也啟示我們應用系統的眼光來看待森林生態價值的計算[22]。
3.4 主體參與方面
政府應積極引導市場和民間力量來參與生態補償建設,社會和民眾生態補償意識逐漸增強,生態補償從開始的被動行為演變為自覺性公眾參與行為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日本民間設立了“綠色羽毛基金”,每年由民間組織負責向日本各大財團、企業和個人籌款,為森林補償建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同時,非政府組織和社工團體等也對生態補償體系建設起到了補充作用。
市場主導型的自愿協商補償是基于科斯外部性內部化的最有效方式,然而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可能會使賠償在短期內或無法實現,同時運用市場方法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相關者意愿分析應考慮制定政府補償標準。
Yu等指出市場監管與政府管理相結合,將更好地推動補償的實施。在生態補償的運作體系中,應該使用市場調節,補償金額將由受益人的需求和付款人的供給決定[3]。在生態補償管理體系中,政府管理部門將在必要的監督管理方面作出更多的貢獻,建立現場補償監督制度,覆蓋整個補償期間的所有環節和對象。
4 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的構建啟示
公益林生態補償是生態文明思維方式的具體展現,簡言之,為生態環境服務付費。公益林生態補償是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主要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以政府調控和市場配置等經濟手段為主要方式,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根據上述國外先例經驗以及我國具體情況,提出以下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構建啟示。
4.1 加快生態補償全面立法
搭建我國公益林生態補償法律框架,在法律層面對公益林生態保護進行分類細化,把開發、補償、保護等具體情況依次列入并且落實到位,分層級對補償事項進行明文規定,為國家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掃清盲區,同時規范國家對生態保護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和有關地方人民政府生態補償資金的使用,確保其用于生態補償。國家指導受益地區和生態保護地區人民政府通過協商或者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繳納事前生態補償金,最大程度地避免公益林生態補償造成的產權糾紛和經濟問題。
4.2 完善生態補償框架
首先,補償范圍由公益林生態系統的單一領域改變為濕地、河流等生態系統的綜合補償,補償尺度從省內補償逐步到跨省補償,制定符合動態經濟發展的生態評價標準,進行合理的區間估值,科學選擇替代品衡量。
其次,結合生態補償試點,利用機會成本法和條件價值法等,對各環節涉及主體進行責任分配,倒逼產業體系轉型形成綠色產業體系,實現綠色生態與綠色發展的協調一致,成立綠色發展基金充當賠償池的“調蓄作用”,發揮政府“生態補償資金”引導和放大效應。
再次,補償方式多元化,以資金補償為主體,讓技術、物質、產業等多形式參與生態補償。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采納環境污染損失、生態破壞損失、環境質量改善效益、生態系統生態效益、環境容量資產等指標,發展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實施生態補償,切勿搞一刀切和形式主義,更要杜絕政府尋租行為,保持高效的行政效率。
最后,政府需要制定適當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進行杠桿投資,在傳統的土地利用變化和耕作實踐中扮演重要角色,調整造林活動時的市場信號,避免偏離最初的公益林生態補償目標。
4.3 營造生態補償的社會環境
在明確生態服務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之上,分析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的要素、補償方式、形式、標準和補償效率等。積極建設公益林生態補償外環境,積極宣傳生態補償的社會效益,樹立典型改革案例,同時主流媒體進行深入報道并予以高度總結評價,不斷增強民眾的生態環保意識。恢復生態功能的挑戰可能遠遠超出財政能力,科技和教育是推動調節公益林生態補償發展外環境的動力,這就需要發揮兩者的作用,積極挖掘地區生態補償潛力。
同時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機制,包括綜合協調、斷面林地考核、創新資金投入、項目管護機制等,探索小尺度生態補償標準與生態補償協調的社會意識氛圍,為公益林生態補償機制提供理論依據,為建立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態補償制度積累經驗。
參考文獻:
[1]Koh N S. Safeguards for enhanc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Sweden[J]. Land Use Policy,2017,64:186-199.
[2]Borgstrm S. Reviewing natural resources law in the light of bio-economy:Finnish forest regulations as a case study[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8,88:11-23.
[3]Yu B,Xu L Y. Review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hydropower development[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6,55:729-738.
[4]Getzner M,Gutheil-Knopp-Kirchwald G,Kreimer E,et al. Gravitational natural hazards:valuing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Alpine forests[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7,80:150-159.
[5]Maestripieri N. Dynamic simul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normative scenarios:the case of timber plantations in the southern Chile[J]. Futures,2017,87:65-77.
[6]Truong D M,Yanagisawa M,Kono Y. Forest transition in Vietnam:a case study of Northern mountain region[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7,76(SI):72-80.
[7]Mansourian S. Governance and forest landscape restoration:a framework to support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2017,37:21-30.
[8]Yovi E Y,Nurrochmat D R. An occupational ergonomics in the Indonesian state mandatory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strument:a review[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8,91(SI):27-35.
[9]Bull J W,Abatayo A L,Strange N. Counterintuitive proposals for trans-boundar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under ‘no net loss biodiversity policy[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7,142:185-193.
[10]Mohammed A J,Inoue M,Shivakoti G. Moving forward in collaborative forest management:role of external actor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socio-ecological systems[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7,74:13-19.
[11]李文華,李世東,李 芬,等. 森林生態補償機制若干重點問題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7,17(2):13-18.
[12]薄其皇. 基于機會成本的森林生態補償標準研究[D]. 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5.
[13]張 媛. 森林生態補償的新視角:生態資本理論的應用[J]. 生態經濟,2015,31(1):176-179.
[14]陳 曦. 歐盟森林生態補償制度及其借鑒[D]. 杭州:浙江農林大學,2012.
[15]蔡邦成,溫林泉,陸根法. 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的理論思考[J]. 生態經濟,2005(1):47-50.
[16]孫新章,謝高地,張其仔,等. 中國生態補償的實踐及其政策取向[J]. 資源科學,2006,28(4):25-30.
[17]米 鋒,李吉躍,楊家偉. 森林生態效益評價的研究進展[J]. 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3,25(6):77-83.
[18]Macmillan D C,Harley D,M O M.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woodl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8,27(3):313-324.
[19]Kenneth M C,Keith A,Timothy S T,et al. Opportunity costs of conservation in a biodiversity hostspot:the case of southern Bahia[J]. Envri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10(3):293-312.
[20]Wünscher T,Engel S,Wunder S. Spatial targeting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a tool for boosting conservation benefit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5(4):822-833.
[21]張 茵,蔡運龍. 條件估值法評估環境資源價值的研究進展[J]. 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41(2):317-328.
[22]Scruton D,Clarke K D,Roberge M M,et al. A case study of habitat compensation to ameliorate impacts of hydroelectric development:effectiveness of re-watering and habitat enhancement of an intermittent flood overflow channel[J]. Fish Biol,2005,67:244-260.羅 晰,周業付. 政策設計視角下蛋雞行業橫向供應鏈聯盟實現模式——以江西省為例[J]. 江蘇農業科學,2019,47(1):33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