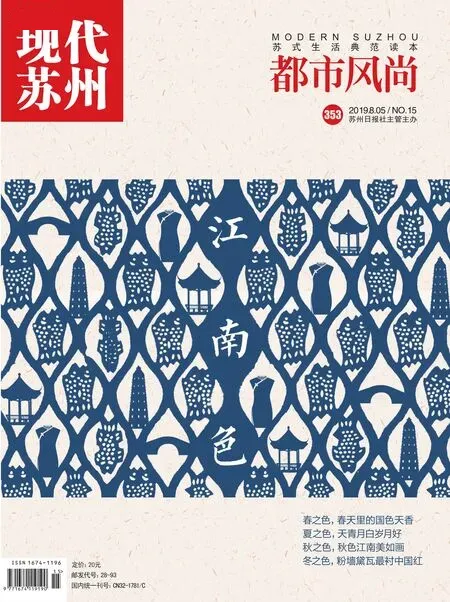詩心一片
韓光浩,筆名廣豪,東吳曲社創社會員、《現代蘇州》雜志常務副主編。著有《典范蘇州—昆曲》、《盛世流芳—蘇昆六十年》、《百工遺韻》等。
懂得點繪畫之道的都知道,太似媚俗,不似欺世。古人說,“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但是什么叫做似與不似之間的,我的理解,就是有意思。萬物都有那么一種意思,生而具有的。這種意思通常叫做精神,萬物存與世間,都有著一種精神。
這種“似與不似”的意思叫做共性,共性是你和他人的一致,也是你的作品和萬物的一致性,找到共性了,一下筆,如有萬物。這個比個性要高級多了。共性就是天生天養,最親近自然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而這個時代,遺憾的卻是個性的時代。
共性意味著做減法,用最簡單的筆法、文法來勾勒出最深刻的精神,這就是有共性的意思了。將看上去并不調和的東西,讓其得到調和,就是好的藝術境界。這和太極拳一樣,太極拳為什么能成拳中之王,不在于它的技擊,而是在于它能將不可能變為可能,四兩撥千斤,無力勝有力。人和自己合,和他人合,在與天地合二為一,戰無不勝,甚至不戰而勝,這就是一種共性的力量。所以儒家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樣的道理。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文學上的體現,就是物我一體,詩心一片。這一片詩心最典范的例子,就是唐詩。典范的意思,就是唐人對天地領悟力高。一首唐詩好像沒用什么技巧,內容也沒有特別復雜的,但其中就有一種深刻的詩性,讓后人難以模仿。就像我們看見一個人登上了山頂,但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字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維的兩個句子,“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還有一首《鹿寨》,“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太妙了。日本的陰翳美學,就是從王維手里學去點皮毛。當代人去東洋膜拜,卻不知道祖師爺在我們自己家里。這種詩性,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人體會自然的一種共鳴。形而上謂之意,形而下謂之詩。詩意,就是一種古意。古,不是古代,而是天地。
當然,唐詩是《詩經》的子孫,《詩經》里處處都有著詩意盎然。有古意,才有詩意,因為有活力。所以我們做人要充滿魅力,就要達到意這個狀態,有一種特別的味道。要腹有經典,修身齊家,格物致知,有容乃大。然后才有古意盎然,才有詩意。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都理解錯了。才,是技巧,好女子不講技巧,講的是心性。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里的句子,柔情萬種,古意盎然。十六個字,時光、空間、人事、情感、景物、心事、喟嘆,盡其中矣。古,口字上面一個“十”,不是十字架,蓋棺定論,作古之人。而是縱及千古,橫及八荒,就是宇宙,是指人在各個方向上都有認知的可能。它又是一種狀態,是一種古老的,又是日日新的狀態,是永恒的狀態。元趙孟頫,明董其昌認為最高的審美方式是“尚古”,可惜的是清代以后的人泥古不化,誤入歧途,終于望文生義地把古與新對立起來。《尚書》上講“人惟求舊,器惟重新”,將精神與物質的位置一語道破。當世變為人求新,器重舊,正好顛倒了過來。
人的心就像是一面鏡子,世界萬物都能最真實純粹的反映在心里。孟子說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如果知道了這一點,所有事情都可以坦坦蕩蕩,真正的修煉,就是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既能入乎其內,也能出乎其外。這個境界,為人做事,既有古風,又有古意,就是一片詩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