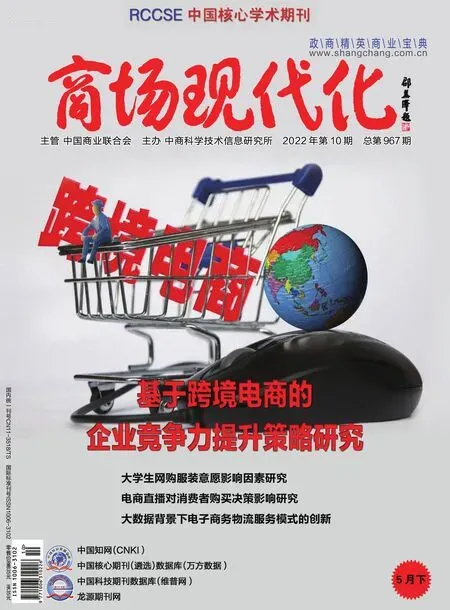國企并購行為對高管薪酬激勵的影響
李雨霏
摘 要:企業并購動因理論提出企業管理層出于私利發動企業并購,然而,對于我國的國有企業,控制權的特殊性讓人們認識到其經營目標既包括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包括承擔社會責任與獲得政治效益。本文從國企并購行為視角出發,分析了在不同股權性質的國有企業中,并購行為對高管薪酬激勵的影響。
關鍵詞:國有企業并購;高管薪酬;控制權與激勵沖突
一、引言
雖然國有上市公司的產權具有特殊性,但并不影響其在資本市場上的影響力。近年來,國有企業在不斷進行模式的創新與突破,許多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也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其中,負責人的選聘和考核標準、薪酬的分配方式改革以及兼并重組等企業重要內容都在改革試行范圍內。從理論上來講,這些改革和非國有企業極其不同,一是國有企業所具有的雙重代理問題是非國有企業所不具備的。即相比于傳統的“經濟人”身份,還有另外一重“政治人”身份,存在高管晉升空間,(鄭志剛等,2012);二是控制權與非國有企業不同。國有企業股權集中度高,且大股東多為政府,這樣特殊的背景使得國有上市公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在戰略決策及社會責任等方面有很大差距。研究國企并購對高管薪酬的影響,除考慮傳統的理論外,還要結合具體的情況進行分析:首先,國有企業的并購行為是否會對高管薪酬變動產生影響?其次,將國企按股權性質進行詳細劃分后,是否會影響高管的薪酬以及影響效果如何?最后,國有企業并購對股權激勵的實施效果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文本將對以上問題進行分析。
二、文獻回顧
從上世紀60年代起,西方的一些學者對企業的并購動因和之后的績效兩方面進行研究。在并購動因方面,Rhoades(1983)對比了20世紀初期與60年代的并購浪潮,提出了“經典帝國理論”,該理論認為是管理層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而發動并購,并不是基于為企業謀取更大的利潤為出發點;Jensen(1986)基于自由現金流量視角,認為經理人會將自由現金流量用于建造個人帝國大廈、管理層的權力及薪酬;“套利假說”則認為股票市場具有非有效性,管理者會利用市場的非有效性以及激勵政策的范圍,在進行并購時會優先考慮個人收益而做出主觀性的決策。我國在此領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李增泉、余謙和王曉坤在2005年發表的文章,他們立足于我國股權集中度高這一現實情況,以“掏空”和“支持”觀進行研究,針對我國股權集中度較高的所有權模式,闡明了企業并購的動因。在并購績效與高管薪酬關系方面,追求價值最大化的股東與以私利為導向的管理者之間存在著代理沖突,管理者的決策往往會影響著企業并購過程中的價值。所以,可以通過制定科學的管理機制來激勵高管為企業謀取最大化價值。一方面,企業的董事會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監督作用;另一方面,股東為了降低代理成本、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需要制定完善的薪酬體系來激勵高管。然而,在制定的過程中,由于董事會想要以高管的能力和其能夠為公司帶來的價值這些不可直接觀測的信息為標準,但這些信息的獲取成本較高,此時股東通常選取一些可觀測的替代性指標——企業規模最大化或股東價值最大化。盡管很多企業將公司業績與高管薪酬直接掛鉤,但Finkelstein在1989年的研究表明高管的薪酬大都與公司規模成正比,而和企業價值的相關程度較低。而且理論和實務界對管理者薪酬的影響因素的研究都表明與公司規模關系密切。即公司規模越大、公司戰略并購重組次數越多,那么高管的薪酬水平就會越高,因此忽略了并購后公司的聲譽以及股東財富(李善民和朱滔,2005)。
三、理論分析
1.國企并購決策與薪酬變動
李善民指出,一定程度上,公司高管的薪酬會受到管制是因為中國并不像西方資本市場那樣擁有真正意義上的經理人市場。并且由于這種嚴格的管制,管理者的相對收入水平扭曲更加嚴重。陳冬華(2005)對此做出了進一步解釋,即這種嚴重的扭曲是因為我國政府的行政干預以及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在薪酬管制下,薪酬激勵的欠缺帶來了很多不良結果。首先,管理者為了彌補在薪酬管制之下導致的薪酬激勵不足,會自發提高自己的在職消費來作為獲取私利的替代。在職消費是公司契約不完備性以及正常經營的需要的產物,這一行為本身有其存在合理的一面。若制度尚不完備,那么在職消費就可以成為經理人自我激勵的方法。但在很多國有企業,在職消費總是超出其應有的水平,表現為自我激勵成本巨大(陳冬華、陳信元,2005)。其次,會造成企業進行很多低效的投資,而并購作為外延式的資本擴張方式,它的發生可能也與薪酬制度的不完備有關。最后,薪酬管制下高管股權性薪酬水平過低,但其比重有逐漸增大的趨勢。因此,隨著中國國企不斷進行改制以及經理人市場不斷的完善、管理者持股水平逐漸增大的同時,應進一步關注利用高管股權性薪酬去緩和高管并購決策中的激勵不相容問題。
結合中國國有上市公司并購事件來看,其并購動因可以分為政府干預性資產重組和投機性資產重組(馮福根,2001);大部分的國企并購行為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主并公司管理者推動完成的,特別是處于打造政績的地方政府會積極鼓勵當地企業并干預并購行為的發生,這便為主并公司管理者追求個人私利提供了寬松的環境。而且,國企承擔著較多的政策性負擔,使得其普遍采用“規模導向型”的發展方式,于是并購就成了一個除企業內部積累外次優的選擇,由文獻綜述可知,并購帶來規模的擴大,業績的提升,這為管理層提升薪酬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因此,從總體上來說,對于國有企業發動的并購后造成的結果應該是高管薪酬,包括貨幣性薪酬與權益性薪酬的提升。
2.控制權不同影響企業并購與薪酬變動的相互關系
國有企業的性質不同于民營企業,它存在著政企不分、“一股獨大”的情況。最終控制人是政府的特殊性質,讓國有企業既需要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需要承擔社會責任,甚至履行社會責任的目標比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更重要。考慮到這一層面,將國有企業按控制權分類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和國資委控制來分析并購對薪酬變動的影響是有必要的。夏紀軍提出,組織治理的兩個重要工具,即控制權配置和激勵安排。由委托代理理論可知,以客觀績效為標準衡量的激勵契約能較好地解決代理問題。但是,在委托代理關系中,假如代理人的激勵問題和集體決策協調問題同時存在,那么代理人的激勵和委托人的決策控制權就可能產生沖突,進而對組織績效產生影響。在公司治理層面,這種沖突就表現為管理層激勵和大股東控制權之間的沖突。根據這樣的分析,國有企業并購中,政府會進行更多的干預,但控制權與激勵是否會產生強烈的沖突,需要進一步結合股權性質以及政府目標市場化和管理層目標市場化的同步性來考慮。
(1)中央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
相對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市場化程度較低,而且,管理層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相對于政治激勵,貨幣形式的激勵要處于次要地位,即使企業的目標和政府的目標相悖,管理層也不會因此和大股東發生沖突,反而會堅定實現政府目標(夏紀軍,2008)。因此,在中央政府干預下,國企并購多是出于政府目標,管理層也通過并購擴大了企業規模,進而提升了自己的薪酬水平,因此,和其他股權性質的企業比較,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國有企業在發動并購之后薪酬水平較并購前提升,且股權激勵效果會較好。
(2)地方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
地方政府的市場化程度相對于中央企業要高,受到的約束相對較弱,而且管理層一般是由高度市場化的職業經理人組成,此時需要區分地方政府干預并購決策的動機,一類是政府(官員)出于政府目標(居民福利)去干預企業決策,另一類是官員出于私人收益去干預企業決策,如果企業面臨的是前一種情況,那么管理層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可能就會與政府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目標相沖突,此時,管理層對于并購的積極性就會降低,而且并購行為對于管理層的薪酬也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并且股權激勵的效果也會比較差。反之,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么政府干預往往表現為官員與管理層的合謀或腐敗(夏紀軍,2008),這種干預會有損公司價值,但不會導致控股方與管理層目標的沖突。此時,并購行為能夠給管理層帶來薪酬的顯著提升,即使并購后公司績效并沒有得到改善。對于高管持股的影響,這里的分析借鑒李善民(2009)的研究結論:高管發動并購行為并不能增加其股權性薪酬,高管持股之后,發動并購事件的目的便不再是增加個人收益,而是個人私有收益之外的其他目的。故而對于地方控制的國有企業,高管持股能夠緩解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
(3)國資委控制的國有企業
通常來說,由國資委控股的國有企業管理層市場化程度較中央直屬國企高,但控股股東目標的市場化程度又低于地方政府,這樣一來,國資委控股的國企中的控制權與激勵的沖突會更加嚴重。因此,并購行為對管理層的貨幣性薪酬以及股權性薪酬影響很小,高管的股權激勵效果較差。
四、啟示與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下列建議:
第一,在國有企業中,應該提升績效在薪酬考核中的比重,同時應打破“董監高”現象,強化薪酬委員會專家作用;第二,設計合理的薪酬結構,增加股權激勵比重,積極發揮薪酬的激勵作用;第三,合理選用人才,減少政府直接任命,善用市場化機制引進人才。
參考文獻:
[1]陳冬華,陳信元,萬華林.國有企業中的薪酬管制與在職消費[J].經濟研究,2005(02):92-101.
[2]陳信元,黃俊.政府干預、多元化經營與公司北績[J].管理世界,2007(01):92-97.
[3]方軍雄.政府干預、所有權性質與企業并購[J].管理世界,2008,(09):118-123+148-188.
[4]李善民,曾昭灶,王彩萍,朱滔,陳玉里.上市公司并購績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世界經濟,2004,(09):60-67.
[5]李增泉,余謙,王曉坤.掏空、支持與并購重組——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05,(01):95-105.
[6]權小鋒,吳世農,文芳.管理層權力、私有收益與薪酬操縱[J].經濟研究,2010,(11):73-87.
[7]張新.并購重組是否創造價值?——中國證券市場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3,(06):20-29+93.
[8]潘紅波,余明桂.支持之手、掠奪之手與異地并購[J].經濟研究,2011,46(09):1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