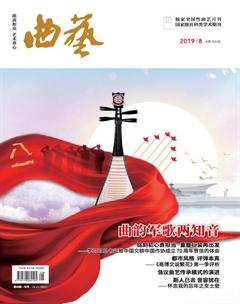芻議曲藝傳承模式的演進
賈振鑫
曲藝起源于人們田間地頭、胡同里弄的勞動生活,經過了一代代人的傳承,綻放著獨特的藝術光彩,為人們送去了無限的歡樂。曲藝的傳承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基本以拜師收徒的社會傳承為主,家傳性質的家庭傳承為輔,少見專業化、規模化、系統化的學校傳承模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朝著更加多元、科學的方向邁進。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曲藝傳承講究“無宗不立,無師不傳,無徒不繼。過去,要想從藝,沒有師承門戶的得不到同行業的認可,也就是沒有取得行業的準入證,這既不可能學到技藝的真諦和精髓,又不能填飽肚子。”①所以,“凡是江湖藝人,不論是干哪行兒,都得有師傅,沒有師傅是沒有家門的,到哪里亦是吃不開的。就拿評書的藝人說吧,他要是沒有家門,沒拜過師傅,若是說書掙了錢,必有同行的藝人攜他的家伙。”②“相聲的同行‘盤道沒有評書場這樣繁瑣,但‘攜家伙攪亂場子的事大同小異,所以也得拜師。”③那些沒有拜師的行藝之人,被稱作“海青”,時時受到同行的排擠,要繼續從事這個行業就要拜師門,或被迫轉行。雖然有少數例外,如王少堂派揚州評話有行規,家傳子弟可以不再單另拜師,但這種情況放在曲藝界整體來看畢竟是少數。
相聲的拜師儀式,要有引師、保師、代師。引師就是拜師的介紹人;保師是師徒雙方的保證人,一般由社會上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擔任;代師則可以替師授業,傳授基本功、小段之類。拜師大體分拜門、授業兩種,前者系帶藝投師,拜師只為入門。早年的曲藝界,無論多大的“家”多大的“萬”,子女要想從事這個行業,即使有家傳也得另外再拜師門。說相聲的馬三立(拜師周德山),說快板書的李少杰(拜師高鳳山)都有家傳,父輩也是名家,但是依照這種規矩另行拜師。這種拜師就牽扯到了另外一種拜師形式——帶拉,就是師父不在人世了,由同門大師兄代師收徒;也有在師父的家人許可下拜入師門的。授業是徒弟開蒙問藝,需要三年零一節(春節、端午或中秋)才能出師,滿師后還要給老師效力一年,舉行謝師會。授業期間的衣、食、住、行由老師負責,凡三節兩壽,禮物不管厚薄多少,都要拜望師父。授業期間,死走逃亡,業師概不負責。拜師需要“擺知”,宴請業內有關人士,也起到一個告知的作用。徒弟有拜師帖,師父有收徒帖,這是拜師收徒的憑證。
蘇州評彈的拜師,徒弟入門要向給師父交納拜師金(亦稱“贄金”、“壓貼”),數量的多少與老師的業務能力及社會影響力相關。光裕社時期,藝徒出道還有“茶道”與“大道”兩個步驟,即師父根據徒弟的學藝情況在每年農歷正月二十四和十月初八(即所謂“三皇祖師”的生日和忌辰),分別邀請業內人士飲茶、聚餐,這些活動的費用自然由徒弟支付。其活動性質與北方的“擺知”相像,起到一種告知的作用,同時徒弟也分別取得演出、收徒的資格。此外,曲藝界還有拜干爹的傳統,就是已經有師門的人和對自己藝術有幫助的人之間確立一種近乎師生的關系,也算是對拜師收徒方式的一種補充。曲藝界拜師儀式的繁瑣,首先說明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得到了弘揚,師徒之間的融洽關系受到了重視;再就是維護了本行業的尊嚴,求得了一種心理的平衡。藝人自古就有“寧舍十吊錢,不把藝來傳”的說法,表面上是藝人們的思想保守所致,實際是因為他們把賴以為生的藝術看得比泰山都重,認為藝業不可輕傳,讓別人學得容易會讓人覺得不值一文而丟得更容易。
當時的授業方式,老師主要傳授發聲、吐字等基本功的練習方法以及基本的段子,教授作品主要靠“熏”,就是讓徒弟到老師演出的地方觀看演出,晚上或第二天一早讓徒弟把聽過的內容給老師背述(揚州評話里叫做“回書”),老師再進行指導。當然,也有“對口喂”的口傳心授方式,就是老師一句一句地教臺詞,手把手地教會表演動作,但學習提高主要靠學生的個人領悟,這就是所謂的“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了。
拜師的人大多是為了學習藝術的需要,也有的是為了要一個門戶的名分,不排除看重師父的名望,有著“借萬揚萬”的想法。曲藝“行界里最忌的現象是‘跳槽,即同一曲種拜了師父又拜他人。有的人為了圖門戶關系或者想借師父的名氣,甚至不惜降低自己的輩分重復拜師,這在歷史上算得上是沒有藝德的表現。”④ 當然,這種“功夫在詩外”的拜師,其本質上是投機心理的產物,不值得提倡。不過,出于提高藝術水平、傳承藝術事業的另行拜師,是可以另當別論的。因為曲藝界傳統拜師“從一而終”的思想,體現了曲藝從業者的保守思想和不自信心理,徒弟如果又拜他人可能意味著收徒者前期培養付出的流失,也有被別人質疑藝術水平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些藝人出于自我保護,凡事計較個人得失,沒有甘當人梯的奉獻精神,不具備支持曲藝人才、曲種乃至曲藝事業發展的大局觀。而在學校教育模式中,一個有上進心的學生上完小學,進而初中、高中、本科、碩士、博士,可以有多個老師,學生如果愿意,可以稱呼所有老師為“師父”。但曲藝行里拜的老師好比娶回家的媳婦,不能有“出軌”行為,老師要是只有小學或初中的水平,再拜個高中及以上水平的師父就要被扣上“欺師滅祖”的帽子,從“道德”角度大受攻擊。如此,確實限制了曲藝人才的發展,也不利于曲藝事業的整體進步。再就是,拜師收徒“口傳心授”教學模式的優勢在于一對一地針對性教育,便于因材施教;缺點是缺乏理論原理的講授,教學方式相對刻板,學生要原封不動地拿來,靠自己的感悟和實踐提高藝術水平。再者,拜師收徒的傳承方式是產生于自給自足經濟模式下的文化現象,與現代藝術人才培養的分工明確、科目條理相比,在人才培養的質量、數量上顯然處于弱勢,無法滿足社會對曲藝表演、創作、編導、策劃、營銷、編輯等高層次綜合人才的需要。如果曲藝傳承能夠將學校教育專業化、規模化、系統化的優勢與“口傳心授”的優勢加以融合,實現曲藝人才規模化培養與精英化培養相結合、現代教育模式與傳統模式相補充,那將是再好不過的。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曲藝人才的培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首先,在拜師收徒的基礎上,出現了“以團(隊)帶班(或訓練隊)”的培訓模式。1958年至1960年,天津市曲藝團一共招收了三屆共60人的曲藝訓練隊,隸屬于天津市戲曲學校,由市曲藝團負責培訓。教學曲種包括了京韻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樂亭大鼓、天津時調、單弦、山東琴書、快板書、相聲、河南墜子等,還有相關的樂器伴奏專業。訓練隊教學手段豐富,既有傳統的口傳心授教學,也有觀摩演出、實習演出、文化課學習、音樂素質課等現代教學方式。這批學員不僅是天津曲藝團的后起之秀,有的還成為了全國曲藝名家,如籍薇、張志寬等。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種培養方式已經不復存在了。此外,1952年冬至1953年冬,志愿軍政治部在遼寧省開原縣連續舉辦了三屆曲藝培訓班,曲種有京韻大鼓、西河大鼓、山東快書、單弦等;1953年冬,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在北京舉辦了曲藝培訓班,曲種有京韻大鼓、西河大鼓、山東快書、河南墜子等。此后,以部隊政治文化部門和地方文化主管部門舉辦的曲藝培訓班紛紛出現,山東快書等地方曲種正是依賴這種方式實現了人才的規模化培養,迅速走向全國。
其次,曲藝學校教學模式得到發展。1962年,在陳云同志的建議下,文化部出資扶持、江蘇省人民政府批準創辦的蘇州評彈學校成立,這是省屬的中等專業藝術學校,是當時全國唯一培養評彈人才的教學機構。目前,這所學校和蘇州市評彈團合并辦公,實行的是“團校聯合”的運作模式。1978年,山東省藝校在省級藝校中率先開設曲藝科,設有山東快書、山東琴書、相聲、快板、西河大鼓、河南墜子專業,培養了曲藝理論家郭學東、山東快書表演藝術家李東風等一批曲藝人才,這些學員成為山東曲藝的中堅力量。1984年,在陳云同志的關心下,駱玉笙等老藝術家奔波操勞,文化部直屬的中專學校“中國北方曲藝學校”破土動工,并于1986年9月開始招生,培養曲藝演員和編創人員,開設有相聲、評書、鼓曲、韻誦類等多個專業,現在活躍于曲壇的相聲演員周煒、高曉攀及梅花大鼓演員楊菲等都是這個學校的優秀學員。后來,北方曲藝學校并入天津藝術職業學院,成為其中的曲藝系。
曲藝學科建設也得到極大推進。繼蘇州評彈學校、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之后,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于1986年在北京宣告成立,由此形成了“兩校一所”的曲藝教學研究格局。在當時,老一輩曲藝家也提出了建立“中華曲藝學院”的構想,可惜未能進入實施階段。1984年,河南民俗學者任騁提出了建立曲藝學的設想,這在許多高校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正在變為現實:中央戲劇學院2001年曾招收相聲大專班,培養出了賈玲、王彤等一批優秀相聲演員;遼寧科技大學曲藝表演本科專業2004年開始招生,主要開設有相聲、評書、快板等專業,至2019年已有十二屆學生畢業;北京電影學院2013年開始招收相聲與喜劇表演專業本科生;北京城市學院目前也在招收曲藝專業本科生;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從2002年開始招收曲藝史論、曲藝評論方向的碩士,2009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南開大學、中國音樂學院、聊城大學等數所高校開設有曲藝課程或者在音樂學等專業下培養主修曲藝的本科生;中央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也曾招收培養過曲藝方向的學生。2015年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高等職業教育(專科)專業目錄(2015年)》中,“曲藝表演”名列表演藝術之中,標志著曲藝高等職業教育已取得“正式戶口”。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即現天津藝術職業學院曲藝系及北京戲曲職業學院等8所職業院校都在培養專科職業曲藝人才。山東省《關于申報2016年“3+2”“3+4”職業教育對口貫通分段培養試點專業的通知》(魯教高處函〔2016〕3號)中,曲藝表演專業赫然在列,本科專業代碼130302,參考對應本科專業名稱為戲劇學。據悉,山東省濟南藝術學校正在與有關高校協商,謀劃實施曲藝職業教育從中等專業教育到高等本科教育的七年一貫制培養。目前全國已有幾十所高等院校開展曲藝學歷教育或通識教育,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國曲藝家協會重視曲藝學科建設的推進,全國高等院校曲藝教育峰會從2015年開始,已分別在遼寧科技大學、北京城市學院、四川師范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聊城大學連續舉辦了五屆,團結了曲藝高等教育力量,推出了曲藝高等教育成果,激發了高校曲藝教學的熱情與信心。與此同時,中國曲協與遼寧科技大學共同開發編寫的高等教育曲藝類本科專業教材《中國曲藝發展簡史》《中華曲藝圖書內容概覽》《中華曲藝圖書資料名錄》《中國曲藝藝術概論》《評書表演藝術》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相聲表演藝術》等教材全部進入編撰出版階段。曲藝高等教育本科教材的問世對推動曲藝學科建設有著重要的作用。
目前的曲藝高等教育仍較為薄弱,與擁有400多個曲種的龐大藝術體系、與社會對曲藝的關注度以及社會對曲藝學歷人才的需求不相匹配,對曲藝學術研究的開展、高層次綜合人才的培養以及曲藝事業整體的發展進步都有一定限制作用,但是,這些不利因素之于曲藝既是挑戰,更是機遇,以中國曲藝家協會為主導的曲藝學科建設,符合曲藝發展規律,符合時代需要、人民期待,相信在好事多磨后一定會取得全面的勝利。
再次,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傳承弘揚,教育部門素質教育相關政策的實施以及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活動的開展,都為曲藝發展營造了有利的生態環境。
對中小學教育而言,曲藝進校園、進課堂實現了曲藝學校傳承從無到有的突破,為曲藝贏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教育部門關于藝術教育的系列文件,促進了中小學對藝術教育的重視,特色立校、特色興校的理念逐漸得到落實,曲藝成為很多學校開展藝術教育、傳承傳統文化的優先選項。在此背景下,一些富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地方文化主管部門、曲藝家與時俱進,積極組織實施了曲藝進校園、進課堂的活動,培養小小曲藝家,傳承曲藝藝術。有的學校還專門編寫了曲藝校本教材,積極推出適合兒童特點、有溫度、有勁道的曲藝作品,還有的在結合《三字經》《百家姓》等傳統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另外,一些學校在邀請曲藝傳承人走進校園、走進課堂的同時,也積極鼓勵青年教師加入曲藝傳承的隊伍,既撒下曲藝種子,也培養曲藝園丁,確保了曲藝學校教育生命力的延續。
新世紀以來,藝術培訓行業的快速興起促進了曲藝社會培訓的發展,曲藝培訓以曲藝或以語言表演培訓的名義面世,有些已取得突出成績。如由李少杰主辦的“竹韻齋”就以培養曲藝人才為宗旨,在全國多個省市設有分部,培養的小學員在各級各類展演比賽中多有上佳表現。由于學習普通話的社會需求廣泛存在,北方曲藝中的相聲、快板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受到熱烈歡迎,其他地方曲種依賴社會培訓力量的傳承模式則有待得到加強。
此外,曲藝拜師收徒的培養模式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著各地地方曲種入選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曲藝業余愛好者的拜師人數呈逐年上升之勢。這部分人大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基本不依靠曲藝養家糊口,自娛自樂的成分較多,也有些愛好者對曲藝有著別樣的人生寄托,還有一些半職業和業余曲藝人才有著較高的藝術造詣,在各級各類曲藝活動中有著高水平的展現。
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曲藝傳承模式僅限于拜師收徒和家庭傳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曲藝傳承實現了社會傳承、家庭傳承、學校傳承的立體化、多元化傳承模式,開啟了曲藝專業化、規模化、系統化的傳承時代。特別是曲藝的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實現了歷史突破,正式“登堂入室”進入了國家正規教育的范疇。由此,曲藝飽含著“民間基因”的舞臺化道路將一片坦途,將為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更大貢獻。
注釋:
①煒熠:《有感而發話拜師》,《曲藝》,2015年第5期。
②連闊如:《江湖叢談》,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③劉連群:《馬三立別傳》,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版。
④張睿萌:《摒棄或傳承——且聽趙連甲先生解讀》,《曲藝》,2015年第5期。
(作者:聊城大學音樂與舞蹈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