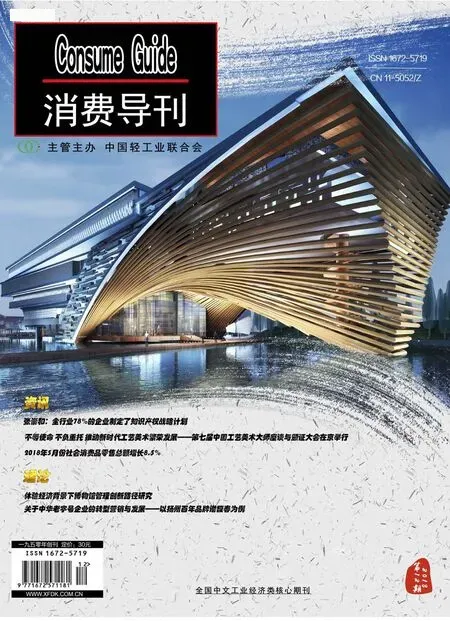論民事糾紛中的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
李青南
摘要:當(dāng)下,醫(yī)患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逐漸成為醫(yī)患溝通的橋梁。醫(yī)學(xué)與法學(xué)同作為具有公共性、專業(yè)性的學(xué)科,交叉意義重大。從學(xué)理的醫(yī)療行為傷害說(shuō)角度看,醫(yī)療行為的侵襲性和治愈性是共生的,在法律上,通常可理解為違法性和阻卻性之間的關(guān)系。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存于現(xiàn)行法的篇幅較少,但都以知情同意制度、緊急救治、不可抗力等為主,學(xué)術(shù)界更是眾說(shuō)紛紜。然而必須承認(rèn),在現(xiàn)行法的框架下,其不足之處逐漸被暴露于眾,如知情同意制度立法的模糊性、患者家屬濫用知情同意權(quán)的可能性、緊急救治下專斷醫(yī)療的信息不對(duì)等性等等。鑒于此,確立患者意思第一順位、推廣代理評(píng)價(jià)機(jī)制、緊急醫(yī)療提前簽字制度等或許能作為方案設(shè)想助于完善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體系。
關(guān)鍵詞:醫(yī)療行為 違法阻卻 知情同意 緊急救治
在我們的普遍認(rèn)知里,“打開(kāi)”他人的胸腔,切除他人的器官等皆是嚴(yán)重的侵權(quán)行為,但作為醫(yī)療手段卻合法正當(dāng)。醫(yī)療行為的侵襲性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產(chǎn)生了眾多矛盾。醫(yī)患矛盾即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古有曹操盛怒斬殺華佗,今有醫(yī)鬧血案屢發(fā)不止,數(shù)據(jù)表明,近三年來(lái),全國(guó)已發(fā)生典型暴力傷醫(yī)案百余起。醫(yī)患矛盾愈演愈烈的背后,除了人性的缺失外,還伴隨著制度的不健全。固然,醫(yī)療行為的侵襲性與修復(fù)性是共生的,而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尤其是在法治社會(huì)下,侵襲性與正當(dāng)性如何“自圓其說(shuō)”的問(wèn)題就涉及到違法阻卻事由了。
違法阻卻事由作為一個(gè)法律概念,在民法范疇和刑法領(lǐng)域皆有一席之地,放到當(dāng)下的醫(yī)療糾紛亂象下,更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其一,醫(yī)鬧屢禁不止,行業(yè)危機(jī)升級(jí);其二,醫(yī)療內(nèi)涵及外延愈發(fā)寬泛性,各類(lèi)“醫(yī)療服務(wù)”層出不窮:其三,醫(yī)療損害舉證責(zé)任規(guī)定變化,影響漸長(zhǎng)。
一、醫(yī)療行為違法性的概述
(一)醫(yī)療行為定義
關(guān)于醫(yī)療行為的定義,現(xiàn)行法并未作出明確規(guī)定,僅用“醫(yī)療活動(dòng)”或“醫(yī)師的執(zhí)業(yè)活動(dòng)”等概括,僅《醫(yī)療機(jī)構(gòu)管理?xiàng)l例實(shí)施細(xì)則》第88條有對(duì)“診療活動(dòng)”進(jìn)行解釋,但其著重強(qiáng)調(diào)活動(dòng)本身,忽視細(xì)節(jié),難以作為完整的概念運(yùn)用。也許相關(guān)法也是考慮到醫(yī)療的囊括性及變化性,所以作此安排,但無(wú)疑增大了醫(yī)事法律的不確定性。而其他國(guó)家和地區(qū)對(duì)此定義呈狹義和廣義之分。
1.國(guó)內(nèi)外定義
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認(rèn)定:“凡以治療、矯正或預(yù)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于診察、診斷結(jié)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之處方或用藥等行為之一部或全部之總稱,皆為醫(yī)療行為”此概念著重于診療的目的性,和我國(guó)的“診療活動(dòng)”解釋有本質(zhì)相似,具有狹義之不足,難以適應(yīng)當(dāng)下諸如美容整形、變性手術(shù)、人體實(shí)驗(yàn)等項(xiàng)目的發(fā)展。
相較而言日本的規(guī)定更加廣義:“若欠缺醫(yī)師的醫(yī)學(xué)判斷及其技術(shù),則會(huì)對(duì)人體產(chǎn)生危害的行為”此定義以否定式表達(dá),從內(nèi)容和主體上都做了更寬泛的保留,不再僅限于醫(yī)師所實(shí)施的診療行為。但過(guò)于寬泛仍未解決定義的不確定性,反而過(guò)分加大了主體的范圍,有損醫(yī)務(wù)人員的專業(yè)性。
2.本文觀點(diǎn)
筆者認(rèn)為,在對(duì)醫(yī)療行為下定義時(shí),應(yīng)尤其注意特定的主體,即醫(yī)護(hù)人員;注意特定的客體,即患者;注意特定的內(nèi)容,即專業(yè)性醫(yī)療服務(wù),與此同時(shí),控訴醫(yī)生的醫(yī)療行為侵犯隱私權(quán)。的案件也屢見(jiàn)不鮮。因此綜合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及社會(huì)醫(yī)療服務(wù)實(shí)踐,醫(yī)療行為可定義為:醫(yī)療機(jī)構(gòu)運(yùn)用包括心理手段在內(nèi)的醫(yī)學(xué)手段對(duì)人體實(shí)施的一定干預(yù)或改變的行為及為了實(shí)施此行為的必要配套行為。
(二)醫(yī)療行為的違法性
不同的法律之間可能因保護(hù)法益的不同而“相互矛盾”,違法阻卻事由便能協(xié)調(diào)其中。因此,在討論醫(yī)療行為的性質(zhì)時(shí),大可大膽將其歸類(lèi)于違法性中,正如依據(jù)刑法二階層體系討論犯罪構(gòu)成時(shí),客觀意義的“違法”是非終局的,只有經(jīng)過(guò)阻卻事由的檢測(cè)才能得出有效結(jié)論。德國(guó)判例界及日本理論界即使如此。作為其主流觀點(diǎn),醫(yī)療行為傷害說(shuō)承認(rèn)醫(yī)療行為對(duì)人體的侵襲性和高風(fēng)險(xiǎn)性,該傷害性與違法性“師出同門(mén)”,筆者亦贊成此觀點(diǎn)。
二、違法阻卻事由
我國(guó)目前并未以法律形式列明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僅《醫(yī)療事故處理?xiàng)l例》規(guī)定有關(guān)醫(yī)療事故的免責(zé)事由,但眾多學(xué)者對(duì)此早有關(guān)注。如張明楷教授認(rèn)為,“醫(yī)生基于患者同意或推定同意,采用醫(yī)學(xué)認(rèn)可方式,客觀上損害患者身體的治療行為,屬于正當(dāng)業(yè)務(wù)行為,但其阻卻違法的要求更為嚴(yán)格”。
(一)知情同意
1.定義及源起
所謂知情同意制度,指醫(yī)方應(yīng)就自己具有的,可能影響患方作出是否同意實(shí)施特定醫(yī)療行為決定的重要事項(xiàng),向患方予以充分說(shuō)明解釋,患方在此基礎(chǔ)上自由做決定的制度。自美國(guó)1914年的Schloendorffv.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起,到“患者自主決定權(quán)”運(yùn)動(dòng)和《紐倫堡法典》的通過(guò),最后到1957年salgo v。LelandStanford Jr.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案,“informed consent”概念誕生。隨后,英國(guó)、法國(guó)及德國(guó)也分別確立了知情同意理論及制度,中國(guó)大陸學(xué)者將該舶來(lái)品譯為“知情同意”。
2.醫(yī)務(wù)人員的告知義務(wù)
知情同意制度的發(fā)展具體可體現(xiàn)為它從強(qiáng)調(diào)患者的權(quán)利演變到重視院方的義務(wù)層面。《病歷書(shū)寫(xiě)基本規(guī)范》明確將獲得患方知情同意書(shū)列為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同時(shí),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列舉規(guī)定相應(yīng)告知內(nèi)容,如:病情、診療(手術(shù))方案、風(fēng)險(xiǎn)益處、費(fèi)用開(kāi)支等。告知對(duì)象不限于患者,還包括患者家屬;告知方式不限于口頭交涉,還包括門(mén)診告示、入院須知、電話告知、病程記錄、知情同意書(shū)等。
3.患方的同意
在知情權(quán)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chǔ)上,法律明確規(guī)定須獲得患方書(shū)面形式的同意,因此知情同意書(shū)作為承載醫(yī)患雙方意思內(nèi)容的法律文件,在實(shí)踐中應(yīng)用廣泛,但同時(shí)也不否認(rèn)在特定情況下的口頭同意及推定同意。除形式要求,享有知情權(quán)、同意權(quán)的主體也有特定要求。《醫(yī)療機(jī)構(gòu)管理?xiàng)l例》規(guī)定了“患者、患者家屬或關(guān)系人、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同意順位。就患者家屬而言,實(shí)踐中絕大部分只承認(rèn)配偶及直系血親,但尚未界定當(dāng)眾多患者家屬意思不一致時(shí)的處理方案。
(二)緊急救治
《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和《醫(yī)療事故處理?xiàng)l例》均規(guī)定緊急情況下的救治是知情同意制度的例外。對(duì)于何為情勢(shì)緊迫,理論界基本達(dá)成了一致觀點(diǎn):生命遭受重大危險(xiǎn)性、時(shí)間的緊迫性。但筆者認(rèn)為,在此基礎(chǔ)上還應(yīng)考慮醫(yī)療手段的實(shí)施可能性,即醫(yī)院擁有能實(shí)施急救的條件。至于其作為阻卻事由的正當(dāng)化依據(jù),理論界目前觀點(diǎn)有二。
1.推定同意
《里斯本宣言》規(guī)定了在緊急情況下,醫(yī)師應(yīng)當(dāng)采用最有利于患者利益的最佳行動(dòng)并可推定其及家屬同意。但在1994年日本教徒拒絕輸血搶救案中,雖手術(shù)大獲成功,但卻被法院認(rèn)定為侵犯患者自主決定權(quán)。在此案中“生命權(quán)”非患者的最大利益,維護(hù)宗教信仰凌駕于生命;在中國(guó)陜西也有類(lèi)似糾紛:一早產(chǎn)新生兒情況危急,醫(yī)院不顧其父母“拒絕插管治療”的意思表示而仍為其插管搶救,醫(yī)院主張“患者生命利益為大”,以醫(yī)學(xué)標(biāo)準(zhǔn)判斷應(yīng)當(dāng)實(shí)施特殊治療,父母主張知情同意權(quán)受侵犯致患兒未有尊嚴(yán)地死去。若以推定同意論,明示拒絕自然可以否定醫(yī)師的緊急救治。
2.緊急避險(xiǎn)
此時(shí)患者的身份為被保護(hù)法益人、被犧牲利益人及引起險(xiǎn)情(疾病)的人,患者家屬也可因?yàn)榫芎灥刃袨槌蔀橐痣U(xiǎn)情的人,根據(jù)《侵權(quán)責(zé)任法》規(guī)定,院方緊急避險(xiǎn)實(shí)施緊急救助,不承擔(dān)責(zé)任,因此在特定情況下,該角度可以緩和因知情同意帶來(lái)的僵化效應(yīng)。同時(shí)緊急避險(xiǎn)能賦予院方更多的專業(yè)判斷空間,避免很多因家屬拒簽導(dǎo)致延誤治療的后果。但是,裁量空間擴(kuò)大必然伴隨著對(duì)方權(quán)利的讓步,過(guò)分鼓勵(lì)專斷醫(yī)療行為同時(shí)容易成為醫(yī)院的濫用違法阻卻的依據(jù)。
(三)醫(yī)療意外
醫(yī)療意外,也可稱作不可抗力,指不可能預(yù)見(jiàn)的意外情況作為違法阻卻事由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類(lèi)比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介入因素,一般情況下,病情異常或體質(zhì)特殊還是有認(rèn)定為存在因果關(guān)系的可能,即使不負(fù)刑事責(zé)任,還是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但醫(yī)學(xué)領(lǐng)域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xiǎn)性,病情的發(fā)展及體質(zhì)的差異都是隨個(gè)體不同變化的,故很多患者及家屬都持有“進(jìn)了醫(yī)院一切后果都由醫(yī)院負(fù)責(zé)”的觀念是錯(cuò)誤的,為了醫(yī)師的職業(yè)安全,其不應(yīng)當(dāng)對(duì)此擔(dān)責(zé)。
當(dāng)然,此處指的病情異常是指根據(jù)現(xiàn)有的醫(yī)療水平和當(dāng)時(shí)的醫(yī)療條件無(wú)法被預(yù)知發(fā)展,體質(zhì)特殊指的是根據(jù)醫(yī)療行規(guī)和測(cè)試無(wú)法檢測(cè)到的。
三、阻卻事由的拓展
實(shí)踐中諸多棘手的案例和悲劇皆警醒著立法者和執(zhí)法者:知情同意制度作為一個(gè)舶來(lái)品,體系外殼乃至理念設(shè)計(jì)的移植勢(shì)必“水土不服”;患者家屬濫用知情同意權(quán)或正成為延誤治療的“罪魁禍?zhǔn)住?緊急救治下醫(yī)生完全的“一言堂”難免使得本就“舉步維艱”的醫(yī)患溝通更加阻礙重重。
(一)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不足與設(shè)想
1.現(xiàn)行立法存在模糊性
《醫(yī)療事故條例》以及《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在相關(guān)規(guī)定中都強(qiáng)調(diào)了“應(yīng)當(dāng)避免對(duì)患者產(chǎn)生不利后果”,筆者認(rèn)為此處存在立法上的模糊性。第一,此規(guī)定或許出于“不告知患者”成為一種治療的輔助手段以便患者保持良好心情接受治療考慮,但患者知情與產(chǎn)生不利后果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是難以判斷的:第二,此規(guī)定容易使醫(yī)院以剝奪患者知情同意權(quán)的代價(jià)來(lái)主張醫(yī)療行為正當(dāng),有專斷醫(yī)療的嫌疑;第三,此規(guī)定也容易使患者家屬對(duì)患者擁有過(guò)大的處分權(quán),有失公允。
因此,筆者認(rèn)為,解決方案有二:一刪去該部分規(guī)定,在允許的條件下毫無(wú)例外地履行院方告知義務(wù),滿足患方知情同意權(quán);二結(jié)合法律和醫(yī)學(xué)規(guī)定,以治療手段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為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何種治療必須要求患者在知情條件充分發(fā)揮自主決定權(quán),而無(wú)論是否造成不良后果,如在具有履行告知義務(wù)可能的條件下,對(duì)婦女內(nèi)檢、對(duì)癌癥患者實(shí)施損傷性極大的化療、對(duì)患者實(shí)施有創(chuàng)性治療等必須獲其同意,此就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禁止性目的規(guī)定導(dǎo)致的因果關(guān)系難判斷性。
2.患者家屬濫用知情同意權(quán)
患者家屬代理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權(quán)的情形通常發(fā)生于嬰幼兒、智力或精神障礙者,因疾病發(fā)作、突然外傷受害及異物侵入體內(nèi),身體處于極度痛苦或危險(xiǎn)狀態(tài)的患者,但濫用家屬代理權(quán)往往導(dǎo)致實(shí)踐中將家屬意見(jiàn)等同于患者意見(jiàn),醫(yī)療糾紛也通常以侵權(quán)損害賠償而非違法醫(yī)療合同定性,客觀上都易損害患者利益。
筆者認(rèn)為,現(xiàn)行的知情同意制度有助長(zhǎng)此類(lèi)濫用的嫌疑,以南通414事件為例。本案中福利院根據(jù)相關(guān)法規(guī)享有被看護(hù)人的監(jiān)護(hù)權(quán),但其是否有非以治療為目的而割除患者子宮的同意權(quán)呢?當(dāng)年的法院判決給予其否定答案,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人及院方責(zé)任人以故意傷害罪入刑。這個(gè)案例具有較強(qiáng)的判例意義,我們必須認(rèn)識(shí)到知情同意的代理權(quán)不是代理人“支配”、“處分”患者的工具。然而相關(guān)法規(guī)卻未跟上實(shí)踐的“腳步”,在規(guī)定知情同意權(quán)時(shí),使用“或者”來(lái)表明患者與其家屬享權(quán)的一致性和同等性,如《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
筆者就以上不足提出以下方案:
1.確立患者意思相對(duì)第一順位原則,在實(shí)踐中,醫(yī)院通常采用患者及其家屬雙簽字的形式以保證其知情同意權(quán),但對(duì)患者和其家屬之間意見(jiàn)不一致之情形未作規(guī)定。通常情況下,醫(yī)院以維護(hù)患者生命權(quán)為最高準(zhǔn)則,但卻會(huì)遭遇患者抵觸,甚至對(duì)簿公堂。此是否屬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的“不宜向患者說(shuō)明,應(yīng)當(dāng)取得其近親屬同意并獲得書(shū)面同意”?筆者認(rèn)為,在知情同意的細(xì)節(jié)上,應(yīng)以患者意思第一順位為原則,家屬意見(jiàn)為例外,雖然前文提到外國(guó)的判例遵循生命權(quán)益也應(yīng)讓位于患者的知情同意,但根據(jù)我國(guó)傳統(tǒng)倫理道德以及法律保護(hù)權(quán)益順位,應(yīng)推崇生命權(quán)第一。
2.建設(shè)代理評(píng)價(jià)機(jī)制,實(shí)踐中,一份事前的全權(quán)授權(quán)委托書(shū)能給予其家屬全面的代理權(quán),然而,全權(quán)代理應(yīng)是有條件地行使,即患者意識(shí)不清無(wú)法表達(dá)時(shí)。因此,判斷患者家屬是否能代理患者知情同意,不應(yīng)僵硬地關(guān)注是否擁有委托文件,還應(yīng)審查患者是否無(wú)法表達(dá)真實(shí)意思,對(duì)此,醫(yī)院可結(jié)合醫(yī)學(xué)標(biāo)準(zhǔn)及法律上的限制或無(wú)民事行為能力設(shè)定行使全權(quán)代理標(biāo)準(zhǔn)。
(二)緊急救治下提前簽字制度建設(shè)
在緊急救治情況下,往往難以取得患者及其家屬的同意,法律規(guī)定應(yīng)上報(bào)醫(yī)務(wù)科,由醫(yī)療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人簽字。那么,針對(duì)隨時(shí)可能陷入病危境地的患者及照看其的家屬是否可以提前簽字表達(dá)同意實(shí)施或不同意實(shí)施某特殊治療呢?前文提到陜西的患者家屬控訴醫(yī)生侵犯知情同意權(quán)案例⑥。從醫(yī)院角度,因病情發(fā)展不可預(yù)見(jiàn)而拒絕提前簽字正當(dāng)而科學(xué);從患者家屬角度,提前簽字也是意思表達(dá)、行使知情同意權(quán)的形式,類(lèi)似附條件生效之合同,確有理有據(jù)。
筆者認(rèn)為,提前簽字制度可以作為一種參考的意思表示發(fā)生效力,即表達(dá)患方的治療傾向性,但不具有正式的書(shū)面同意完整的效力。該意思必須是經(jīng)過(guò)完全的醫(yī)患溝通作出,若后有正式的書(shū)面文件即失去效力。故相對(duì)承認(rèn)患方提前的意思表示也不失為一種避免因緊急醫(yī)療產(chǎn)生糾紛的方案。
四、余論:非倒置舉證責(zé)任與違法阻卻事由
在法律思維下,實(shí)體和程序本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而醫(yī)療糾紛舉證責(zé)任規(guī)定和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都是整個(gè)醫(yī)療制度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理論界和實(shí)務(wù)界,醫(yī)療糾紛舉證責(zé)任規(guī)定正經(jīng)歷顛覆性的變化,而此變化“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醫(yī)療違法阻卻事由勢(shì)必作出“回應(yīng)”。
重慶市高級(jí)人民法院在(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0844號(hào)案例中認(rèn)為“由于本案涉及的醫(yī)療行為發(fā)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侵權(quán)責(zé)任法》實(shí)施后,應(yīng)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侵權(quán)責(zé)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四條規(guī)定的醫(yī)療過(guò)錯(cuò)舉證責(zé)任分配原則已不再適用。”遼寧省高級(jí)人民法院也在(2016)遼民申5240號(hào)案件中認(rèn)定“醫(yī)療損害責(zé)任糾紛一般情況下適用過(guò)錯(cuò)責(zé)任原則,“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即患者應(yīng)當(dāng)對(duì)醫(yī)療機(jī)構(gòu)存在過(guò)錯(cuò)及診療行為與損害后果存在因果關(guān)系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可知,醫(yī)療損害賠償糾紛舉證責(zé)任的變化已得到實(shí)踐的承認(rèn)。
筆者認(rèn)為,違法阻卻的存在意義即給予一定醫(yī)療行為免責(zé)事由,規(guī)避不應(yīng)由院方承擔(dān)之風(fēng)險(xiǎn)。故在普通的醫(yī)療糾紛中采用非倒置的舉證責(zé)任規(guī)則更有利于違法阻卻事由在實(shí)踐的落實(shí)。首先,由于信息的不對(duì)等和醫(yī)療的專業(yè)性,非倒置的舉證將對(duì)患者的起訴以及醫(yī)院的信息披露提出更大的挑戰(zhàn):其次,由于起訴和舉證的門(mén)檻較高,醫(yī)療糾紛將相應(yīng)減少,有效避免諸如醫(yī)鬧等向醫(yī)院索取人道主義賠償?shù)氖虑榘l(fā)生,當(dāng)然從患者角度看或許有失公允;最后,由于患者自身局限性,有利于鼓勵(lì)其申請(qǐng)醫(yī)療鑒定,交由第三方和平解決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