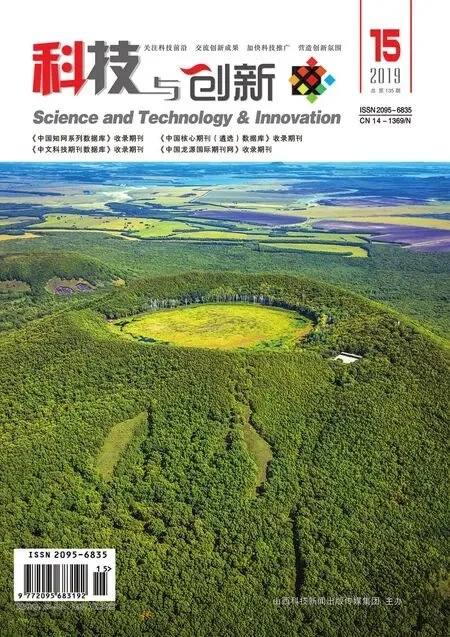微囊藻毒素在水食物網中生物轉歸趨勢的研究現狀及意義
索朗巴珍
微囊藻毒素在水食物網中生物轉歸趨勢的研究現狀及意義
索朗巴珍
(西藏警官高等專科學校,西藏 拉薩 850000)
水體富營養化帶來的藍藻水華在世界范圍內頻頻發生,而中國的主要淡水湖泊,如巢湖、太湖、滇池等藻類污染非常嚴重,其中淡水藻類銅綠微囊藻產生次級代謝產物——微囊藻毒素(MCs),它是一種肝毒素和腫瘤促進劑,它對水體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危害已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環境問題之一。雖然MCs在不同生態系統的眾多水生消費者中已有定量測定,但它是否在水生食物網中普遍發生MCs生物放大或生物稀釋的作用仍然存在爭議。而國內外的研究更側重MCs對水生生物的毒作用機制,研究MCs在水食物網的生物轉歸作用的文獻很少。根據研究發現,MCs在食物鏈中的傳遞機制,恰恰跟MCs對人類消費者存在的風險密切相關。
微囊藻毒素;水食物網;生物放大;生物稀釋
1 研究背景和意義
水質的安全與衛生是人類健康最基本的保障,繼20世紀人們控制了霍亂、傷寒等水傳傳染病后,飲用水中的藻類污染正成為21世紀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近年來,由于來自生活、工業和農業的污染日趨嚴重,使水體富營養化加劇,從而導致藻類水華在世界范圍內頻繁發生。藍藻污染不僅會惡化水質,其中一些有毒藍藻衰老死亡后,釋放出的藻類毒素對淡水體的污染成為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其中危害最大、分布范圍最廣、污染最嚴重的是由銅綠微囊藻、水華魚腥藻和顫藻等藍藻產生的微囊藻毒素(microcystins,MCs)。
早在1878年,FRANCIS在南澳大利亞Alexadrina湖發現并首先報道了泡沫節球藻(Nodularia Spumigena)會對動物產生毒害作用[1],但人們對藻類分子結構的認識還不滿40年。1959年BISHOP首次分離出藻類毒素后,不斷有相關報道發表。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芬蘭等10多個國家都曾報道了其湖泊、水庫中有毒水華的形成,并分離出有毒藻株[2]。中國的東湖、巢湖、太湖、滇池、淀山湖、黃浦江等飲用水水源及各種湖泊在夏秋季節藻類水華嚴重,每年長達7~8個月,而天然水體藍藻水華80%是產毒的[3]。從加拿大、日本、芬蘭、美國、中國等地對湖水、河水、水庫水、井水及自來水等水樣的檢測結果看,有的水體中MCs檢出率高達60%~87%,源水中MCs濃度從130 ng/mL~2 μg/mL不等,經加氯處理后的濃度為0.09 μg/L~0.6 μg/L不等[4]。
因此,MCs污染對人類健康的潛在危害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中國從2007-07-01起,實施了新的飲用水標準(GB 5749—2006),將MCs含量限制為1 μg/L,該標準的實施對水源水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MCs主要是由淡水藻類銅綠微囊藻(Microcystis aeruginosa)產生的一類單環七肽化合物。這類肝毒性物質能強烈抑制蛋白磷酸酶(PP-1和PP-2A)的活性,從而導致機體的肝損傷,同時它還是一種腫瘤促進劑。由于MCs的強毒性和高穩定性,使MCs污染問題得到廣泛關注,目前發現的MCs異構體有80多種,其中,MC-LR是眾多異構體中存在最普遍、含量較多、毒性較大一種。
最近有研究提示,MCs及其毒性會在各個營養級上轉移(即從微囊藻屬到無脊椎動物再到有脊椎食肉動物),這對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更廣泛。水生牧食鏈如圖1所示。水生腐食鏈如圖2所示。

圖1 水生牧食鏈

圖2 水生腐食鏈
人類作為食物鏈的頂端,微囊藻毒素在水體食物網中的生物轉歸作用,對其健康的影響至關重要。盡管MCs已經在各種水生生態系統中的不同消費者中被廣泛測量,并知道MCs可能對人類存在潛在的健康威脅,但是,MCs的生物放大或生物稀釋作用是否在水生食物網中是一個顯著的過程,這個問題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2 研究現狀
MCs在水生消費者體內蓄積及它在水食物網中的生物轉歸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中國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
2.1 國外的相關研究現狀
VICTORRIA R和ISABEL M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被有毒藍藻細菌污染的池塘中,小龍蝦體內蓄積的游離的MCs的量比在鯉魚體內更高,并強調只有定期監控,才能避免通過消費這些水生生物給人類健康帶來的風險。
如預期的那樣,魚和軟體動物是研究最多的消費者,因為它們代表了許多人類所消費的水生物種(IBELINGS and CHORUS,2007年)。令人驚訝的是,盡管大量文獻討論了藍藻和浮游動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但只有少數研究提供了MCs在浮游動物每生物質的濃度和含藍藻飲食中的MCs濃度。雖然大部分的現有文獻中提到了野外條件下收集的不同的種群和營養水平的浮游動物中的MCs負荷,卻只有一個研究(Thostrup and Christoffersen,1999年)收集了在實驗室條件下大型蚤類的相關數據。此外,盡管輪蟲和橈足類是淡水中重要的食草動物,但是沒有發現關于它們的相關實驗研究。而且,很少有研究十足類、鳥類和海龜的文獻,但是,這些高營養級的消費者是與人類消費潛在的風險密切相關。
2.2 國內的相關研究現狀
目前,中國的太湖、巢湖等淡水湖泊受到了嚴重的富營養化污染,對安徽巢湖中處于食物鏈不同營養水平的魚體肌肉組織藻毒素含量進行檢測發現,位于食物鏈上游的食肉性和雜食性魚體內藻毒素顯著高于位于食物鏈下游的以浮游植物為食或草食性的魚體內藻毒素含量。
2009年李旭剛、周剛和周軍等人,在太湖微囊藻毒素對羅非魚體內累積及生物降解的研究中,發現羅非魚體內肝臟組織中微囊藻毒素的蓄積量顯著高于肌肉組織,同時,經過10~20 d自然生物降解后藻毒素含量可降低至安全攝入量之下。有部分國內文獻中提到,處于水生生態系統食物鏈較高等級的魚類,由于微囊藻毒素的生物富集作用,其體內的MCs含量高于環境水中的含量。
3 總結
國內外的研究更側重MCs對水生生物的毒作用機制,而研究MCs在水食物網的生物轉歸作用的文獻很少,另外,MCs在不同生態系統的眾多水生消費者中已有定量測定,但它是否在水生食物網中普遍發生MCs生物放大或生物稀釋的作用仍然存在爭議,至今也沒有有力數據作為證明。
筆者認為不同水生生物的食性和生理條件都存在較大的差異,且不同生物對MCs的生物降解能力也會存在較大差異,這些都是MCs發生生物放大或生物稀釋作用的影響因素。我們應該加強定期的水質監測和生物監測,對不同的水生生物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另外,對于藻類污染嚴重的湖泊和水域,可以通過增大水中生物多樣性來降低水中藻類毒素的濃度。
[1]何家菀.有毒銅綠微囊藻對魚和蚤的毒性[J].水生生物學報,1997,9(1):49.
[2]施瑋,朱惠剛.微囊藻毒素毒理學研究進展[J].上海環境科學,2000,19(2):82-85.
[3]ZHANG D,XIE P,LIU Y,et al.Transfer,distribution and bioaccumulation of microcystins in the aquatic food web in Lake Taihu,China,with potential risks to human health[J].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9,407(7):2191-2199.
[4]BAS W I,KARL E H.Cyanobacterial toxins:a qualitative meta-analysis of concentrations,dosage and effects in freshwater,estuarine and marine biota[J].Cyanobacterial Toxins,2008(32):675-732.
X173
A
10.15913/j.cnki.kjycx.2019.15.026
2095-6835(2019)15-0070-02
索朗巴珍(1990—),女,藏族,學士,助教,研究方向為法化學。
〔編輯:嚴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