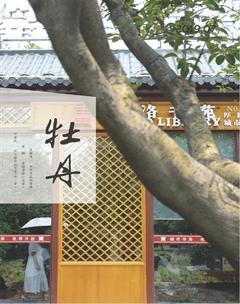淺論沈從文的創作動機
金一筠
《八駿圖》是沈從文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也是一個內涵豐富、具有獨特性的文本。在淺層次上,《八駿圖》可以看作是作家對“都市—鄉村”對立景觀的建構,而其更深的意蘊則體現在潛藏于文本中的作家個人的隱秘心理、價值追求以及技法嘗試等方面,人們從中可以窺見沈從文創作成熟階段較為復雜的創作動機。
發表于1935年的《八駿圖》是沈從文都市題材小說的代表作。通常認為,小說是通過對包括主人公達士先生在內的八位教授的狀貌行為的精神分析式描寫,暴露他們壓抑、扭曲的靈魂,由此批判現代都市文明對人性的戕害。這樣的解讀主要是基于沈從文所構筑的“都市—鄉村”對立模式,失之簡單化和概念化。事實上,《八駿圖》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文本,從題材內容到文體形式,在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都具有代表性,其創作動機值得探究。
一、在自卑與超越中獲得內心平衡
“都市—鄉村”二元對立是對沈從文小說的一種慣常的理解方式。在沈從文的筆下,他毫不吝惜對以湘西為代表的鄉村世界的贊美,而與此相對立的是充滿險惡、壓抑、扭曲的都市社會。這雖不是闡釋其作品的好角度,卻可以成為讀者進入作家內心世界探究其創作動機的切入點。
沈從文為什么要煞費苦心地打造這樣的城鄉對立景觀呢?結合他的早年經歷和種種自述可以看出,原因不是簡單的好惡所能概括的,而是受復雜的心理因素影響。這種隱秘心理動因在《八駿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1922年,沈從文告別了湘西初到北京,抱著考大學、做學者的愿望開始了在大都市中的闖蕩。美國學者金介甫認為:“20年代多數進步的作家全是教授,以他們的學問受到人們的尊重。因此,沈從文顯然必須考進大學。”經濟窘迫,考大學也屢屢落榜,特別是考燕京大學得零分這一經歷使他的自尊心嚴重受挫。為了生計,沈從文只好大量寫作和投稿,但發表并不順利,他的稿件還曾被時任《晨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當眾扔進廢紙簍。經歷了種種挫折,沈從文漸漸明白了大都市的生存法則和他所向往的文化知識界的等級構成。《八駿圖》所描寫的對象——教授,正是文化知識界掌握話語權威的角色。即使在成為知名作家乃至自己也做了教授之后,沈從文對于曾經受到的來自知識界的輕視和羞辱仍然不能釋懷。他針對這一群體的貶損常常十分尖刻:“活在中國作一個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讀書圈兒里。大多數人都十分懶惰,拘謹,小氣,又全身營養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盡管早已是“讀書圈兒”中的一員了,但沈從文顯然將自己這個“鄉下人”與“大多數人”劃清了界線。
《八駿圖》的前半部分里,作家與主人公達士先生的目光是一致的。達士先生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以“醫生”自居,認為其他七位教授“皆好像有一點病”,而病因也被達士先生帶著會心的微笑輕易看穿:“這些人雖富于學識,卻不曾享受過什么人生。便是一種心靈上的欲望,也被抑制著,堵塞著。”接著,作家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分別展示了七位教授的病狀。然而在這一大段的精神展覽中,作家自己的隱秘心理也同樣呈露出來。個體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凌駕于他人之上的行為是對自卑心理的掩飾,“由于自卑感總是會帶來壓力,所以相伴而來的常常是補償性的舉動”。可以說,作家是在展覽七位教授病態精神的同時,完成了對由早年受文化知識界冷遇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補償。
但沈從文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自卑者,他對自己的隱秘心理是有所知覺的,并在創作中流露出自我超越的意圖,這在《八駿圖》中也有所體現。
當教授們的病狀展覽完畢之后,作家的視角就開始逐漸后移,最終將目光投向了主人公自身。這篇小說是帶有自傳色彩的,當作家將解剖刀對準達士先生時,其自我超越的意圖就顯現出來。達士先生一面對其他七位教授的隱秘性心理流露出蔑視和鄙夷,自己卻也不自覺地受了“海”的引誘,患上了與其他教授相同的“病”。小說漸近尾聲,反諷的筆調也愈發明顯:“一件真實事情。這個自命為醫治人類魂靈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樣毫不留情的譏諷或許可以理解為作家自我超越的決心。但根據阿德勒的理論,自卑者有時會樂意承認自己的弱點以隱藏其對支配地位的迷戀。據此來看,沈從文對達士先生的無情解剖可能只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種體現,其自我超越的意圖恐怕未必能夠真正達成。
二、在現實與夢幻中找尋真善美
盡管從《八駿圖》等描寫都市情狀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現實批判成分,但沈從文的眼光顯然不止停留在批判的一面。相應地,人們也不能將作者對湘西世界的書寫簡單地理解為浪漫抒情。
宗白華認為,詩人藝術家可具有醉與醒兩種態度:“詩人善醒,他能透徹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真境實象……但詩人更要能醉,能夢。由夢由醉詩人方能暫脫世俗,超越凡近……”沈從文的創作就有此傾向。除了對現實的深切體察,作家對自然、生命、美也有著獨特的思考,在這樣的雙重觀照下,沈從文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現實與夢幻結合的創作方式,也正因為此,才可見出沈從文創作的深度。
從具體的文本看,即便是《八駿圖》這樣的反映“現實的丑”的作品,其中也包含著大量“夢幻的美”的因子,這顯然與一般的批判諷刺小說有明顯不同。沈從文在記錄了《八駿圖》創作過程的回憶性散文《水云》中描述了自己在青島海邊的體驗:“我一面讓和暖陽光烘炙肩背手足,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熱力,一面即用身前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我的生命。時間長,次數多,天與樹與海的形色氣味,便靜靜的溶解到了我絕對單獨的靈魂里。”顯然,作家的感受是美的,并十分自然地將它融入了作品之中。小說中每每出現自然景物的描寫時,作家的筆觸都是散文化的、詩化的,作家顯然毫不在意將這些美的成分穿插在對教授們病態心理的描摹之中。作家的情緒是處在醉醒間的,只是捕捉內心的感受固定成文本,而并未刻意將小說作為純粹反映和諷刺現實的創作,而文本的意味也隨之豐富起來。同樣地,在《邊城》《三三》等寫鄉村的作品中,除了展現美好的人與物,作家對湘西世界漸漸失落的不可抗性也有著清醒的認識,這也正是作家徘徊于夢幻與現實之間的體現。
除了天生內心纖細而敏感外,個人經歷是沈從文產生此種創作傾向的重要原因。沈從文有著強烈的超脫現實的需要,他說:“人生實在是一本大書,內容復雜,分量沉重……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許看的事跡。我得稍稍休息,緩一口氣!”他要通過創作建造一座希臘小廟,一處充滿真善美的神圣之地,用以休息喘息,療愈靈魂。
但是,沈從文從沒有耽于夢幻,他在創作中保持了作家應具有的自覺意識。純然的理性表達或許深刻,但也格外沉重;而無節制的感性抒發往往呈現為一種個人化的境界,使讀者難以進入。從這個角度看,沈從文的創作無疑是有節制、有節奏的,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種柔和的張力,意蘊豐富且不失可讀性。
三、在傳統與現代中探索文體形式
沈從文有“文體作家”之稱。夏志清認為,沈從文在創作初期由于不諳西方小說技法又未曾受過正統訓練,是“難得有幾篇沒有毛病的”,但是對沈從文創作成熟期的敘事藝術給予了肯定:“在他成熟的時期,對幾種不同文體的運用,可以說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在創作實踐中,沈從文逐漸認識到了文體形式的重要性,并進行了持續的探索。
《八駿圖》中,文體的糅合運用十分明顯。當寫到青島海邊的自然風光時,小說的節奏明顯慢了下來,呈現出散文化的特點。例如,達士先生在給未婚妻的信中所描寫的窗外景色:“我房子的小窗口正對著一片草坪……上面點綴了一些不知名的黃色花草,遠遠望去,那些花簡直是繡在上面……草坪盡頭有個白楊林,據聽差說那是加拿大種白楊林。林盡頭是一片大海,顏色仿佛時時刻刻皆在那里變化;先前看看是條深藍色緞帶,這個時節卻正如一塊銀子。”
《八駿圖》還顯示了沈從文在創作成熟期對敘事模式的探索。小說中存在著“故事套故事”的敘事方式。教授丙給達士先生講了一段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有“病”的,這個嵌套的故事與小說本身所講述的故事是同構的,加強了反諷效果。與《八駿圖》同時期創作的《月下小景》,同樣是以人物講故事的方式結構小說的。盡管仍屬于傳統的“說/聽”模式,但是作家顯然有意識地運用敘事技巧來擴張小說的意蘊,這種敘事方式與沈從文早期的作品有較大區別。
沈從文敘事方式的轉變在《燈》(1929)這篇小說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小說開篇寫道:“因為有個穿青衣服底女人,到X住處來,見X桌上的一個燈,非常舊且非常清潔,想知道這燈被主人敬視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給這青衣女人關于這個燈的一件故事。”然而在小說結尾處,X不小心說出了這盞燈是“借他們樓下姨娘的”,燈的故事的真實性頓時消解,形成了另一種意蘊更加豐富的反諷。這與當代先鋒作家喜用的“元敘事”十分相似,沈從文在敘事探索上的創造性可見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沈從文不斷嘗試形式上的創新,卻并未輕視故事本身。有論者認為:“在現代作家中,沈從文是強調小說故事性最用力,對‘去情節化傾向批評最激烈的一個。”談及小說創作,沈從文認為,“就‘技巧二字加以詮釋,真正意義應當是‘選擇,是‘謹慎處置,是‘求妥帖,是‘求恰當”。可見沈從文對文體形式的創新追求,出發點與當代先鋒作家是迥然不同的。《八駿圖》中,對教授們潛意識的狀寫,作家采用的是速寫的方式,給人層層推進、娓娓道來的感覺,形式上具有創新性,而對每個人物不同的速寫角度又使小說情節得到了豐富,故事性增強,最終呈現出一個意味無窮的文本。這是作家精心“選擇”的結果。由此可見,沈從文對小說形式與內容的理解是辯證的:形式與內容是互相“選擇”的,配合得當,才能“妥帖”和“恰當”,才是好作品。
四、結語
沈從文的小說創作數量十分豐富,無論是題材還是形式都富于變化,顯示出作家復雜的創作動機,其中的內涵和意蘊是值得讀者反復發掘的。盡管沈從文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個人經歷的影響,但對藝術的摯誠、對自然和美的熱愛使他的作品充溢著人文關懷和豐富深邃的意蘊,給讀者帶來了新鮮而美好的審美體驗,也為中國現代小說史添上了不可忽視的一筆。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