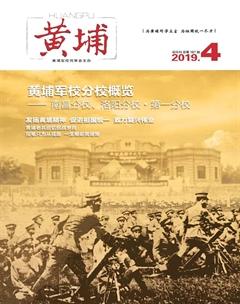我與《黃埔》雜志
顧少俊
上世紀90年代,我在朋友家中看到幾本《黃埔》雜志,隨手翻了一下,很快就對這本雜志產生了興趣。《黃埔》雜志里的文章大多是親歷抗戰的老兵們寫的,文字樸實無華,內容真實感人。以后,我經常看《黃埔》雜志,看完后推薦給同事、同學。他們都認為這本雜志不錯,最大的特點就是真實。
《黃埔》雜志讓我了解到,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幫助下創辦的,建校的初衷是“創造革命軍隊,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黃埔軍校以“親愛精誠”為校訓培養軍事政治人才,組成以黃埔學生為骨干的革命軍,目的是武裝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國民革命。
1926年夏天,國民革命軍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戰歌出師北伐。黃埔教官們在北伐軍中擔任領導職務,黃埔生們在基層帶兵,部隊士氣旺盛,不到10個月的時間,打敗了封建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幾十萬大軍。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再度攜手,兩黨黃埔師生無役不與,200多黃埔師生擔任師以上軍職,指揮全國三分之二部隊。抗戰中,黃埔師生奮不顧身、血灑疆場,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黃埔》雜志讓我知道,我們身邊還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經歷過戰火硝煙,也見證了祖國的發展和強大,他們豐富的人生閱歷是國家和民族珍貴的記憶。幾年前,省委統戰部的一位領導讓我把全省100多位黃埔抗戰老兵采訪一遍。我非常高興接受這樣的任務,這是一個和黃埔抗戰老兵零距離接觸的機會。黃埔抗戰老兵是不可再生資源,如果不搶救那一段歷史記憶,以后就永遠沒有機會了。和老兵們頻繁接觸的那幾年,是我一生中珍貴的記憶。
2015年8月,我到沛縣楚埠村采訪一位叫沙以德的黃埔抗戰老兵。公交車開到半路停了下來,前面修路走不了。我問當地人:“這里離楚埠村有多遠?”那人說,還有幾十里。我決定走過去,周圍人都吃了一驚,炎熱的夏天,烈日當空,坐在家里身上都不斷地淌汗。這樣的天氣,步行幾十里,簡直不可想象。那天,我從上午9點多開始步行,中間沒有歇一口氣,一直走到下午2點多,才在楚埠村找到沙老的家。沙老躺在床上,神思還很清楚,我心中一喜,心想此行不虛。誰知采訪了一半,沙老的兒子堅決制止我采訪,說:“我懷疑你是騙子。”并說出理由:“第一、省里安排你到我家采訪,縣里怎么不用車子送你過來。第二、這么熱的天,你坐公交車,步行5個多小時,讓我無法想象。我懷疑,你肯定有什么其他目的。”我把介紹信拿給他看,對他說:“你可以打電話到省里核實。”他仍然不相信,采訪不得不停止。幾個月后,他打電話向我道歉,說錯怪我了。我又一次去楚埠,才完成采訪任務。
有朋友對我說:“這些老兵都是90多歲的人了,你對他們好,他們沒有能力報答你。他們的后代還會誤解你,你這樣做何苦呢?我們也奇怪,你的動力是從哪里來的呢?”我說:“《黃埔》雜志給了我力量和勇氣。《黃埔》雜志像一個精神寶庫,里面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每當采訪遇到困難時,翻開雜志,心中就會豁然開朗。特別是‘黃埔精神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忠勇赴國難,癡心為統一等欄目和文章,更是給我啟迪和奮勇向前的力量。”
黃埔老兵徐壽山參加過武漢會戰,當時他在25軍任排長。我根據老人的回憶,寫了《鏖戰南潯線》一文,文章被《黃埔》雜志采用。徐壽山家在淮安漣水,當時老人102歲,采訪的時間不能長,我前后去了3次。從我家到漣水要坐3個多小時的汽車。我不怕辛勞,老人每講一點,我都認真記錄。文章發表后,我接到一位抗戰老兵后代打來的電話,他說:“我爸爸1937年參軍,也在25軍。參軍后,家里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你能幫我問問老人,他認識我爸爸嗎?我不奢望他還活著,只想找到他犧牲的地方。”我遺憾地告訴他,老人在我采訪兩個月后過世了。
在黃埔老兵家中采訪發現,他們把《黃埔》雜志視為至寶,搬家時,其他東西都可以不要,但《黃埔》雜志一期都不能少。黃埔老兵呂振錕說:“現在《黃埔》雜志越辦越好了,內容豐富,文章優美。”呂老曾通過《黃埔》雜志找到他的貴州同學黎克松,對《黃埔》雜志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由此可見,《黃埔》雜志是黃埔老兵、黃埔后代之間聯系的紐帶。
采訪老兵的那幾年,《黃埔》雜志擴增到96頁,全彩印刷,并推出“我的軍校生活”“兩岸關系展望”“中國遠征軍”“黃埔老兵的人生紀實”“我心中的黃埔前輩”“黃埔老人的幸福晚年”“臺兒莊大捷”等主題策劃,可讀性、史料性大大增強。《黃埔》雜志每一期我都認真閱讀,每看一次都會有新的感悟。外出采訪,我也把雜志帶在身旁。
2017年,我采訪揚州黃埔老兵汪安民時,他拿出他姐夫生前寫的回憶錄給我看,告訴我,他姐夫陳華是黃埔軍校5期生,陸軍大學將官班2期畢業生。抗戰期間,陳華在二戰區和八路軍并肩戰斗,多次合作,取得了一次次輝煌勝利。
我想起《黃埔》雜志上有老兵寫過第二戰區國共合作打鬼子的一篇文章。忻口會戰期間,5萬日軍在50輛坦克、20輛裝甲車、幾十架飛機的掩護下,猛攻衛立煌部隊的陣地。衛立煌部隊傷亡慘重,壓力很大。朱德命令八路軍129師夜襲日軍陽明堡飛機場,一舉炸毀24架日機,使日機數日內無法對忻口正面作戰的友軍實施轟炸。那篇文章是一個基層軍官寫的,雖然不太詳細,但抗戰期間二戰區是國共合作的典范卻是不爭的事實。陳華當時任14軍10師30旅58團上校團長,他的回憶很有史料價值。我看了回憶錄后,參考相關資料寫了一篇《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文章。文章發表后,讀者反響很好。《黃埔》雜志讓我懂得,真實的文字才能打動人,采訪老兵不能隨意加上自己的臆想和推斷,必須真實地寫出老兵們的所見所想。
《黃埔》雜志自1988年創刊以來,秉承“為黃埔同學立言,為祖國統一盡力”的宗旨,登載黃埔抗戰老兵們以及黃埔后代的故事,關注臺海形勢,宣傳黨的對臺方針政策。《黃埔》雜志傾注了編輯們的汗水和心血,他們為弘揚黃埔精神,促進國家統一兢兢業業地工作。多年來,我對《黃埔》雜志的喜愛有增無減,今后,我還會一如既往地認真閱讀《黃埔》雜志。世界炎黃是一脈,天下黃埔是一家。我相信兩岸統一的那一天一定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