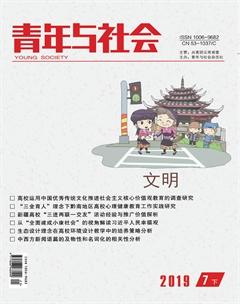解讀安德森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概念
辛睿
摘 要:民族和民族主義作為現代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最活躍的部門之一,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話題。文章嘗試以安德森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概念為討論中心,結合筆者關于民族主義問題的思考,力圖深化對“民族”與“民族主義”概念的認識。
關鍵詞:民族;民族主義;概念解讀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逐漸被建構到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中,與此同時,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動態發展,也引起了許多備受矚目的社會問題。盡管目前對于民族與民族主義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但在綜合的理論研究特別是一些基礎概念問題上仍然缺乏共同認識。作為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起源與散布》中,安德森將民族、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認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從社會、文化、心理等角度剖析了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為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考途徑。
一、安德森其人
本尼迪特·安德森是愛爾蘭裔,但他出生在中國云南,從小就在一個充滿中國風味的家庭環境里成長。由于戰爭,早期有過幾年不得回家鄉的“流亡”經歷;青年時期,遠赴美國投入印尼研究;博士期間,更在雅加達學習和生活過;這些經歷使安德森對印尼、爪哇等地區的研究產生滿腔熱情,與他日后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態度、對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同情立場密切相關。1972年,被禁止入境印尼之后,他將研究目光轉向了東南亞的其他國家,這對他關于東南亞地區、乃至亞洲各殖民地地區的道德同情情懷的產生有重大影響。他幾乎一生流浪于異鄉,對殖民地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被譯者吳叡人稱作“一個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戲的觀眾”。
二、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想象的共同體
在安德森給出自己關于民族的定義之前,斯大林是這樣定義民族這個概念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與此不同的是,安德森回避了尋找民族客觀特征的障礙,認為民族是集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它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民族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它是一個想象的過程,同時,還具有很強的政治性訴求。
筆者認為民族的政治性是將其與部族或族群等與民族有著相似社會—文化特性的概念所區分開的最顯著的特征,即可以將民族認定為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但安德森在凸顯民族的政治性特征的基礎上還強調了民族是具有主權的,“因為這個概念誕生時,啟蒙運動與大革命正在毀壞神諭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性。”誠然,“民族發展臻于成熟之時,人類史剛好步入一個階段”,民族產生于現代化的過程中是現代性的重要表現,我們可以將民族與現代化的進程視為一種由某些共同的、特定的因素促進因而幾乎在同一時間段產生,并且產生的過程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但并不如安德森所說“…衡量這個自由的尺度與象征的就是主權國家”,真正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民族構成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然而事實上,這種極端的情況從未出現過,民族國家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現代國家的代名詞。
三、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
安德森從文化根源來探討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這也為研究民族主義探索出新的研究方向。因為盡管政治共同體是民族主義很重要的訴求,民族主義無疑要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根基。安德森探討民族主義和其起源與散布的歷程時,不但從傳統史學研究所關注的政治、經濟等領域探究民族主義的發展,更開創性的以社會、文化的視野,分析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安德森認為“民族的屬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紀末被創造出來,其實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復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這些“歷史力量”被總結為兩個重要的歷史條件——認識論上的先決條件與社會結構上的先決條件。認識論上的先決條件分為三點:宗教信仰和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它們給民族主義的產生搭建了舞臺。但與民族一樣世俗的、水平的、橫向的共同體還有很多,民族主義脫穎而出還需要另一個先決條件,即社會結構上的先決條件:資本主義印刷科技和人類的語言宿命的多樣性。
宗教共同體的式微。安德森將中世紀以前的宗教信仰稱為“宗教共同體”,語言和教義共同粘合了這個共同體,但在中世紀后期,歐洲以外地區的地理發現,“急遽擴大了文化和地理的視野,也因而擴充了人們關于人類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加之拉丁文統治地位的喪失,使宗教共同體走向了衰落。
王室的衰微。古典王室的君權大都來自神授,君王能夠輕易的通過神授的合法性實現對臣民的統治。但隨著神圣君主的合法性的式微,君主為了鞏固與延續自己的統治開始尋求新的規則。正如安德森所說:“在舊的正當性原則無聲無息地消亡之際,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標志”以求保住其僅存的合法性了。”
對時間理解的改變。隨著世俗科學的發展,時間的概念清晰的體現在日歷和時鐘上。雖然一個人一生至多能遇見與認識的不過是自己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罷了,但人們卻相信在同一個時間上,他們進行著穩定的、匿名的活動。隨著印刷報紙的普及,人們更加清晰的認識到:就在此時,自己的同胞也在閱讀著相同的報紙。
如果說文化根源為“想象”民族主義搭建了舞臺,那么社會結構的改變則是民族主義的產生的必要的條件。“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語言,安德森認為早期人們“想象”民族就是通過閱讀文字實現的。正如安德森所說,隨著拉丁文作為世界性語言的霸權地位的喪失,地方性語言開始發展,通過小說和報紙,地方性語言的整合能力得到提升,這為想象一個民族的共同體孕育了胚胎。
四、結語
作為民族主義研究理論范式中建構現代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安德森通過闡明印刷資本主義與新的政治共同體的產生過程中相互作用和影響的關系,不僅論證了民族形成是一種現代的創造過程,更表明了民族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不是民族產生了民族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為民族主義研究中的現代主義派別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安德森關于民族主義的研究的另一大貢獻和富有“哥白尼精神”的理論是他打破了在他之前的被困于歐洲語境的民族主義研究,不再將民族主義的散布過程敘述為一個由歐洲向世界擴散的故事,即民族主義并不是歐洲的產物。這或許和他本人青少年的求學經歷和長期在東南亞做田野調查的經歷相關,了解安德森生平的人都知道,他的經歷和思想與當時傳統的西方學者有很大不同。他提出了民族主義起源于北美殖民地地區,指出第一波民族主義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南北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克里奧爾”民族主義。安德森的話語打破了那些認為民族主義是以歐洲地區為中心區域,向世界其他地區擴散的當時西方學界主流的觀點,他關于民族主義起源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創新和突破。
除此之外,與其他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著作相比,安德森這一著作以廣泛多元的視野和強調關注社會和文化的“新史觀”,“重新勾畫了 17世紀以來的世界史, 顯示出淵博的知識和強大的敘述能力 。”他把視野關注于常被人們忽略的文化角度,深刻地探究了民族主義的文化根源,他不再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更復雜和深刻的社會文化現象,即“文化的人造物”。
安德森這種視角這不僅為學術理論做出貢獻,其現實意義更在于當我們面對變化的民族主義問題時,可以從政治以外的社會、文化等角度進行研究和思考。
參考文獻
[1] 本尼迪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起源與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M].2011.
[3] 姜鵬.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對歐洲現代民族主義的考察[J].歐洲,2000(03):70.
[4] 吳瑛.多維視野下的民族主義的詮釋——評本尼迪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起源與散布>[J].當代亞太,2008(02):143-152.
[5] 陳獻光.解讀霍布斯鮑姆的“民族”概念——以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為文本[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4):95-97.
[6] 王文奇.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構建析論[J].史學集刊,2011(03):10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