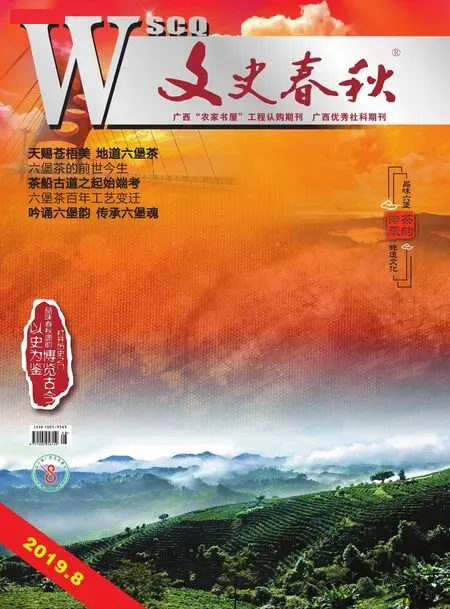六堡茶百年工藝變遷
2019-09-02 14:07:22彭三口
文史春秋
2019年8期
關鍵詞:工藝
● 彭三口

回首百年前,正是六堡茶的黃金歲月,據當年的老茶人回憶,清末民初,由于海外需求量逐年遞增,六堡茶區里漫山遍野都是茶園,人們忙著采茶、制茶、炊蒸壓簍、裝船運輸,每年數10萬斤,最高峰時近100萬斤(注:此數據乃六堡一區而言,真正的六堡茶連同當時賀縣即今賀州市八步區水口一帶,應該超過100萬斤了)的六堡茶沿著六堡河、東安江、賀江、西江所構成的“茶船古道”遠銷南洋,以價廉物美而享譽海內外。由六堡茶而帶動的如竹編、木柴、制炭、運輸、雜貨貿易等也出現了繁榮景象。
這100多年來,六堡茶幾經滄桑,幾歷戰火,幾番盛衰,茶樹被砍、被棄,茶園復墾、再荒蕪,再種植、再閑置,幾多曲折與磨難,歷經時局動蕩及戰火洗禮,歷經土改茶山再分配,歷經復興公社茶場,歷經重振公社茶園的大生產,以及生產隊建立初制廠、公社發展精制廠等等,可謂坎坷。在1937年出版《廣西特產物品志略》里面有記載:“在蒼梧之最大出品,且為特產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區而言(五堡,四堡)俱有出茶,但不及六堡之多,每年出口者,產額在60萬斤以上,在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間(1926—1927年),每擔估價30元左右。”
20世紀初,正值產銷巔峰狀態的六堡茶到底是怎么樣的?在名茶眾多的中國,為何能闖出這么一片廣闊的僑銷市場?百年前六堡茶工藝和品質是怎樣的?
百多年來,六堡茶的產區和銷區(嶺南及馬來西亞錫礦區)如同滄海桑田,變化巨大,六堡茶多次盛衰起落,戰火與自然,所幸,經過筆者在海內外多方尋找,找到了一些文獻資料及六堡茶老茶實物,能比較客觀地推斷出當年的六堡茶種植、生產以及品質狀況。……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特種設備安全(2022年5期)2022-08-26 09:19:32
礦產綜合利用(2020年1期)2020-07-24 08:50:40
山東冶金(2019年6期)2020-01-06 07:45:54
收藏界(2019年2期)2019-10-12 08:26:06
世界農藥(2019年2期)2019-07-13 05:55:12
世界農藥(2019年2期)2019-07-13 05:55:10
模具制造(2019年3期)2019-06-06 02:11:00
山東工業技術(2016年15期)2016-12-01 05:30:59
銅業工程(2015年4期)2015-12-29 02:48:39
新疆鋼鐵(2015年3期)2015-11-08 01:5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