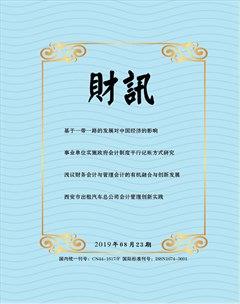淺析房地產企業融資的困境及對策
田昊
摘 要:在房住不炒及防范金融系統性風險的背景下;本文從房地產企業融資特點出發,闡述了企業融資現狀,分析影響企業融資困境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我們認為,未來房地產企業應增強自身競爭力,積極探索新型融資業務,必將走出融資困境。
關鍵詞:房地產企業;融資;政策
在“房住不炒”、“租售同權”的經濟背景下,在整頓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環境下,國家陸續出臺多項房地產調控政策,使房地產企業的融資業務面臨一定的困境,本文打算從房地產企業融資特點及現狀出發,對影響企業融資因素進行探討,對房地產企業走出融資困境提出對策,為房地產企業走出融資困境提供借鑒意義。
一、房地產行業融資特點
(1)融資業務受宏觀調控政策影響性強
回顧房地產行業市場化改革以來,國家對地產行業的調控政策相伴而生,調控的領域包括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等,這些政策既影響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資金投放量,如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也影響著企業的融資形式和渠道。
(2)融資渠道多樣,各渠道發展不均衡
房地產企業可用的融資渠道眾多,包括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境內市場包括銀行貸款、股權融資、債券融資,非標債權融資、融資性租賃、房地產私募基金,資產證券化等。境內市場融資目前主要集中在銀行貸款、非標債權及債券融資等傳統方式,在境內外市場融資業務比重方面,境內市場目前依然是房地產企業的主要融資方式,境外市場融資近年發展較快,房地產企業在境外市場的發債規模不斷擴大,但境外融資比例依然較低。
(3)融資與企業資質相關
企業資質包括企業背景、規模、商業模式、運營能力等相關因素,通常央企較民企更容易獲得資金,民企中規模大、信用評級高、綜合實力強的企業更易獲得金融機構青睞,同時企業的融資規模也與商業模式及運營能力相關,如針對商業地產項目的經營性物業貸款更看重房企的商業模式,同時經營貸款的規模與經營物業的租金價格、租金收繳率息息相關;以收益權為底層資產的資產證券化融資,更看重收益的穩定性和未來增長空間。
二、房地產企業融資困境的表現
(1)政策調控力度加大,融資渠道收緊。為了貫徹“房住不炒”、“三去一降一補”經濟政策,規范整治金融環境,國家加大政策調控力度,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緊縮,2018年房地產行業出現了最難融資環境,銀行貸款額度吃緊,中小房企難以取得項目開發貸款,花樣年、碧桂園、富力、合生創展發債全部遭遇中止,公司債大幅萎縮,信托規模增速下滑。
(2)融資成本持續攀升。隨著融資渠道收緊,市場融資成本持續高漲,據統計,2017年房地產企業國內平均融資成本約為8%-9%左右,2018年國內平均融資成本已經超過12%,即便如此,眾多中小房地產企業依然難以融到資金。
(3)融資風險制約企業融資。融資風險包括企業的信用評級、項目區位及產品結構、操盤團隊的項目經驗、經營業績等等,它關乎金融機構能否按時足額收回借款,那些依靠過度舉債,自身競爭力不強的企業必定面臨融資難的困境。
三、融資影響因素分析
(1)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2015年以來,房地產市場重現火爆狀態,交易量和價格飆升,嚴重干擾廣大居民對房屋的居住需求。黨的十九大提出房住不炒,租售同權政策,提倡大力發展保障房和租賃住房建設,并在金融、稅收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具體房地產企業融資方面,銀行貸款和債券融資都加大對保障房和租賃住房產品的投放力度,以銀行貸款業務為例,從2016年3季度到2018年1季度,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增加值3.42萬億元,其中投向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余額增加值2.66萬億元,占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增加值的78%,投向非保障房項目的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長緩慢,房地產企業獲取銀行貸款更加困難。
(2)金融監管政策影響分析
近幾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金融市場也推出了眾多“創新產品”,土地融資、房地產首付貸產品相繼出現,為了規避金融市場監管政策,各類金融產品利用政策漏洞,實行多層嵌套,加大財務杠桿,資金池業務盛行造成資金期限錯配,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場風險,各類資金紛紛涌入房地產行業,行業融資亂象叢生。為了整頓金融秩序,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國家出臺眾多金融監管政策,短期內對房地產企業融資業務造成較大沖擊,造成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
銀行業務方面,2018年1月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管理辦法,對委托貸款的資金來源及用途進行明確界定,辦法發布后,房地產企業委托貸款業務處于急劇萎縮狀態,信托借助銀行的通道業務被封閉。
信托融資方面,以“業務合規”為原則,堅決堵塞各類資金通道類業務,銀保監會發布的關于銀信類業務的通知中明確約定商業銀行和信托公司開展銀信類業務,不得將信托資金違規投向房地產,同時各種通過信托繞道進行土地款融資業務已基本暫停。
資管類業務方面,2018年相繼發布資管新規及細則,要求加強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向上穿透最終資金來源,向下穿透最終資金投向,對資管計劃投資于非標債權的規模進行明確限定,資管新規嚴禁資金池業務,禁止資管產品期限錯配,明確限制通道類業務,禁止資管產品多層嵌套,嚴控杠桿,直接使房地產投融資杠桿和資金規模大比例下降。中基協也加強對地產類私募基金的備案審查,對于私募基金投向房地產債權類資產業務停止備案。
金融監管政策的出臺,一方面規范金融市場秩序,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同時也強化金融監管政策的效果,有效地整頓了各類金融機構資金池和通道類業務,短期內對房地產企業融資帶來沖擊。
(3)房地產企業自身影響分析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集中度不斷提升,市場的頭部效應更加明顯,傳統的融資渠道更看重房地產企業的背景、規模、信用等級等。銀行融資方面,銀行貸款實行白名單管理,更青睞于央企及規模民企,客戶基本分布為地產百強企業及地方龍頭企業,因此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處于銀行白名單上的房企開發貸額度較為充沛,而中小型房企在銀行端開發貸的融資沒有得到改善。
債券融資方面,上交所及深交所對房企發行公司債進行分類監管,采取了“基礎范圍+綜合指標評級”的分類監管標準,發債主體的基礎范圍包括主體評級AA及以上的上市房企、央企、省級政府、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地方政府所屬企業、房地產行業協會排名前100的其他民營非上市企業。對企業綜合指標評級包括企業的總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凈利潤及房地產業務非一、二線城市占比是否超過50%等指標,根據房企觸發綜合指標的數量將房地產企業分類為正常類、關注類和風險類,加強對關注類和風險類企業的風險管控,提高了房企的融資門檻。
(4)金融市場影響分析
房地產企業融資形式多樣,包括銀行貸款、股權融資、債券融資,非標債權融資、資產證券化及私募等,金融市場種各種融資渠道發展極不平衡,據統計,傳統的融資渠道如銀行貸款、非標債權融資占企業外部融資60%-70%,而這兩種融資渠道是目前政策調控的主要對象,股權市場由于受調控政策影響,房企IPO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利用定增等方式募集資金的規模和頻率被進一步壓縮,其他融資形式所占比重較低,房地產企業常用的融資渠道狹窄,融資壓力依然較大。從金融市場分布看,房地產企業融資業務依然以境內市場為主,境外市場為輔,境外資金運用規模和效率依然不高。
四、房地產企業融資對策
(1)房企適度參與保障房及租賃住房建設
在房住不炒、租售同權的政策基調下,保障房及租賃住房市場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大部分城市土地出讓中明確約定配建保障房或租賃住房,在國家加強對保障房及租賃住房的資金政策扶持下,銀行貸款及債券融資渠道投向保障房及租賃住房的資金比重不斷提升。房地產企業應轉變思維,適度發展保障房及租賃住房建設,如國有或國有控股的房地產企業可以在短期融資券或中期票據等債券端募集資金,萬科、碧桂園等房企已經通過資產證券化形式募集大量資金用于租賃住房建設。
(2)加強企業信用建設,提高自身競爭力
傳統的融資業務均是以企業的信用等級作為背書,信用等級高的企業不僅可選擇的融資渠道更多,而且融資成本更低,更受金融機構的青睞,當前金融環境更加支持對優質企業的政策支持,企業應大力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同時,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新型融資業務更加關注企業的商業模式和運營能力,關注企業未來的經營業績和現金流管理水平,企業融資不僅僅是財務部門的職責,需要房地產企業全員努力,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
(3)積極拓展融資渠道,大力發展新型融資業務
房地產行業融資渠道眾多,各種渠道融資發展極不平衡,目前房企融資主要集中于銀行貸款、非標債權融資等傳統融資方式,其受調控政策影響較大,而對于資產證券化等新型融資業務,目前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國家政策也大力支持發展資產證券化融資業務,包括供應鏈融資近年方興未艾,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另外,房地產企業境外融資比重雖然較低,但近二年出現快速發展的態勢,房地產企業應放眼國際資本市場,進行積極融資探索。
(4)引進戰略投資者、通過合作開發等模式解決資金不足
金融監管政策基本堵塞金融機構的土地款融資業務,對于資金薄弱的中小企業而言,其自身資金不足以撬動項目發展,可以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合作開發、小股操盤等方式解決資金不足問題。
總體而言,在房住不炒、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基調下,為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調控政策,使金融市場秩序得到及時整治,降低企業的財務風險,短期內對房地產企業融資造成較大沖擊。我們應該看到,國家同時鼓勵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新型融資業務,隨著新的融資產品不斷出現,企業自身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金融市場必將助力房地產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房地產企業必將走出融資困境。
參考文獻
[1]喻婕.淺析房地產企業融資的困境及出路[J].中國集體經濟,2019(10):111-112
[2]羅業輝.淺析中小型房地產企業融資困境及對策[J].會計師,2017(12):47-48
[3]李傳鵬.我國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困境與創新[J].經貿實踐,2017(23):128
[4]劉杰.淺析企業融資的困境與出路——以民營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為例[J].中國商論,2019(06):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