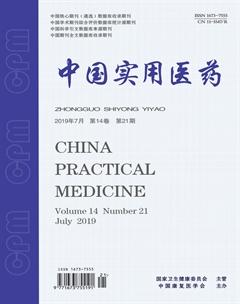神經調控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臨床研究
倪歡歡
【摘要】 目的 探討神經調控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臨床效果。方法 20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隨機分為A組(70例)、B組(70例)及C組(60例)。進入第1周導入期后, A組接受針刺足三里穴(ST36)治療, B組接受針刺內關穴(PC6)治療, C組接受假性神經調控治療, 均接受為期4周治療后進入1周洗脫期, 然后三組患者均接受ST36+PC6治療4周。觀察比較三組消化不良癥狀、焦慮自評量表(SAS)、簡明健康狀況調查表(SF-36)評分及胃容受性水平。結果 2個療程結束后, B組、A組消化不良癥狀、SAS評分均低于C組, SF-36評分均高于C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組消化不良癥狀評分(10.18±2.00)分、SAS評分(45.76±3.11)分均低于A組的(13.36±2.51)、(49.16±3.26)分, SF-36評分(92.10±2.53)分高于A組的(87.87±2.66)分,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組、A組初始胃容積量、最大胃容積量均明顯大于C組, B組初始胃容積量(368.69±39.80)ml、最大胃容積量(726.60±47.68)ml均明顯大于A組的(312.27±36.66)、(651.28±44.09)ml,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通過神經調控能夠改善患者胃容受, 緩解臨床癥狀, 提高患者生活質量。與神經調控ST36比較, 神經調控PC6功效更佳, 可作為首選治療方案。
【關鍵詞】 神經調控;功能性消化不良;胃容受性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9.21.064
一項家庭調查顯示, 人群中有25%左右患者受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困擾[1], 患者可出現腹部脹氣、腹痛不適、噯氣、餐后飽脹、惡心嘔吐等癥狀表現。目前臨床尚未明確其發病機制, 多數認為與胃容受性、內臟敏感性升高及胃排空延遲有關, 臨床多采用促動力藥、改善胃腸運動的藥物治療, 然而本病涉及多種病理生理機制, 同時患者癥狀多樣化, 因此治療效果并不理想, 病程遷延、反復發作。本院近年來在部分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治療中采用神經調控治療, 取得了顯著的臨床效果, 現將具體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6年3月~2018年3月收治的20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作為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①年齡18~65歲;②羅馬Ⅲ關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診斷標準[2];③6個月前經胃鏡確診為慢性淺表性胃炎患者;④血糖、肝腎功能、血常規檢查以及B超等檢查完善, 無器質性疾病。排除標準:腹部手術、精神疾病、妊娠或哺乳期、治療依從性差患者。將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A組(70例)、B組(70例)及C組(60例)。A組男38例, 女32例;年齡18~65歲, 平均年齡(45.68±9.23)歲;病程2個月~8年, 平均病程(2.87±1.72)年。B組男37例, 女33例;年齡18~65歲,?平均年齡(45.70±9.24)歲;病程2個月~8年, 平均病程(2.90±1.71)年。C組男31例, 女29例;年齡18~65歲, 平均年齡(45.74±9.25)歲;病程2個月~8年, 平均病程(2.90±1.72)年。三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進入第1周導入期后, A組接受針刺ST36治療, B組接受針刺PC6治療, C組接受假性神經調控治療, 即針刺ST36、PC6的假性穴位位置, 即不在任何脈絡上。神經調控治療方法:餐后即行電刺激術, 持續2 h。知情的裝置程序設計員對患者進行培訓, 指導患者把電極放在正確的部位, 每個穴位上放2個電極(1個在穴位上, 另1個在穴位所在脈絡相距穴位4~6 cm處), 微刺激裝置位于兩個電極間的皮膚上, 同時行電刺激。刺激2 s/次, 停止3 s, 脈沖頻率為25 Hz,?脈沖持續0.5 ms, 振幅范圍為2~6 mA。ST36位于脛骨與腓骨間, 從外膝下4指寬, 脛骨旁1指寬處;假電針穴位位于ST36外側往下10~15 cm無任何經絡線的部位及PC6距離15~20 cm無任何經絡線的部位。治療4周為第1個療程, 之后進入1周洗脫期, 洗脫期結束后三組患者均采用神經調控治療, 即ST36+PC6治療4周為第2個療程, 治療期間患者無需改變日常活動。患者共入院隨訪5次, 情況錄入后、導入期后、第1個療程結束后、洗脫期結束后以及第2個療程結束后分別隨訪1次。每次隨訪時, 患者均空腹入院并抽取其靜脈血, 檢測胃腸激素血樣。
1. 3 觀察指標及判定標準
1. 3. 1 消化不良癥狀評分 癥狀包括上腹部不適、上腹痛、上腹部脹滿、餐后飽脹感、惡心嘔吐、早飽、胃燒心感及過度打嗝等癥狀, 每個癥狀評分為0~3分, 分別代表無癥狀、輕微癥狀、中度癥狀及嚴重癥狀, 最高分為36分, 分數越高表明癥狀越嚴重。
1. 3. 2 SAS評分 量表由20個問題組成, 每題1~4分, 分別代表“沒有或很少有”、“有時有”、“大部分時間有”、“絕大部分或者全部時間都有”, 以50分為界限, 分數越高則表明焦慮情緒越嚴重[3]。
1. 3. 3 SF-36評分 從生理機能、軀體疼痛、生理職能、一般健康狀況、情感職能、社會功能、精力以及精神健康進行評價, 總得分換算為100分, 分數越高則表明生活質量越高[4]。
1. 3. 4 胃容受測試 患者所能攝入的最大液體體積即為胃容受。禁食12 h后, 患者依照指示按照30 ml/min的速度喝下試餐(0.95 kcal/ml), 直至患者感覺完全飽腹。間隔5 min, 專人對其飽感進行評價[5]。0分:無癥狀;1分:輕微癥狀;2分:輕度癥狀;3分:中度癥狀;4分:明顯癥狀;5分:最大或者難以忍受的飽腹感。達到5分后, 患者停止喝試餐。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兩組比較采用t檢驗, 多組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 三組消化不良癥狀、SAS及SF-36評分比較 2個療程結束后, B組、A組消化不良癥狀、SAS評分均低于C組, SF-36評分均高于C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組消化不良癥狀、SAS評分均低于A組, SF-36評分高于A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 2 三組胃容積量比較 B組、A組初始胃容積量、最大胃容積量均明顯大于C組, B組初始胃容積量、最大胃容積量均明顯大于A組, 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 討論
有研究發現, 近端胃舒張功能受到損害為患者出現消化不良癥狀的主要病理基礎及重要機制, 因此在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療中, 提高胃容受性功能為治療關鍵[6-8]。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B組、A組初始胃容積量、最大胃容積量均明顯大于C組, B組初始胃容積量、最大胃容積量均明顯大于A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可見通過針灸穴位神經調控可以提高胃容受性, 糾正胃電節律紊亂, 從而達到調節自主神經系統失衡的效果。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可出現頑固的上腹部不適、上腹痛、惡心嘔吐、早飽等癥狀, 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同時病程遷延, 胃腸長期處于激惹狀態, 極易引起強烈的焦慮、恐懼感。本次研究中, 2個療程結束后, B組、A組消化不良癥狀、SAS評分均低于C組, SF-36評分均高于C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組消化不良癥狀、SAS評分均低于A組, SF-36評分均高于A組,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分析認為通過將針灸針連接到電脈沖發生器上, 對穴位產生持續刺激, 從而達到人工針灸相同效果;通過穴位刺激, 促進餐后胃動力及胃排空的恢復, 有效改善癥狀, 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綜上所述, 神經調控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 能夠調節自主神經。與神經調控ST36比較, 神經調控PC6功效更佳, 可作為首選治療方案。
參考文獻
[1] 武彥芳.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焦慮狀態的影響因素分析. 山東醫藥, 2016, 56(30):64-66.
[2] 孫菁, 袁耀宗. 對功能性消化不良羅馬Ⅲ標準的淺識. 中華消化雜志, 2006, 26(11):764-765.
[3] 于惠玲, 魯素彩, 孟杰, 等. 馬來酸曲美布汀聯合舒肝顆粒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評價. 中國臨床藥理學雜志, 2016, 32(6):499-501.
[4] 楊大榮. 針刺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效果觀察. 實用中醫藥雜志, 2016, 32(7):714-715.
[5] 時昭紅, 付麗鶴, 趙蕾, 等. 不同證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容受性及胃排空功能差異的臨床研究. 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 2017, 33(6):565-569.
[6] 陳軍, 湯凈, 譚安萍, 等. 體表神經調控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臨床研究. 成都醫學院學報, 2018, 13(1):59-63, 67.
[7] 姜寧, 姚芳, 范一宏, 等. SNM-FP03神經電刺激儀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臨床試驗研究. 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 2016, 40(5):405-410.
[8] 湯凈, 陳軍, 譚安萍, 等. 體表神經調控對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容受及胃電圖的影響. 實用醫學雜志, 2018, 34(3):406-409, 415.
[收稿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