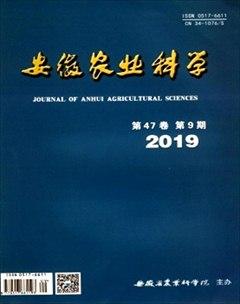社會風險視角下“村改居”轉型社區治理研究
弓順芳
摘要 處理好城市發展速度與質量、發展層次與整體水平之間的關系,高效率、高質量的防范和化解社會風險,全面提升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是地方政府推進城市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城鄉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完善社區治理的法律制度,實現利益博弈的合法化和規范化;轉變傳統的社區治理理念,不斷完善社區風險預警和防范體系;實行“參與式”社區治理,構建社區共同體;及時了解和正確引導社區輿論,優化政府服務方式,促進轉型社區治理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關鍵詞 社會風險;“村改居”;社區治理
中圖分類號 D66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9)09-026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9.074
Abstrac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speed and 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and overall level, high efficiency, high quality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social risks,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re urgently needed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we must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est games;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ommunity risk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ion system;implement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build communities Community;timely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guide community public opinion, optimize government service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Social risk;“Village change”;Community governance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實施了《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最高決策層做出的關于城鄉社區治理的綱領性文件,為我國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村改居”社區是城市化過程中拆“村”建“居”形成的新社區[1],是城市邊緣的農村就地城市化的產物。近年來,我國學者對轉型社區的研究,大多采用傳統的經濟學、管理學研究方法,著眼于宏觀層面上對農村土地配置[2]、人地關系[3]與基層組織[4]方面的研究,而對轉型社區風險治理方面的研究較少。因此,從社會風險的視角對轉型社區進行深入剖析,旨在構建風險防控下社區的多元化治理路徑,創新社區治理模式,為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村改居”社區治理提供經驗借鑒。
1 “村改居”與傳統社會區的區別
“村改居”是一個過程,在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變過程中,它具有構成社區的四大基本要素:特定的地域、同質的人口、相似的文化和特殊的地域感。但與傳統社區相比,“村改居”社區有具有特殊性[5]。
(1)“村改居”社區不僅是一種地理居住形態,還是一種社會形態。一方面,由于特定地緣和血緣構成的原村籍身份將他們結合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原著村民在社會管理方式、思想觀念、居民素質、生活方式和風俗文化等方面,仍然保留著農村社會的特點,并沒有鍍上“城市金”。
(2)戶籍問題并非區別“村改居”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標準。有的“村改居”社區的土地雖然被征用,村民身份由農民戶口已經轉為城市戶口,但是部分村民還未被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福利。
(3)轉型社區的社會風險防控難度大。轉型社區是一個動態概念,各種傳統與現代、城市與農村的復雜要素相互交融。一方面,“村改居”社區的村社共同體作為城市慢節奏人員的庇護所,為不具備市場就業能力的“村改居”社區居民提供了收入來源。另一方面,“村改居”社區與城市社區漸趨相似,逐漸彌合,最終過渡到城市社區。
2 “村改居”轉型社區社會關系的典型特征
馬克思認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6]。在我國,農村社會結構仍然是一個強調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社會關系的取向與社會資本范式有不謀而合之處,但在市場經濟推動下的村莊,過去由國家高度集中配置資源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資源在單位制度之外的分配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并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因此,當人們不再強烈地依賴于單位或集體來獲取所需的社會資源,而是由市場主導下多元化渠道獲取時,社會的個體性、人地關系、社區建設理念隨之發生了變化。
2.1 去集體化后的“碎片化”
2.1.1 轉型社區個體性增強。轉型社區個體性的增強不是農民“原子化”或農村社會的“個性化”狀態,而是意味著集體對農民約束減少,個人獨立自主的行動增多[7]。基于“村改居”轉型社區的居民占小部分的是本村村民,但大部分來自外省甚至外國的流動人口,個體的自主行動范圍擴大,無形中增加了社區管理的難度。擴大了個體的自主行動范圍。
2.1.2 公共服務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去集體化后的社區居民,雖然自治權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釋放,但是在有限社區空間下,如何提高社區公共服務質量、促進流動人口社區融合、構建社區共同體等方面還缺乏相關制度保障。
2.2 人地關系的“模糊性”
“村改居”后,居民身份由農民變為城市市民,管理部門由村委會轉化為居民委員會,土地性質由集體所有轉變為國家所有,經濟由集體經濟轉變為股份合作公司,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隨之趨于模糊。
2.2.1 農民對土地的依存關系日益模糊。農民需要土地,但又愿意接受征地合理條件下放棄土地。
2.2.2 農民使用土地但實際上并不擁有土地。拆遷后村民分配的房屋有的是小產權性質,有的具有完整的房屋產權證,但大部分沒有房屋產權證。例如,鄭州市規定被安置村民補償商品房的房屋產權雖然屬于個人所有,但在獲得所有權5年后才能網簽交易。因此,以集體產權為標志的人地關系發生變化,這意味著農村與農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2.3 行政化社區的“差異性”
大多數“村改居”社區是依靠行政力量進行大量征收、拍賣農村土地,針對城市和農村交匯處的“城鄉結合部”建設的新型社區。由此可見,“村改居”社區是以城市社區的管理體系為參照,通過“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外生行政權力再造而成的行政化社區。因此,以城市面貌、財政收入和經濟指標為衡量標準的轉型社區,農民的生活方式、生計手段和價值取向“支離破碎”。與此同時,改造后行政化社區的人口構成比較復雜,包括本村村民、外來務工人口、陪讀家庭,甚至還有外國留學生,由此對社區功能和結構細分、不同層級居民需求的滿足、基礎設施的供給都帶來不小的沖擊。
由此可見,轉型社區在社會關系上有著不同于一般社區的典型特征,容易出現社區秩序失序與信任缺位等問題。還有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社區認同與歸屬感匱乏、溝通渠道不暢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容易造成社區糾紛甚至沖突的“易燃劑”和“導火索”。
3 “村改居”社區風險因素分析
3.1 利益分配格局失衡 在“村莊變遷”社區建設過程中,存在著利益分配不平衡的現象。“村改居”轉型社區建設過程包括地方政府與村民,開發商和村民,村委會和開發商以及村民之間的多個利益博弈關系,其中,房屋拆遷和重建問題是許多矛盾的焦點。然而,目前的慣例是政府在實施改造時給予村民一定的補貼,村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將歸還給政府。政府將大量農地轉為商業開發,村民無權參與土地收入分配。在拆遷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未能妥善處理與村民的關系,導致暴力拆遷事件。此外,在建設移民社區的過程中,開發商或物業公司也存在住房質量差,公共活動空間減少,未能滿足公共綠地等問題。
3.2 基本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
城市化的本質是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村改居”不應僅僅是城鄉空間的轉變,而是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由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的文化素養普遍較低,雖然征地拆遷補償能夠在短時間內滿足其生活需要,但對于年齡較大,病情較重的居民仍然缺乏維持生計的基本保障。因此,如何構建起失地村民的民生模式,滿足城鄉基本公共產品供給的均等化,避免造成社會階層分化,是轉型社區風險防控的重點。
3.3 社區認同感缺失 社區認同與社區穩定具有正相關性,缺乏社區認同就會降低“村改居”轉型社區的結構穩定性。社區是農民“洗腳進城”的重要途徑,但很多地方的村民“脫鞋而不剝離”,即雖然生活在城市社區,但是并沒有形成相應的社區意識。不少居民依然秉持傳統“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觀念,缺乏對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設施管理的“主人翁”意識。因此,居民對社區認同感不強,缺乏社區凝聚力,進而影響社區結構的穩定性。
3.4 集體經濟生產經營和組織弱化
農村集體經濟轉型以后,基本屬于一個封閉運行的狀態。作為分配組織,村一級土地國有化后,村集體經濟只是選擇最簡單的出租甚至變賣土地的方式與其它單位部門合作,村集體提供廠房和廉價勞動力,合作單位提供就業和教育便利。但由于村集體經濟缺乏現代生產經營經驗和資金支持,集體經濟淪為物業經濟和分配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只有直系血緣的新生人口才有權進入,而且集體經濟組織的社區和物業管理人員基本由原村干部和村民擔任,極少向外聘請。在從搬遷到回遷的過程中,村民經歷了由過去靠土地生活到靠收取租房費用生活,在拆遷改造時期又轉化為靠領取“過渡費”“分散租賃”生活的方式到回遷后同外來流動人口“混合居住”,靠領取社區福利和租賃房屋費用生活的最終階段。集體經濟組織的相對封閉和組織弱化使轉型社區缺少發展動力和條件。
4 構建“村改居”轉型社區風險治理機制
隨著城市社會風險增多,城市脆弱性日漸明顯。在城鄉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完善法律制度,實現利益博弈的合法化和規范化[5],不斷完善社區風險預警和防范體系,實現“參與式”社區治理,加強城鄉社區的相互融合和特色發展,不斷優化政府服務,促進轉型社區治理的和諧發展。
4.1 規范城鄉社區建設工程的實施 法治化、科學化的制度規范是社區治理的先決條件。預防和化解城鄉社區建設中的各類風險:①以社區黨組織建設為基石,以滿足居民需求為導向,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形成基層黨組織領導、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社區治理體系。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對各利益群體的行為進行規范,嚴格界定政府職能邊界,不斷完善社區信息披露和網絡監督機制,監督政府和企業的市場行為。②加強社區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訓工作。提高社區工作者依法行政,落實政策,服務居民的能力,建立一支品質卓越、群眾滿意的社區工作隊伍。最后,完善政策標準體系和激勵宣傳機制,積極開展城市和諧社區建設。規范“消防安全社區”“文明和諧社區”評價體系,提高社區社會治理的質量。
4.2 構建和完善社區風險預警與防范體系 危機是風險的極端形式,預防和化解社區風險,需要根據居民實際需要及時調整公共服務供給。
4.2.1 完善社區應急物資保障,統籌規劃應急物資的調動使用,提高社區應急準備能力。加強信息共享和物資調劑,改變應急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情況。
4.2.2 推進基層應急隊伍建設。依托共青團、總工會、高等院校、基層社區、行業協會和慈善機構等,強化社區應急志愿服務力量。
4.2.3 加強基層應急管理的規范化。量化標準,推進“預案完善、隊伍精英、保障有力”精細化社區建設,做好重大事項決策的風險評估、隱患排查、預警信息傳播和信息上報工作,提高風險防控和危機應對能力。
4.3 創新轉型社區生產經營方式,解決居民安置問題 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精神,政府應通過引入制度外生變量來激活農村生產要素,賦予農民更多的自治權利,創新農業經營模式,為“村改居”后居民的就業創業提供內生性動力[8]。要遵循地區經濟發展規律,將重點放在培育和支持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上,創新和鼓勵現代農業經營方式,解決農民就業問題,并創造良好的公共服務和政策環境。積極培育健康的社區文化,引導居民參與非政府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建立心理咨詢和矛盾內部調解機制,提升社區矛盾預防和化解能力。
4.4 及時了解和正確引導社區輿論 在社區治理過程中,應當及時了解社區輿論的熱點和發展,消退社區“謠言”。“村改居”社區是由長期居住在同一地區的居民形成的熟人關系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社區關系。社區資本在處理社區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對社區公眾輿論產生重要影響。社區居委會要積極加強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建立健全社區與居民的溝通機制。①增強社區公共事務的透明和參與性。建立社區主任定期接待機制,完善政府部門和社區居委會的“互聯網+政務”模式,推進智能社區信息系統建設,增強社區信息共享。②充分發揮社區黨員帶頭作用,及時了解社區居民的利益偏好和需求。例如,社區居委會在評選“低保戶”時,提升評選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性,能夠有效防止社區輿情的異化。
4.5 實行“參與式”社區治理,構建社區共同體 風險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社區公共安全水平,維護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社區居民既是風險治理的主體,也是公共安全產品的服務對象,只有當個人有機會直接參與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決策時,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過程[9]。因此,必須充分動員公眾積極參與風險治理,形成共享共建共治的社會共同體。
4.5.1 樹立風險防控的主體意識。在制訂、執行公共政策和重大項目規劃過程,要將社會風險穩定性評估納入重要考核指標,重視公眾的意見與利益訴求。
4.5.2 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通過常態式的危機模擬演練和培訓等多種形式,強化公眾對社會風險的防控意識,增強其參與風險治理活動的自覺性和協調性。
4.5.3 注重社會工作。要積極動員社會公眾參與志愿行動,通過志愿精神宣傳、公共政策引導、完善志愿者管理制度等措施開發公眾志愿者資源[10],使社會工作成為推進社區治理的重要力量。
5 小結
基于“村改居”轉型社區的風險的主要誘因是經濟原因,具有群體性、范圍廣和擴散性特征。因此,在城鄉社區治理過程中,首先要注重完善社區治理的法律制度,實現利益博弈的合法化和規范化;其次,應急理念要由傳統的“救火式”應急處置理念,轉變為“關口前移”的風險防控理念,加強社區隱患排查治理,不斷完善社區風險監測預警和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最后,推動“參與式”社區治理,通過構建社區共同體,構建更加民主、更加科學和更加安全的社區治理體系。
參考文獻
[1]呂青.“村改居”社區秩序:斷裂、失序與重建[J].甘肅社會科學,2015(3):135-138.
[2] 徐勇.土地問題的實質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問題[J].探索與爭鳴,2004(1):8-9.
[3] 溫鐵軍.“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兩個基本矛盾[J].群言,2002(6):12-14.
[4] 趙樹凱.“公司化”的基層政府[J].中國老區建設,2011(9):13.
[5] 段麗.城市邊緣區“村改居”社區改造案例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學,2006:9.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
[7] 陸益龍.鄉村社會變遷與轉型性矛盾糾紛及其演化態勢[J].社會科學研究,2013(4):97-103.
[8] 謝俊,陳海林.融解、引導與阻燃:“村改居”社區社會風險治理的思考[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14,13(10):36-41.
[9] 張承安,鄒亞楠.反思與路徑:社區共同體建設中的公眾參與[J].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21(1):72-76.
[10] 董幼鴻. 社會組織參與城市公共安全風險治理的困境與優化路徑:以上海聯合減災與應急管理促進中心為例[J].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7(4):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