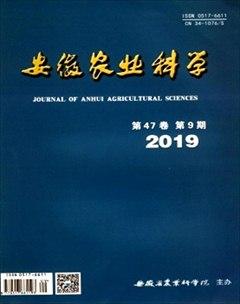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與土地利用分析
張悅悅 夏浩 李翠珍
摘要 不同城郊帶農戶呈現差異化的生計特點和土地利用特點,并存在某種相互影響關系。從農戶層面和區域理念出發,建立農戶生計多樣化與土地利用理論框架,以河北省19個村莊416戶農戶調研問卷為基礎,分析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與土地利用特點,研究結果表明:城市郊區農戶偏好糧食作物種植活動和兼業型生計策略,農地利用強度較低,農地轉出可能性高;近郊農戶的農地利用強度因農地經營規模的不同而不同,選擇經濟作物和多樣化農業生計策略可能性較大,轉入農地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遠郊農戶多采取滯留農業或脫離農業生計策略,農地利用情況因生計策略的不同而不同。
關鍵詞 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土地利用
中圖分類號 S-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9)09-0270-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9.075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 show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exists som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e farmer's level and regional concep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farmers'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An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16 households in 19 villages of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land use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rmers in urban suburbs prefer grain crops planting activities and facultative type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is low, the pos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is higher;the intensity of farmland use in the suburbs varies with the scale of farmland management, and farmers are more likely to select crash crops and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reupon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ring to farmland increasing;farmers in the outer suburbs most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staying in or ou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farmland use varies with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Key words Different suburban areas;Farmers;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Land use
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大量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大量農田被撂荒;農戶發生分化,兼業和非農農戶數量增加[1];勞動力結構趨于老齡化和低齡化,“空心村”數量增加[2];同時,由于建設用地占用、農業結構調整、生態退耕和災害毀損等原因,耕地面積減少的速度呈加快趨勢[3]。此外,城鄉資源長期配置不均的狀態也使得農村一直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區域。針對農村地區存在的問題,鄉村振興戰略應運而生。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則詳細規劃了鄉村振興戰略具體的實施內容[4],這是國家在新時期關于“三農”問題的全新部署,強調農村現代化發展。
農戶作為農村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主體與最基本的決策單位,其所采取的生計策略直接影響土地利用的數量、效益和結構[5]。同時,地貌類型、氣候、地理環境、區位(尤其是距離大都市遠近)、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或直接或間接通過土地利用變化影響農戶生計策略選擇,而農戶生計轉變又會通過農地流轉、勞動力轉移等促使土地利用變化[6-10]。由此,筆者從農戶層面及區域理念入手,建立農戶生計多樣化與土地利用理論框架,分析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和土地利用特點及相互關系,力圖為其他地區實現農戶生計與土地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
1 理論框架
根據可持續生計框架[11]可知,處于脆弱性背景下的農戶憑借自身生計資本,選擇生計活動,制定生計策略,最終形成某種生計成果,影響農戶的生計資本,從而進入下一個“生計資本→生計策略→生計成果”循環。生計策略由不同生計活動組成,可分為滯留農業、農業與非農兼顧和脫離農業3種形式,生計多樣化表現為農戶選擇生計活動的多少,有多種表現形式。生計策略傾向性質表現,生計多樣化傾向數量表現,因而,分析生計策略和生計多樣化情況,可以全面地了解農戶生計狀況。所處城郊帶不同(以城區建成區為中心劃分環帶范圍,范圍取值為1~5 km,5~50 km,50 km以外,城郊帶依次為城市郊區、近郊和遠郊),農戶生計資本及所感知的外界環境也會有所不同,進而造成生計策略、生計多樣化及土地利用的區域差異性,同時,因內生資源稟賦、應對風險能力等方面的不同,農戶分化,筆者根據農戶家庭成員特征及收入結構將農戶分為純農戶、農為主型兼業戶、均衡型兼業戶、非農為主型兼業戶和非農戶5類,不同類型農戶的生計狀況及土地利用行為不同,因而,不同城郊帶不同類型農戶的生計多樣化和土地利用均會呈現差異性(圖1)。
農戶是農村土地的實際管理者,與土地緊密相連,其生計選擇會對土地利用產生或正或負的影響,例如農戶選擇脫離農業生計策略,可能會撂荒土地或轉出土地,選擇作物多樣化種植,可能會增加農地利用強度,也可能轉入農地進行規模生產,并帶來土地利用類型變化。不同城郊帶農戶,因就業機會、地區發展水平等不同,會選擇不同的生計策略,并呈現不同的生計多樣化水平,也因此,其土地利用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同時,因地區發展需要,建設基礎設施、發展工業產業等使得部分農村土地利用類型改變,進而影響農戶生計選擇,例如因轉出農地渠道和非農就業機會增多等原因,農戶偏好兼業型和非農型生計策略,因土地規模生產效益增加,偏好農業規模生產等等。
2 實證分析
基于理論框架,利用河北省農戶調研數據,分析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與土地利用規律。調研數據共416份農戶問卷,問卷有效率97.84%,共涉及石家莊市和保定市19個村莊。研究區域可分為城市郊區(石家莊市)、石家莊近郊、保定近郊、石家莊遠郊和保定遠郊5個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指數可通過計算農戶家庭生計活動數目的總和得到。
2.1 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規律分析
2.1.1 生計多樣化指數。
除石家莊遠郊農戶的生計多樣化指數集中在2外(圖2),余下4個城郊帶的均集中在1~4;城市郊區和石家莊遠郊農戶最多選擇2種農業生計活動,其他城郊帶最多選擇3種;城市郊區和石家莊遠郊農戶最多選擇3種非農生計活動,其他城郊帶最多選擇2種。
分析數據知,農業生計活動中,各城郊帶農戶選擇糧食作物種植活動的比例均較高,城市郊區的最高,遠郊次之,不同城郊帶其他農業活動的選擇偏好存在差異;非農生計活動中,各城郊帶農戶選擇非農打工的比例均較高,遠郊的最高;兼業活動中,城市郊區農戶的選擇比例高于近郊,高于遠郊,且不同城郊帶的兼業活動中的非農活動多為非農打工。此外,非農活動偏好和就業地方面,城市郊區農戶偏好非農打工,就業地離家近;近郊農戶偏好非農打工和個體經營,就業地主要是本村和本市城區;遠郊農戶偏好非農打工,多為外出打工,就業地涉及本市、鄰近省市(如北京等)和不固定的地區。在此基礎上,分析各城郊帶不同類型農戶的生計狀況知,各城郊帶不同類型農戶的群體占比、生計多樣化水平和生計活動選擇均存在差異,兼業型農戶的生計多樣化水平均高于純農戶和非農戶,各城郊帶不同類型農戶占比呈現顯著區域差異。
2.1.2 生計策略。
基于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指數分析,該部分從兩項和三項生計活動(即生計多樣化指數2和3)兩個方面分析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活動組合即生計策略的規律。城市郊區農戶,共18種生計策略;兩項生計組合中,兼業型生計策略占比最高;三項組合均為兼業型生計策略。近郊農戶共69種生計策略;石家莊近郊,兩項中,兼業型生計策略占比最高,三項組合均為兼業型生計策略;保定近郊,三項中,兼業型生計策略占比最高。遠郊農戶共34種生計策略;石家莊和保定遠郊農戶的兩項生計組合中,一項生計活動為糧食作物種植的農戶比例均超過90%;保定遠郊農戶的三項生計組合中,兼業型生計策略占比最高。此外,不同城郊帶兼業型生計策略中,非農為主型兼業戶占比均最高。
綜上,不同城郊帶農戶的生計活動選擇、生計多樣化指數及生計策略和各城郊帶農戶類型占比均呈現區域差異性。離城區建成區近的農戶生計多樣化水平較高,傾向于選擇兼業或非農生計策略,生計策略較多樣,各城郊帶的兼業型生計策略占比最高。
2.2 不同城郊帶農戶土地利用規律分析
2.2.1 農地利用強度。
農地利用規模指農戶經營農地的面積。城市郊區的農地利用規模普遍較小,超過95%的農戶經營(0,0.33] hm2規模的農地;近郊的農地經營面積多低于0.67 hm2;遠郊經營(0.33,0.67] hm2規模農地的比例最高,(0,0.33] hm2次之;相較近郊,城市郊區和遠郊純農戶或兼業戶的農地利用規模較小。農地復種指數為一年內農戶家庭作物種植總面積與農地經營面積的比值。城市郊區和遠郊的農地復種指數集中在(1.5,2]內,農戶比例均超過80%;近郊集中在1和(1.5,2]范圍內,其中,石家莊近郊集中在(1.5,2]范圍內(65.52%),保定近郊主要集中在1(62.50%);相較近郊,城市郊區和遠郊兼業戶的農地復種指數高。農地物質投入為農戶對農地的物質總投入。城市郊區在10 000元/hm2以下各農地物質投入范圍內的農戶比例較均衡;近郊農地物質投入的農戶比例呈“兩頭高,中間低”的特點;遠郊的農地物質投入集中在10 000元/hm2以下;相較城市郊區,近郊和遠郊純農戶和兼業戶的農地物質投入高,其中,純農戶的更高些。
2.2.2 農地流轉。
不同城郊帶農地流轉率(農地流轉農戶數與總被調農戶數的比值)表現為近郊>遠郊>城市郊區,農地流轉率均不高;農地轉出率表現為遠郊>城市郊區>近郊;農地轉入率表現為近郊>遠郊>城市郊區;石家莊近郊農地轉出率和轉入率均高于保定近郊,石家莊遠郊的均高于保定遠郊;城市郊區中,非農為主型兼業戶的農地轉出率較高,近郊中,各類型農戶的農地轉入率高于轉出率,遠郊各類農戶的農地流轉率均不高。此外,城市郊區中,農地轉出的用途多為非農性,如基礎設施建設、工業開發,租期較長;近郊中,農地流轉的用途多為種植業,經濟作物種植比重較高,租金不等,租期一般多于5年;遠郊中,農地流轉的用途也多為種植業活動,轉出的農地多為規模生產,租期較長。
2.2.3 農地利用類型。
分析農地作物播面比例(一年內農戶家庭某種作物播面占總播面的比重),來探究不同城郊帶農地利用類型差異,包括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果樹或林業播面比例。城市郊區農地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為100%;石家莊近郊農地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最高(76.74%),經濟作物次之(20.95%),保定近郊糧食作物和果樹或林業播面比例較高(57.37%、37.62%);石家莊和保定遠郊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均超過80%;石家莊近郊純農戶和兼業戶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均最高,且隨著農戶非農程度加深,其比例提高,保定近郊均衡型和非農為主型兼業戶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最高(67.87%、84.70%),純農戶和農為主型兼業戶的果樹或林業播面比例最高(67.81%、58.73%),其次,為糧食作物(28.57%、34.75%),遠郊均衡型和非農為主型兼業戶的糧食作物播面比例均超過90%。
綜上,不同城郊帶農戶的土地利用表現為,近郊和遠郊農戶小規模經營的農地的利用強度低,大規模經營的農地的利用強度高,城市郊區的農地利用強度處于中等水平;隨著農戶非農程度加深,農地利用強度呈降低趨勢,不同城郊帶的情況有差異;不同城郊帶農地作物播面比例因農戶非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3 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城郊帶農戶的生計多樣化和土地利用呈現出區域差異,其差異特點和相互關系表現為:
(1)距離城區建成區近的農戶,一方面,有更多就地從事非農工作的機會,其采取兼業型生計策略的機會成本較其他地區農戶有所降低,而選擇兼業型生計策略也可能促使其更加集約地利用農地資源,因為距離城市近,巨大的農業消費市場、便利的交通道路條件,會使得農戶傾向種植經濟作物,增加農地利用強度,獲得農業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城市工業的擴張,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占用大量農村土地,農地流轉率提高,由此,農戶家庭財產性收入增加,農業生產活動收入減少,進而,使得農戶更多地從事非農生產活動。
(2)距離城市遠的農戶,就地就業機會較少,為獲得更多的收入,農戶會選擇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往往是農村年輕勞動力,農戶家庭成員中,留守在農村的往往是勞動能力低的婦女、老人和孩子,因而農戶家庭生計往往呈現出單一性或以非農為主的形式。也因此,農戶家庭的農地利用集約度降低,作物種植單一,同時,可能因地區發展水平不高,其農地流轉率較低。
不同城郊帶農戶生計多樣化和土地利用呈現的特點及相互關系表明,鄉村振興策略提出的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深化農村土地制定改革、實現鄉村產業全面振興等等將有利于保障農戶農地產權的穩定性,促進多樣性的規模經營,并進一步降低農戶生計風險性,促進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因此,各地區應根據規劃制定并實施符合地區發展的政策措施,因地制宜,建設基礎實施,扶持特色產業發展,促進農戶生計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續發展,并最終,促進農村地區產業發展、糧食安全和生態環境的改善。
參考文獻
[1] 郝海廣,李秀彬,辛良杰,等.農戶兼業行為及其原因探析[J].農業經濟技術,2010(3):14-21.
[2] 劉新靜.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傳統農村的轉型及新農村的轉型及新農村建設研究[J].學術界,2013(3):22-30.
[3] 陳瑜琦,李秀彬.1980年以來中國耕地利用集約度的結構特征[J].地理學報,2009,64(4):469-478.
[4] 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A].2018-9-26.
[5] BIRCHTHOMSEN T,FREDERIKSEN P,SANO H O.A livelihood perspective 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emiarid Tanzania[J].Economic geography,2001,77(1):41-66.
[6] DIB J B,ALAMSYAH Z,QAIM M.Landuse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Indonesia[J].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18,94:55-66.
[7] 李贊紅,閻建忠,花曉波,等.不同類型農戶撂荒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重慶市12個典型村為例[J].地理研究,2014,33(4):721-734.
[8]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區農戶生計多樣化及對土地利用的影響:以北京市大興區為例[J].地理研究,2012,31(6):1039-1049.
[9] 王成超,楊玉盛.農戶生計非農化對耕地流轉的影響:以福建省長汀縣為例[J].地理科學,2011,31(11):1363-1367.
[10] 馬志雄,張銀銀,丁士軍.失地農戶生計策略多樣化研究[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3):54-62.
[11] DFID.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