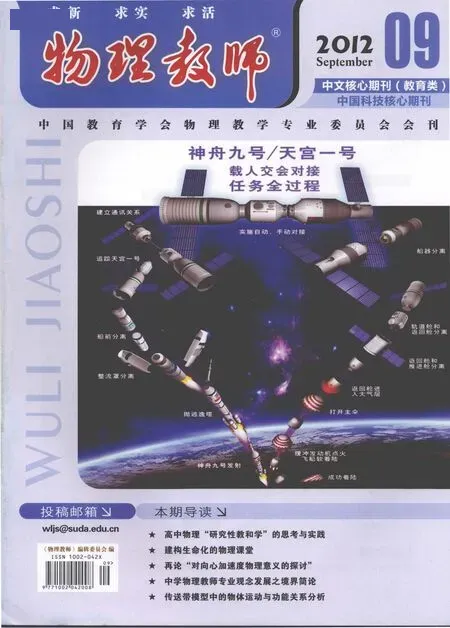“磁感應強度”的說課設計
劉立軍
(浙江省溫州中學,浙江 溫州 325014)
筆者就人教版選修3-1教材第3章第2節“磁感應強度”,在2011年華東六省一市物理年會上進行了公開說課.現將筆者在說課中的做法整理如下,供同仁們參考.
1 物理化與生活化并重
高中物理新課程目標強調,要把物理的教學內容和學生的生活實際聯系起來.這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強化學生的實踐意識,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把物理知識與應用技術和人文科學結合起來.這能使學生獲得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有助于學生形成科學的價值觀,增強社會責任感.教師應精準地把握所授教學內容中的物理知識點和能力點,能對教學重點和難點進行了層層剖析的展開和步步深入的挖掘,而且能利用學生身邊熟悉的生產、生活情境,設置問題.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學生探究學習的興趣和熱情,并且有助于加深學生對知識理解的生動性和深刻性,真正體現“從生活走向物理,從物理走向社會”的新課程理念.
筆者在說課中利用視頻向學生展示:電磁鐵吸引鐵塊;候鳥的遷徙;鯨魚的巡游和磁懸浮的飛馳4段情景.這些生活中的事例都說明磁場具有強弱和方向.這樣情景生活化地引入新課,可以使學生一下子就從物理走進了生活,又一下子從生活走進了問題.在新課的結尾部分利用課后的“科學漫步”向學生介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近150年來,地球的磁感應強度急劇減弱了10%~15%,這就可能是地球磁場發生大翻轉——南、北極互換的前兆.科學家指出,地核周圍的鐵流體好像一部“發動機”,不停地將巨大的機械能轉化成電磁能,從而形成地球磁場的改變.科學家們通過對海底熔巖的研究發現,地球的磁場曾經發生過多次翻轉.研究表明,地球磁場平均每50萬年翻轉一次,而最近一次的翻轉發生在78萬年前.然后向學生提出3個問題:(1)地球磁感應強度的減弱會不會對人類的生存造成危害?(2)會不會對地球生物圈造成重大影響?(3)這樣減弱過程會不會發生逆轉?這樣留白式的結尾既可以呼應本節教學的內容,又可以使物理知識得以延伸,學生對物理與生活的探索得到延續.
2 探究性與創新性共存
傳統的物理課堂一向重知識結論的傳授,輕物理思維過程的演繹,可謂是“知識型課堂”.而在高中物理新課程教學過程中,科學探究不但是重要的學習方法,也是重要的學習內容,可謂是“探究型課堂”.探究課堂不再是教師表演的舞臺,不再是學生進行訓練的場所,而是師生交往、互動的舞臺,引導學生發展的場所,是教師教育智慧充分展示的舞臺,也是學生自我探究、獲取、知識生成的場所.
新課程理念下的探究是真正意義的探究,要讓學生真正的參與,真正的探索.這就要求教師在使用和處理教材時,要變“教教材”為“用教材教”,要對探究方式加以改進革新,對探究實驗進行自主創新,將演示實驗探究和自主實驗探究巧妙地結合,讓學生體驗科學探究的樂趣,學到科學探究的方法,領悟科學探究的精髓.
筆者在說課中設計了兩個具有創新性的探究實驗:
(1)對教材中關于定性地探究磁場對電流作用力的大小與電流大小和導線處于磁場中長度的關系的實驗加以了改進,從而實現對磁場力粗略的定量探究.
①將教材中的3塊蹄形磁鐵換成了5塊相同的蹄形磁鐵(如圖1所示),并且將懸掛其中的導線引出6根接線.這樣通過改換接線的位置和改變磁鐵的塊數可以使導線處于磁場中的長度被改變5次.

圖1
②在導線的一側添加1根細鐵絲作為指針(如圖2所示),通過下面放置的刻度尺可以讀出導線水平的偏移量.
③將懸線的長度加長到約為60cm,使導線擺動時其偏角極小.從而可以近似地認為磁場對電流的作用大小正比于導線擺動時的水平偏移量.
(2)筆者又設計了一個DIS實驗可以較準確地定量地探究磁場對電流作用力的大小與電流大小和導線處于磁場長度的關系.
自制一個200匝的方形線圈并且引出5個抽頭(如圖3所示),改換兩個抽頭的接線可以使線圈分別為200匝、150匝、100匝和50匝.這樣可以使線圈處于磁場當中的長度分別約為12m、9m、6m和3m.

圖2
然后通過力傳感器、電流傳感器和數據采集器,將磁場力的大小、電流的大小和導線處于磁場中的長度錄入電腦,再通過電腦的專業系統軟件處理,實現了當磁場與電流垂直的情況下,影響磁場力的大小與哪些因素較準確定量的探究(如圖4所示).

圖3

圖4
教育的改革就是教育觀念的變革,也是教學技能的變革.這就要求教師要具備創新的意識和能力,要求教師要具備理論聯系實際意識和實際探究理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