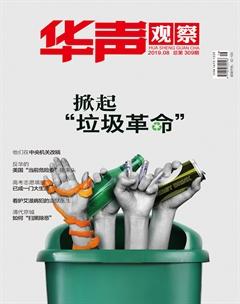當代人寫文言文:一場尷尬的行為藝術
曹徙南
還有什么事,是比用文言文講漫威故事更讓人尷尬的?
6月初,遼寧沈陽的一位中學語文教師寫了一篇《鋼鐵俠傳》,寥寥幾百字寫完了鋼鐵俠的一生。這種中國文言文和好萊塢超級英雄故事的結合,迅速攀上當天微博熱搜。
“托尼早孤,銳志好學。其父霍華德在時,嘗以其寄庠序,尼不知其父有志于國,謂其漠己……誓日,孰弒吾親,必手刃之。”
“銳志好學”化用《漢書》中的“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銳志”一詞本就作為動詞,來表示志向堅決,加上一個“好”字,似乎重復了。“漠”雖然有冷淡、冷漠的意思,但從古到今都沒有及物動詞的用法,“漠己”這種強行縮句,讀來也有些別扭。至于最后的這個“弒”,只能用在僭越倫理、下層殺戮上層的情況,用在這里也不太合適。
近年來,從辭職信、請假條到情書,每一次文言文創作似乎總能成為社會熱點。其實,無論從立意還是文采來說,在當代被追捧的文言文創作都非常平庸,但偏偏被標榜為才華與文采的象征。在復古的光暈下,這些作品的實際水平基本停留在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廉價模仿。
死掉的古文,活著的行為藝術
1926年,魯迅在《古書與白話》中直言:“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但我們對于魯迅先生的呼吁,向來都是選擇性的。這不,最近幾年寫寫半生不熟的詩詞古文。儼然成了附庸風雅、擁抱傳統文化的捷徑。
文字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套符號,它還牽連著一整套思維方式和時代精神。文言文和現代白話文盡管使用著共同的文字,但實際上已經是迥異的文字體系。作為一個接近封閉的系統,文言文已經停止更新,而無法與當代生活真正融合。
不信來看看網絡熱詞的文言文版本:“土豪我們做朋友吧”成了“富賈,可為吾友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了“天高地闊,欲望觀之”,“我讀書少你不要騙我”成了“君莫欺我不識字,人間安得有此事”。
無非是強行塞了一些“之乎者也”,其不倫不類程度,只有職場上流行的中文夾英文能夠比擬。
無法融入現代生活的文言文,很難講述高鐵、移動支付、互聯網的生活,只好重復著駕長車、金龜換酒、鴻雁傳書的古典幻夢。漢服黨之所以遭人詬病,是因為他們鼻梁上的黑框眼鏡和衣擺下若隱若現的AJ籃球鞋。古風歌曲之所以被群嘲,是因為它們用古典元素妝點爛俗的言情故事。
白話文運動之后的文言文風潮。本質上也只是一次逆歷史而動的大型懷舊。
文言文熱:一場“葉公好古”
2001年,南京十三中高三學生蔣昕捷以一篇題為《赤兔之死》的文言文作文轟動一時。這是高考歷史上第一篇滿分作文,蔣昕捷因此被稱為“高考作文滿分第一人”。
“赤兔馬絕食數日,不久將亡。孫權大驚,急訪江東名士伯喜。此人乃伯樂之后,人言其精通馬語。”這篇《赤兔之死》讀來讀去,怎么看都是一股子《三國演義》的味道,可脫胎于民間話本的《三國演義》,算得上文言文嗎?如果將其改成“赤兔不食數日。將亡。權驚,急訪江東名士伯喜。喜,伯樂之后也,有言其通馬語”,或許才更多了點文言文的精煉味道。
比《三國演義》成書晚了幾百年的《聊齋志異》,倒是實實在在的文言文筆記小說。在那篇著名的《狼》里,看看蒲松齡是怎樣用文言文寫動物的: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歘一狼來,瞰擔上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
回頭再看《赤兔之死》中煞有介事的“文言文”,嚴格來看,有明顯的文白混雜的拼湊痕跡,不過這并不妨礙之后考生的競相模仿。在高考作文這個舞臺上,也的確有人靠著豪賭拿到了大學的入場券。
2009年高考,武漢考生周海洋用51行102句每句七言的“古體長詩”《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贏得“國學奇才”的稱號,最后被三峽大學“破格錄取”。其后。四川考生黃蛉,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等古文寫了一篇高考作文,也被輿論熱捧,最終被四川大學“破格錄取”。
然而這些投機者最后都被證明并無真才實學,周海洋三年掛了四門課,連“古代漢語”都考不及格。而四川大學專門為其配置。一對一培養黃蛉的指導教師、古文字專家,兩年后向學校提交辭呈,原因是黃蛉“學風浮躁,不愿再教”。
推崇、鼓吹文言復興的人往往強調文言文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其背后是追認、接續歷史的焦慮和對于古代生活凌空蹈虛的美好幻想。
歷史自然有其溫情脈脈的一面,但那些風流氣象與我們今日的想象,總歸相去甚遠。無論是漢服黨還是古風圈,都市青年極盡妄圖復現古代社會的玫瑰色,塑造出來的終究只是旅游鞋配漢服的四不像。
古人到底怎么說話
當然,并不是說我們要完全舍棄文言文,它永遠是中國人與歷史溝通的符碼。我們要警惕的是厚古薄今、濫用文言文甚至扭曲文言文。
精通古漢語的語言學家王力,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批評過青年人間流行的“非驢非馬”的文言文寫作:學習古文。主要是學它的文氣,而不是學它的詞藻。如果一味堆砌詞藻,就是文格卑下。濫用文言文不過是故作搖曳的附庸風雅。
話說回來,越接近現代的古人,對于文言文的使用頻率也許遠沒有我們想的那么高。
史書上,明神宗萬歷皇帝曾對太子說過這么一番話: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的純誠、孝友、好善的心,我平日盡知……我思念你恐有驚懼動心,我著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時忿怒、動火,難以盡言。
沒有“之乎者也”,連“朕”都沒有,幾百年前的帝王之家,皇帝訓斥太子的話,聽起來和今天你爸訓你也沒有太大分別。
時間再往后推一個朝代,在各種穿越小說、清宮電視劇里,四爺雍正皇帝率領后宮嬪妃,恨不得張口閉口念詩詞,下筆盡是文言文,文縐縐得很。
可歷史上的雍正帝是怎么給田文鏡批奏折的呢?“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這樣看來。我們今天束手束腳地用所謂的“文言文”寫漫威故事,用所謂的“詩經體”湊韻腳,然后對著四不像的成品拼命鼓掌,是不是也太矯情了些?
摘編自搜狐網

清末詩人黃遵憲曾嘗試將電報、火車等新鮮事物寫入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