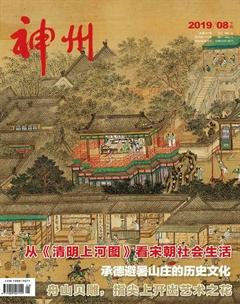簡述戲曲演員舞臺上動作與表情的有機結合
摘要:戲劇藝術是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設計、舞臺美術設計與觀眾集體創作,以演員的表演為中心的綜合藝術。演員表演的基本手段不是別的,是動作、是表情,其本性在于它本身的直觀性與非直觀性的揭示性的統一。
關鍵詞:舞臺;戲曲表演;直觀性;程式舞臺動作;眼神
戲曲舞臺表演的直觀性,通俗地講,就是動作直接訴諸于觀眾視、聽的特征。非直觀的揭示性,就是作用于觀眾視聽的動作與表情,必然地反映出人物的心理內容。直觀性與非直觀的揭示性,兩者的統一構成完整的舞臺動作與表情的內涵,舞臺動作與表情是經過藝術加工的,是藝術家創造的結果。
戲曲表演,是以表演為中心的綜合藝術,也是以舞臺動作與表情為手段的戲劇形式。現有人認為,戲曲舞臺動作中包含著歌舞化的意思,戲曲的程式是歌舞化動作這種戲劇“語言”的“語法”,戲曲的舞臺動作與表情必須運用這樣的語法,才能成章,否則戲曲則無“戲曲味兒”,也就不能稱其為戲曲。由此說戲曲歌舞化的舞臺 動作與表情也是具有程式性質的,程式性舞臺動作也就是程式性歌舞化舞臺動作。
舞臺動作與表情都是通過“怎么做”來體現“做什么”和“為什么”的,“怎么做”是直觀化內容的具體形態,包含著角色的思想感情。戲曲舞臺動作與表情不僅包含著角色的思想感情,甚至是角色思想感情的直觀形式,因此是有意味的形式,這種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個演員長期審美沉淀的成果,在審美的過程中,從程式性舞臺動作與表情中可直接感受角色的思想感情,從而產生共鳴。獲得感情并不是一件簡單伸手而得的事情,它還需要使舞臺動作與表情和相之規定的情境相結合,才可貼近完美。
把戲曲程式性舞臺動作和表情看作是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假設這種程式在形成的時候,已經自然的與一種內在精神凝結在一起,比如:青衣行當穩重、端莊;花臉則粗獷、豪放,“亂錘”慌亂不定;“慢板”中蘊涵濃情,跑圓場緊迫,耍水袖激情,可見程式舞臺動作已經不是簡單的形式,而是內容本身。這種內容本身指的是人的內在情意,情意熔鑄程式之中猶如水乳交融。程式舞臺動用與表情伴隨著戲曲藝術的發展積淀而成,作為戲曲表現生活的形式,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作為戲曲塑造形象的手段,卻不斷顯現著獨特的戲曲藝術風格。
程式舞臺動作與表情,一經形成,亦可作為創造角色的手段,在運用程式手段進行角色創造的時候,還需進行二次體驗,從老師那里學來的程式需要體驗,在舞臺上演出需要體驗,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新的體驗,創造新角色更需要體驗,否則,這種程式便是死的,不可能產生意味。
程式舞臺動作在規定的情境中,除用姿式刻畫人物形象,體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神采外,面部表情既“眼神”的作用亦極重要。正如人們常說“一身之戲在于臉,一臉之戲在于眼”,眼晴是心靈的窗戶,要想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到演員身上,眼晴傳情傳神至關重要。當一個演員表演和身段動作及眼神運用非常自如,觀眾會情不自禁地夸贊說:“演的真好,瞧那雙眼睛像會說話似的”,要不戲劇的行話咋叫做“手眼神情”呢。
眼神表情的運用具體地說有正眼、斜眼、喜眼、怒眼、呆眼、病眼、冷眼、睡眼、賊眼、媚眼、色眼、死眼等。正眼一般用于演員表演白天和正視對方的一舉一動,而斜眼在舞臺表演中用于互相猜疑及傾聽別的談話和其它聲音等,如淮北梆子戲《秦香蓮后傳》一劇第五場中,春哥為了躲避紫蘭,故意謊稱自己身受風寒,讓其出去取衣服,謊計得逞后,翻窗逃走之前,附耳斜眼靜聽外面有否有其它聲響。還如《三岔口》一劇,雙方在摸黑搏斗中,彼此看不見對方,用耳聽時,就要用斜眼,這一切都要靠演員視而不見的眼神引導摸黑的手勢,在明亮的燈光下,構成黑夜搏斗的戲劇效果。喜眼用的非常廣泛,無論舞臺還是生活當中,遇到令人高興的人和事,都會用喜眼表現出來。而媚眼、色眼多用調情的表演之中,如《清風亭》中張元秀認子一場,當聽地保講張繼寶得中狀元出任縣令時,興高眼笑;當繼寶養兒不愿相認索要證據時,冷眼橫對,掏取血書;當繼寶養兒拒絕相認,轟攆張元秀下去時,張元秀無奈用“病眼”對恃蒼天;當地保告知張元秀養兒繼寶喪盡天良“賞賜”他們二老二百銅錢時,張元秀用惱怒的眼神責咒著張繼寶;當喪盡天理的 張繼寶得知養父母撞柱氣絕當場身亡時,突遭天雷驚劈,張繼寶頓用“呆眼”“死眼”償食著蒼天鬼魂對他的報應。
眼神的訓練主要依靠眼珠的運轉功,其表現如左右閃動、劃圈轉動、遠視、近瞧等。為把眼神練的靈活多變,前輩藝人們用注視晃動點燃的香,遠視飛鴿,近視魚等方法來苦練眼神,增強在舞臺上表演的效果。為了繼承發揚民族戲曲藝術,我們后生一輩應努力苦練基本功,敬業尊藝,為塑造更好的藝術形象增光添彩。
作者簡介:張馨云(1987.02-)女,安徽亳州人,亳州市演藝有限公司演員,主攻方向:閨門旦、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