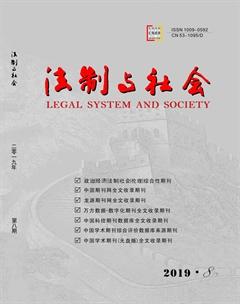穆勒五法在案件分析中的應用
摘 要 在司法實踐中,充滿了各種因果關系,除了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外,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以及法律的解釋與適用,都有著各自的原因,正是因為因果關系的錯綜復雜,才給案件認定帶來了更多的爭議。而邏輯學家約翰·穆勒早在1843年即提出了探求因果關系的五種方法,世稱穆勒五法。本文旨在研究穆勒五法如何在案件分析中發揮其探求因果關系的作用,以期對司法實踐及理論研究進行指導。
關鍵詞 穆勒五法 歸納推理 案件分析
作者簡介:孫濤,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
中圖分類號:D9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286
一、穆勒五法之契合法、差異法及并用法
英國邏輯學家約翰·穆勒在其著作《邏輯學體系》中總結出五種實驗中進行歸納推理的方法,用以探究因果關系,世稱穆勒五法。穆勒五法包括契合法、差異法、契合差異并用法、共變法和剩余法。
其中契合法是指考察兩個出現研究現象的不同研究對象,如果兩個對象除了一個條件相同外其他條件均不相同,那么這個條件就是出現該現象的原因。例如在一個餐館里發生了食物中毒,兩個中毒的人吃的東西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兩個人都吃了a食物,那么就是a導致的中毒。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B∧C→a;A∧D∧E→a;∴A→a。
差異法則是比較研究現象出現的研究對象及不出現的研究對象,如果兩個對象只有一個條件不同,其他條件都相同,那么這個條件就是引起研究現象的原因。例如上述飯館食物中毒事件,如果中毒的甲和沒中毒的乙吃的東西完全相同,區別只是甲吃了a,而乙沒吃a,那么就是a導致的中毒。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B∧C→a;D∧B∧C→~a;∴A→a。
需要注意的是,穆勒五法從本質上來說屬于歸納推理,而歸納推理得出的結論是或然性的,無法得出必然結論,影響歸納推理準確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研究對象的數量。因此為了得出準確率更高的結論,我們就需要使用契合差異并用法(簡稱并用法)。與契合法和差異法研究兩個特殊的對象即可得出結論不同,并用法則需要研究兩組對象。首先需要將對象分組,將所有研究現象出現的對象分為正事例組,而不出現的對象分入負事例組,接下來分別對兩組對象進行觀察,如果正事例組的對象只有一種條件在各個對象中均出現,而負事例組的對象均沒有出現該條件,那么該條件就是引起研究現象的原因。例如上述飯館中毒事件,所有中毒的人吃的東西都不相同,只有a食物所有中毒的人都吃了,而所有沒中毒的人都沒有吃a,那么a就是導致中毒的原因。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B∧C→a;A∧D∧E→a;A∧F∧G→a;……;~A∧B∧C→a;~A∧D∧E→a;~A∧F∧G→a;∴A→a。
不同于以上三種定性的推理,共變法是涉及定量的推理,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某一條件變化的同時研究現象也發生變化,那么該條件就是產生研究現象的原因。例如同等條件下的相同氣體,當溫度升高時氣體體積增大,溫度降低時氣體體積縮小,因此溫度變化就是氣體體積變化的原因。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1∧B∧C→a1;A2∧B∧C→a2;A3∧B∧C→a3;∴A→a。
以上四種推理都是針對簡單因果關系而言的,而剩余法則是針對復雜因果關系的推理,是指當已知復雜條件引起復雜現象時,將其中確定具有因果關系的條件與現象去掉,剩余的條件與現象間仍有因果關系。例如在天文學研究中,發現天王星軌道有四個地方發生了偏斜,其中三個偏斜點都是由于已知行星引力造成,那么第四個偏斜點也應當是受了某個未知行星的吸引造成,進而由此發現了海王星。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B∧C→a∧b∧c;B→b;C→c;∴A→a。
二、契合法、差異法及并用法在案件分析中的應用
在法律適用方面,對于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區分標準并非始終非常明確,有個別罪名的辨析存在著較大爭議,而通過契合法、差異法、并用法可以將具有爭議的情形簡化為不具爭議的情形,進而推導出爭議情形的結論。
例如在刑法理論界,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之間的區分標準始終是“兩個當場”——即當場實施暴力或以當場可實施的暴力相威脅與當場取得財物,只要有一個當場不符合就不能構成搶劫罪而應構成敲詐勒索罪。但是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區分搶劫與敲詐勒索的標準,例如有人認為搶劫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因此不應有任何索要財物的理由,而只要索要財物有一定的理由,就構成敲詐勒索罪;還有人認為,搶劫罪相比于敲詐勒索罪來說屬于嚴重暴力犯罪,因此當暴力程度較輕的情況下,不應構成搶劫罪,而應構成敲詐勒索罪。對這兩個罪名區分標準的探究就可以使用契合法與差異法。首先明確我們需要探究的因果關系是什么,在這里就是“兩個當場”、索財理由和暴力程度哪個才是決定搶劫與敲詐勒索的原因。然后需要構建容易觀察的研究對象,也就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案件。在使用契合法時需要構建一個符合“兩個當場”同時沒有索財理由、暴力程度重的案件,以及一個符合“兩個當場”卻有索財理由、暴力程度輕的案件。經構建之后我們不難發現,第一個案件毫無疑問的構成搶劫罪,而第二個案件可能就沒有這么直觀了,這時我們只需要將第二個案件變為一個生效判例即可。經不完全統計,裁判文書網收錄的有索財理由的搶劫案件一審判決約八千余件,其中不乏暴力情節輕微的。此時我們發現,當“兩個當場”符合時無論有無索財理由、暴力程度輕重,均構成搶劫罪,因此“兩個當場”才是構成搶劫罪的原因,而不是有無索財理由、暴力程度輕重。我們以A代表“兩個當場”,以B代表沒有索財理由,以C代表暴力程度重,a代表搶劫罪,運用邏輯學公式表示上述推理經過即為:A∧B∧C→a;A∧~B∧~C→a;∴A→a。
而運用差異法時同樣需要構建一個符合“兩個當場”同時沒有索財理由、暴力程度重的案件,同時需要構建一個不符合“兩個當場”卻沒有索財理由、暴力程度重的案件。第一個案件仍然沒有爭議的應當構成搶劫罪,第二個案件我們可以將其極端化,例如甲在街上攔住素不相識的乙,要求乙一年后給其十萬元,否則就在一年后殺死乙。這種極端情況下顯然無法構成搶劫罪,而之所以案件顯得極端就是因為本案極端的不符合“兩個當場”。因此符合“兩個當場”的情況下可以構成搶劫罪,而當不符合“兩個當場”時不管再怎么沒有索財理由、暴力程度再怎么重,也無法構成搶劫罪,由此可見“兩個當場”才是認定搶劫罪的原因。我們仍舊以A代表“兩個當場”,以B代表沒有索財理由,以C代表暴力程度重,a代表搶劫罪,運用邏輯學公式表示上述推理經過即為:A∧B∧C→a;~A∧B∧C→~a;∴A→a。
當然,這種推理并不是必然性推理,需要加大研究對象的數量才能保證推理的準確性,因此就需要大量的判例數據支持,運用契合差異并用法將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判例分為正事例組與負事例組,再分別觀察兩組中“兩個當場”、索財理由、暴力程度三個條件是否出現而進行分析。本文僅進行方法論層面的探討,具體并用法的研究就不再展開了。
三、剩余法在案件分析中的應用
由于法的滯后性和局限性,法律永遠無法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情況一一進行規定,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時常會出現非典型案件,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之間游移不定,而法律規定及理論通說又對此未予涉及,此時就像西方法諺說的“法官不得因法無明文規定拒絕裁判”,作為司法工作者我們必須作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判斷,這就需要我們運用剩余法推理得出結論了。
所謂非典型案件,并不會完全憑空創造出一種犯罪行為,而是在某種典型案件的基礎上發生了一些特殊的變化而來 。因此,對非典型案件進行分析時就可以將非典型案件中的特殊性去掉,變回我們所熟知的傳統案件,將案情與法律結果之間已知的因果關系排除,并借由剩余法判斷非典型案件的特殊性是否足以成為影響案件處理結果的原因。
例如網絡上引起爭論的“二維碼”案,行為人甲將商店的收款二維碼替換為自己的收款二維碼,在商店購物的顧客如果進行掃碼支付就會將款項轉入行為人賬戶。該案件在盜竊罪和詐騙罪中始終爭論不定。而使用差異法的變體即可做出推理。首先將案件還原為我們知曉結果的傳統案件,即行為人甲和顧客合謀,由甲將頭像與昵稱改為與商店相同或近似,顧客向甲付款后向商店出示付款成功頁面,商店以為顧客已付款允許其將商品拿走。此種情形為典型的詐騙罪。而該詐騙案與本案唯一區別在于行為人與顧客合謀,本案中缺少了合謀,顧客也是同樣受到了欺騙,而合謀還是欺騙僅影響顧客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對行為人甲的定罪并無影響。因此,二維碼案仍應定性為詐騙罪。我以A代表行為人偷換二維碼的行為,以B代表顧客的合謀,以a代表構成詐騙罪,以b代表應追究顧客的刑事責任,則該推理過程以邏輯公式表示如下:A∧B→a∧b;B→b;∴A→a。
由此可見,穆勒五法在案件分析中可以起到指導思維方向、發散思維廣度、將思維過程清晰化、程序化的作用,但需要一再提醒的是,穆勒五法的本質是歸納推理,歸納推理無法得出必然性結論,因此通過穆勒五法推理出的結論是需要大量數據及研究作為依據的,不可對其推理結果過于輕信,需要進行比對及驗證,更不能以此代替法律規定和理論研究。而穆勒五法更多是為我們分析論證提供一種思路以及一種思維方式。
注釋:
本篇由于旨在研究在案件分析中的應用,主要研究契合法、差異法、并用法和剩余法,共變法主要應用于定量研究,對于案件分析這類定性研究應用空間不大,因此本文對共變法僅做介紹不做過多討論。
例如盜竊網絡游戲中虛擬貨幣的行為產生之初,對于案件定性確實引發了廣泛爭議,但該行為無外乎在傳統盜竊行為的基礎上將現實財物轉換為虛擬財物而已,基本行為模式仍是傳統盜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