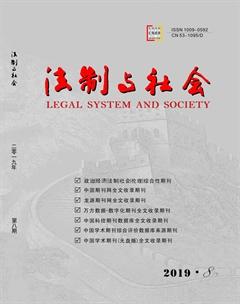挪威的創新系統和創新政策
摘 要 創新政策被認為是決定創新系統發展方向的關鍵。本文試圖引入一個創新政策分析框架來理解挪威過去和現在的創新政策,并對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展望。在闡述挪威創新政策時,通過比較挪威和芬蘭制定創新政策的現實基礎,理解兩國創新政策的差異,并引入SUI和DUI兩種創新模式來分析挪威的創新潛力。最后,總結由挪威創新政策帶來的啟示,為釋放挪威創新的潛力、推動挪威經濟的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詞 創新政策 國家創新體系 創新模式
作者簡介:吳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本科,研究方向:國際貿易。
中圖分類號:D75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354
一、引言
自20世紀60年代末發現海上石油和天然氣以來,挪威的經濟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挪威經濟近海石油和天然氣部門快速發展,并催生油氣和船舶領域特定的產業集群;能源密集型產業獲得大規模投資,一些具有較強信息技術服務能力的公司成為大型工業網絡的重要節點……從上世紀70年代初人均GDP低于經合組織(OECD)平均水平,再到近年來超越OECD國家平均水平甚至北歐五國平均水平,挪威歷經幾十年發展,形成了以石油天然氣、航運、農林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和集群。它主動抓住戰后機遇,通過出口石油積累大量財富,并運用所獲資金在各領域展開投資,利用資金為產業增長和技術升級提供動力,從而建立起一個良性循環,成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
盡管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近年來油價的波動和油氣部門創造財富增速趨緩、經濟增長乏力,使挪威面臨經濟的調整與轉型。創新將在這一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
二、理論框架
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NIS)這一概念來自于Schumpeter和List的學術思想。Schumpeter從創新和新技術概念出發,而List以制度安排和國家為研究基石 。就國家創新體系的內涵而言,目前學者大多采用OECD提出的概念,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是指由參加技術發展和擴散的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組成,為創造、儲蓄和轉讓知識、技能和新產品而相互作用的網絡系統。
創新政策被認為是決定創新系統發展方向和進行制度變革的關鍵 。Cai等學者認為,創新政策是指各級政府的創新政策及其在不同領域出臺的方案,這些政策和方案有意或無意地為本地區創新提供了有利條件 。他提出了一套理解創新政策背后邏輯的框架,在此框架中,他從“專業化與多樣化”和“探索與利用”兩個維度出發,構建四個象限(圖1),并以之代表了四種不同的創新政策邏輯,每一種邏輯都有自己的理論基礎和預期效果(表1):
以創新政策四象限模型為參考,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系列問題:支撐挪威國家和地區創新政策的基本制度邏輯是什么?挪威地區現在的創新情況以及特征有哪些?如何理解挪威政府未來的創新規劃和創新政策?
三、挪威創新政策的制度邏輯和現實基礎
為了更好地理解挪威的創新政策,本文引入芬蘭的創新機制加以對比。芬蘭和挪威同屬北歐國家,根據經合組織2013年報告,挪威已發展成為經合發組織區域內最專門化的經濟體之一,而芬蘭已成為最多樣化的經濟體之一 。這種情況不是隨機出現的,而是經過有意為之的政治進程推動和主動利用新興機遇的結果。
(一)挪威和芬蘭創新政策的制度邏輯
1.挪威的創新政策:歷史與現在
20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挪威在石油領域已經高度專業化。從那時起,國內的創新政策在總體上遵循“專業化開發”邏輯:在創新投入上,以研發投入為例,基礎研究工作仍然集中在國家工業的專門領域;而從創新產出上看,以科學出版物為指標,挪威的科學出版物在與石油和天然氣業務密切相關的學科(比如地球科學和相關學科方面)有很強的優勢 ,這反映了挪威旨在開發現有資源和利用已有知識的政策取向。而進入本世紀,挪威創新政策鼓勵“專業化探索”的趨勢更加明顯,主要表現在對石油工業的大力支持 。
2.芬蘭的創新政策:歷史與現在
芬蘭創新政策和國家創新體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20世紀90年代,芬蘭“專業化探索”邏輯明顯,主要表現在高科技公司的技術創新,如諾基亞領導的ICT集群中創新活動呈指數級增長。雖然芬蘭在研發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其在商業創新方面卻表現的不盡人意,創新成果轉化僅達到OECD國家平均水平。因此目前,芬蘭的創新政策正致力于超越以探索創造為導向的STI主導型政策,向著“多樣化探索”方向發展。
(二)挪威和芬蘭創新政策的現實基礎
可以認為,挪威歷史上奉行“專業化開發政策”,現在有“專業化探索”趨勢;芬蘭在信息技術領域奉行“專業化探索”政策,現在有“多樣化開發”趨勢。那么,如何來理解兩國創新政策的導向基礎?
產業結構是理解兩國創新政策邏輯的重要內容。在OECD最發達的經濟體中,芬蘭和挪威代表著幾乎完全相反的兩個極端。芬蘭向國際市場生產各種制成品,是前十大制成品出口國(OECD, 2013)。其工業結構以中高技術為主,在信息和通訊技術方面具有很強的專門化水平。而挪威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是世界前十大初級產品出口國(OECD, 2013)。其產業結構的特點是高附加值的產業研發強度低 ,尤其是圍繞天然氣、石油和海洋等自然資源進行研發的產業。2018年,挪威近50%的出口為石油相關產品 。與芬蘭更加多樣化的經濟相比,挪威有一種獨特的創新政策邏輯來推動和強化其經濟發展。
從創新模式的角度看,芬蘭和挪威經濟之間的差異說明了STI和DUI創新模式的一些特征 。STI型創新模式的基礎是科學知識,即“知道為什么”(know-why)的顯性知識,這意味著它能夠被寫下來,并被更容易地衡量和理解,最終形成“全球化”知識。而DUI創新模式的基礎是經驗知識,即“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隱性知識,這意味著它不需要陳述就能被理解,“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Fagerberg等學者認為,挪威的創新通常更多地依賴DUI模式,而芬蘭更傾向于STI模式 。
在理解創新政策邏輯以及STI和DUI兩種創新模式后,不難發現,現行偏重STI模式的創新績效評價體系實際上低估了挪威的創新潛力。挪威在人均固定寬帶普及程度、國際合作論文占比、國際共同發明占比等指標上領先芬蘭。在社會制度、立法、政治穩定、公共部門效率、基礎設施和ICT使用方面,挪威經常位列前三,在創造性和人力資本方面,挪威也有著相當高的得分。在數字化時代,挪威具有著多樣化的創新潛力。
四、挪威創新政策未來發展方向
挪威創新政策發展方向是:尋找探索與開發的平衡,科技知識(SUI)與經驗知識(DUI)并重,并在本國具體國情基礎上鼓勵進行多元化創新。
挪威政府制訂了全面的創新政策,試圖通過長期規劃(2015- 2024)引導挪威的創新向多元化開發與探索發展。政府的長期規劃將“海洋”“氣候、環境和綠色能源”以及“技術創新能力”等六個戰略性主題領域列為優先領域;將政策發力領域鎖定在“保障貿易和工業的一般條件”“知識和能力”“研究、開發與商業化”“創業”“電子及實體基礎設施”五個方面。
文末啟示和建議:未來挪威在創新政策上,注重探索與開發的平衡,進行多樣化創新,推動本國優勢產品向著高質量方向發展;在創新績效評價上,注重SUI與DUI兩種模式綜合運用,釋放DUI潛力;在創新體系上,需注重部門之間協調,加強商業部門與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合作;注意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地區和國家之間協調互動,使不同領域的政策產生合力,促進挪威經濟轉型和發展。
注釋:
鄭小平.國家創新體系研究綜述[J].科學管理研究,2006(4):1-5.
Howells, J..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 matter of perspective[J].Research Policy, 2005,34(8):1220-1234.
Cai, Y., Pugh, R., & Liu, C.. A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role of innovation policy i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7,7(4):237-256.
OECD.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3 [M]. Paris: OECD ,2013.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Det norske forsknings- og innovasjonssystemet-statistikk og indikatorer[M]. Oslo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2015.
Wicken,O. Policies for path cre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Norways research-driven strategy for industrialis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9-115.
Forskningsrdet. Instituttsektoren - Forskningsr?dets strategi 2014-2018 [M].Oslo:Forskningsrdet. 2014.
王海燕,梁洪力.挪威創新系統的特征與啟示[J].中國國情國力,2014(5):72-74.
郭愛芳,陳勁.科學學習和經驗學習:概念、特征及理論意義[J].技術經濟,2012,31(6):16-20+49.
趙永強.STI與DUI兩種學習模式的比較分析[J].經貿實踐,2016 (18):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