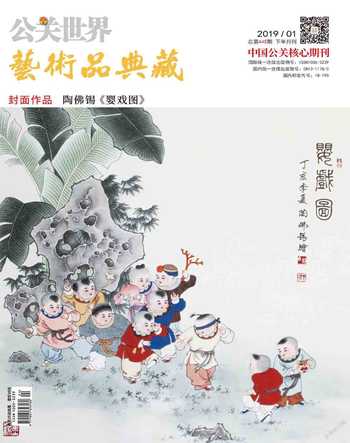再識寫實

時至今日,寫實似乎已漸行漸遠。一方面是因為“進步論”以至繪畫已死的推論,另一方面是當下國際和國內各種藝術潮流的話語建構,寫實主義似乎必須進入狹窄的歷史通道,才更符合文化發展常理。寫實繪畫也已成為過時的“冷飯”,已沒有重炒的必要。即便是當代有弗洛伊德和洛佩茲等人的出現,也被視為寫實繪畫“回光返照”的藝術個案,未能“翻案”。
在首先要接受“繪畫未亡”的前提條件下,寫實需要從普遍審美認識一層層剝開來,才會深入其內在,裸露出其客觀本質。藝術家或美術史一般對寫實繪畫有慣性認識,他們在區別不同藝術傾向的繪畫作品時,通常是根據畫面的視覺經驗結果進行歸納和判定,是抽象還是具象?表現還是再現?寫實還是寫意?有明顯符號特征的容易被認定為抽象,如康定斯基和米羅的條形、方形、孤線等符號構成的畫面。如果視覺效果足以體現畫家所刻畫的形體,并且細節反應客觀并具有高度的形體辨識度,通常會被認為是寫實作品。介于二者之間的帶有書寫性精神表達和意象傾向意味的作品,則被認為是寫意作品,如徐渭和八大山人。基于客觀對象,強調主現感受并有主觀創造表現形式的作品,則更容易被視為表現性繪畫,如席勒和馬蒂斯。這是大家的普遍視覺認知,強調不同風格作品的相異性,繼而理所當然地分門別類地被寫入美術史,供美術工作者和愛好者研究學習。

那么,我們需要提出一個疑問,假設我們去掉“現代繪畫”中“現代”二字的時間界定,塞尚和賈科梅蒂該屬于哪類風格藝術家?中國的八大又該如何分類?按照大家上述的慣性視覺邏輯,塞尚和賈科梅蒂因其主觀的形體解構特征和無休無止的反復涂抹的表現方式,有較大可能會被歸為表現性繪畫。由于兩者在視覺上不如寫實繪畫作品較為全面地體現對象表征,和缺乏細節特征,不可能會歸于寫實。但是,如果把塞尚的二十多件以圣維多克山為繪畫對象的作品,和實景照片進行仔細比對時,結果會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會驚訝發現他的作品形象和實景是如此高度相似,甚至是盡量不放棄細節,塞尚似乎并沒有去刻意去增加什么或弱化什么?他只是竭盡所能地捕捉真實的對象。那為什么盡管他如此真誠地反映對象,繪畫結果卻和對象產生較大的形體差異呢?按照他自己的話,就是他的觀察方法變了,眼中的圣維多克山也就變了,最后是重構后的而又真實的圣維多克山。賈科梅蒂把“繪畫回到視覺本身”和“一點點接近對象”作為終身的信條,他對真實不盡地追問,對象是你看到的樣子嗎?力圖更加接近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比任何一個寫實畫家更加深層次地投入對真實的追尋,甚至可以說,是極度地接近“寫實”。畫家的實際情況和大家的慣性視覺定義產生了較大矛盾和分歧,塞尚和賈科梅蒂高度地追求真實,但他們的作品卻不具有寫實繪畫的形體辨識度和細節特征。
再來看看弗洛伊德和洛佩茲,他們已完成的作品細節畢現,而初步色稿和素描稿看上去卻又似乎非常的抽象,抽象的開始和具象寫實的終稿不在一極最終卻完成統一。中國的八大山人的魚和鳥,扭曲的身體和白眼,和作者本人何其相似反而顯得更加真實和符合常理,作者扭曲的人生觀和感情世界的介入,怎么畫都是桀驁不馴,怎么看都是孤獨清冷,心里的世界決定了眼中的世界,眼中的世界決定筆下的世界。
顯然,通過分類和概括定義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是不具有客觀性和準確性的,藝術家某些創作的潛在性和不可揭示性,致使觀者對畫家作品的解讀具有較大的先入為主性,導致遠離畫家原始的創作動機和創作路徑。這樣的不準確性和前后識讀的相悖性,造成了較大的視覺解析障礙,也給史學家帶來不小的工作麻煩。

那究竟如何認知畫家獨特的創作旅途,并具有客觀的判斷性呢?從上述情況看,畫家的觀察方法才是導致視覺的構成的途徑和方法,也是解讀畫家創作作品的關鍵點,即“眼睛決定自然”,觀看方式決定繪畫效果。畫家的不同風格特征和視覺語言特點皆從觀察方法開始拉開距離。美術史上的革命首先從觀察方法開始革命,而觀察方法的著力點不同導致繪畫效果有較大差異,如賈科梅蒂和洛佩茲的畫面結果差異較大,因為一個著力于對象真實存在的不盡追問,一個著力于對象細節體現,一個反復確定,一個毫發畢現。
即便是不同風格傾向的作品,畫家皆會不同程度地依據對象真實的原形,畫家按照自己的觀看方式和感興趣的著力點表達,畫面呈現出不同的語言范式和審美結果。寫實,其實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只是某些解讀方式遮蔽了我們的眼睛。而我們只有一點點走進藝術家的獨特創作旅途,才可能會真正了解藝術家的真正意圖,更加接近藝術的真相,還原一個真實的延續的不可割裂的美術史。
(作者簡介:黃劍武,湖北黃石人,著名藝術批評家、油畫家,重慶市文化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