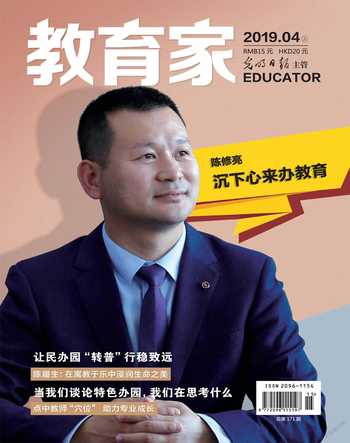民辦園“轉普”,在磨合中前行
谷珵
緊鑼密鼓的政策和行動下,不少民辦幼兒園舉辦者還存有觀望的心態。有從業人坦陳,政策引領的大方向大家都是認同的,但是,上面的政策如何在實施中保障到位,還是有一些擔心。
成本之憂
“推出一項利民政策需要保障舉辦者的合法權益。在學位短缺時期,民辦幼兒園承擔了大部分學前教育領域的基礎投入。如果在需要治理的時候不考慮這些背景,會損傷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也和國家提倡的多種力量辦學的大政方針相違背。”聯幫在線教育創始人、CEO李白直言不諱。她所指的,是今年年初媒體曝出的江蘇豐縣一家小區民辦園被強制收走事件。
彼時,當地教育局給出的回應是開發商違反了有關規定,擅自與私人租賃者簽訂辦園協議,舉辦者無權辦園。在幼教圈子里,這樁新聞幾乎盡人皆知。
“幼兒園房產使用不規范是歷史遺留問題,不能因為現在推進普惠就把歷史情況都忽略。”天津某民辦園園長凌燕對記者表示。幾年前,凌燕從北京的集團園跳槽,令她和投資人慶幸的是,運營的兩所幼兒園均是商業用地,并不受普惠的限制或者面臨強制轉普。
隨著《若干意見》和《通知》頒布,切斷了營利性幼兒園資產證券化的路徑,整個行業震蕩劇烈。但普惠性幼兒園并非新生概念,小區配套園問題更是在2010年“國十條”和歷次“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中反復強調,但因用地性質不清晰、財政投入不足等原因一拖再拖。新政之下一些地方卻迅速有了大動作:強制普惠的消息接二連三,舉辦者心生惶惑,憂慮財產無法得到保障。
“與民生相關的政策落地涉及多部委的協作,需要通過調研、討論、設立試點,最終做全國性推廣。由于教育發展不均衡,這輪幼教政策在形成了時間表后,各省市遇到的困難不同,反應速度不一。”李白表示,各地區具體執行方案的出臺一方面鑒于地方財政情況,一方面應建立在收集信息,制定補貼規則的基礎上。“根據國際經驗看,以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及稅收體系的數據為基礎補貼到家庭,而非無差異化補貼到園所,更適合我國學前教育發展現狀,而幼兒園收費應建立在國家統一的評級評類基礎上。但現在各地沒有這些后臺信息支撐決策,在補貼上只能選擇‘一刀切’。”
保定某集團幼兒園分園園長王歡介紹,在河北省的補助政策里,一個孩子每月只能獲得250-300元的補貼,對于集團下需要轉普的園所來說,運營壓力重重。
“任何投資人在最初都想把事情做好,特別是有情懷選擇幼教的舉辦者,絕不是以牟利為主,這是個資金回籠慢、營利很困難的行業。”凌燕說。目前,我國大部分普惠性民辦園的性質類似捐資辦學——考慮到前期在土地租金、設備購置、人員培訓方面的巨大支出,以及“5年小維修,10年大維修”的需求,以投資辦學進入幼教領域的舉辦者在面對普惠時心存疑慮。如果補貼不足,可能面臨嚴重的虧損。
李白認為,地方政府是愿意給予民辦園更多扶持和補貼的,但總體來說當前的財力有限。這也成為以財政補貼園所的普惠政策推進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先定義分類,再分批次進行支持和補貼,成了各地政府基于現狀的舉措。“規定時間內完成規定動作。”業內人士如是評價。
在凌燕周圍,舉辦者的態度大概分為幾種。一是二類幼兒園和小規模幼兒園,非常認同普惠,也希望拿到補貼,興奮地等待著政策的執行。一是中高端或集團辦園,或者能達到一級一類、示范園水平的民辦園,因為投入不菲,面臨的考驗巨大。也有些虧損的高端項目,主要是考慮普惠的成本,“劃得來就繼續,不行就撤退”。至于辦園比較早、成本回收得差不多的園所,分類時可以選擇非營利,但不選擇普惠,收費就能保障在3000-4000元。“怕就怕開辦時間不長,前期投了1000多萬元,現在哪種都不敢報,不知道未來是什么樣。”
不確定性加重了茫然。根據王歡介紹,轉成普惠有對應的前期投入清算公式。“但這個公式誰來審理,誰來清算,怎么確定投入可以拿到補償,都沒有細節,也不知道普惠后應該怎樣運營。”于是,觀望成了一些人的選擇。而補貼能否及時到位,也化為舉辦者心頭的在意事。
質量之思
地區基本情況和政策執行力度差異大,成為非常現實的狀況。
江蘇一所連鎖園園長葛晴表示,因為江蘇公辦園數量比較多,因此完成指標的壓力并不算大。同時要考慮整體情況,即便局域的普惠覆蓋率已經完成了,一些教育用地的民辦園暫時沒有被“點名”,但如果地區整體未達標,這樣的園所依然面臨必須轉普的出路。
但數據“達標”與緩解“入園難”“入園貴”的體驗能否相吻合?一些地方的公開信息里,公辦園已經達到民辦園的1~2倍,但家門口公辦園難入的新聞依舊層出不窮。許多公辦園都是駐區單位舉辦,大門只向本單位職工子女敞開。
更重要的是,轉普后教育質量打折的擔憂,成為不絕如縷的聲音。一些幼兒園為節省開支,削減師資投入。“按照新的辦園標準測算,教職工工資支出已經占到70%,再辦園只有30%的空間,但是將來沒有工資上調余地。”北京一名經驗豐富的集團幼兒園總園長直言。在她看來,如何保障教師工資待遇和幼兒園可持續發展,是擺在學前教育面前的難題。
“如果補貼不足,質量下降是一定存在的。好老師不好招,招了不好留,有些外教的費用甚至比園長還高。”凌燕指出,削減外教甚至成了普惠性民辦園求生存的“首選”。而王歡所在的集團也要求整體提升效率,并裁掉了相當一部分工作效率低的教師。
相較于公辦園課程偏重主題活動,民辦園的課程更加豐富,但也存在嚴重的“小學化”傾向,普惠后興趣課程必然縮減。也有民辦園采用增加班級人數、不再實行教寢分離制度或者延長寒暑假上學時長等辦法來應對低收費,而無論哪種變化,服務與原先承諾不匹配,都存在家長與園方產生糾紛的可能。
“多數舉辦者寧可注冊成營利性多交稅,也不愿意注冊非營成為普惠,一是顧慮成本,二是承擔風險。”凌燕的態度果決。對她來說,把幼兒園做小、做精,給每個孩子和家長服務到位是第一位的,而非管理大班額的園所。“大體量的校園特別牽扯精力,安全問題、家長糾紛翻了幾番。園長一日三巡,如果是四五百個孩子,除了把任務攤派下去,真的很難覆蓋到位。”
在旁人眼中,凌燕的幼兒園無疑是幸運的那個——第二所趕在政策出臺前拿到了營利性分類的批準。“由于營利性幼兒園的辦園標準和監管標準還需摸索,因此很多地區營利性幼兒園很少獲批。”李白表示。這一說法也在不少園長和學者口中得到印證。
有教育情懷的從業者依然是學前發展的中流砥柱。“平不平庸取決于園長。我已經做了20多年幼教了,看到幼兒教育從單純的保障生活需求一步步走向專業化。各地對民辦園的資金支持短時間內難以達到同樣的力度,但是否就無法進行教研了呢?”在葛晴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她始終記得鼓舞自己的精神榜樣陶行知先生,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下堅持搞研究,“幼教行業需要真正從兒童出發。”
不過,葛晴也理解一些園長對“被普惠”存在抵觸情緒。實際上,有些從業者萌生退意,寄望轉手。“從支持多種力量辦學的角度來說,維護社會力量辦學的合法權益,也是促進行業發展的重要一環。”李白坦言,即便政府作出接手退出者學校的準備,但恐怕沒有足夠的人員去運營,“整個行業的人才缺口還是非常大,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亟待提升。如果執法過程中出現一些強制措施,受害的還是家長和孩子。”
分層之變
宏觀層面的風向標,透露出整個幼教行業分層的加速到來。
李白解釋,政策大方向正確無疑,此前的確出現一些需要治理的亂象。“許多民辦園收費不合理,家長付出的學費未用于教學質量的改善上,而是花費在營銷包裝或者過度的硬件投入。”教育需要回歸本質,因此李白也認為,大部分幼兒園應該是服務大眾,而非成為百姓的負擔。
幼兒教育關乎民生。可以肯定的是,此前粗線條的發展模式將發生改變。新政新法的普及無疑將推動行業的規范化,資本介入帶來幼教領域資源整合趨勢加強,馬太效應會逐漸凸顯。
洗牌的過程中,不少幼教集團開始調整業務方向。具備優質管理團隊和體系者,考慮做to B類業務,提供幼兒園管理、教材、軟硬件開發等配套服務,向輸出運營體系轉型,同時積極擁抱互聯網。轉型快的那批,將會占據先機。
對于夾在普惠園和高端園間的中低端幼兒園,和君咨詢合伙人丁寧表示,其生存空間因為軟硬件方面拼不過公辦園和高端園,想經營下去,轉型是必然面臨的選擇。一些小區配套園在普惠政策實施后開設了額外的興趣班來保證利潤;抱團取暖也被視為另一條出路。而那些中高端幼兒園,丁寧建議將產業鏈延展。王歡所在的幼兒園,就選擇進軍托育業務,“這一領域市場尚不成熟,能夠吸引資本”。
九鼎投資幼教產業整合基金總經理謝萬彬表示,非營利幼兒園依然可以產生盈利:“80%的非營利幼兒園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十分需要教師培訓、軟硬件設施等托管服務。借此,幼兒園可以以精細化管理及規模取勝。”沉下心來做教育的人,反而會迎來一些機會。
至于另外20%的營利性幼兒園應該如何辦,具體的辦園標準還沒有明確。“普惠性幼兒園可以參考公辦幼兒園,但營利性幼兒園現在沒有對標,肯定不能單純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評判。”李白說,“首先要把幼兒園的評級評類做起來,讓百姓看得到實實在在的教育教學質量評估,脫離了這些談營非、普惠,都只是概念。”
作為教育服務類機構,聯幫在線教育主要通過雙師課堂與雙師師訓為二三四線城市的幼兒園提供幫助,讓優質教育資源經由互聯網下沉。李白告訴記者,政策的變動對公司影響并不算大,因為對教育教學質量的需求始終存在,在眼下的環境里,正是發展業務的好時機。但她也承認,此輪政策可能會影響到未來行業的走向。
“當前的幼兒教育行業是‘還債’的過程,政策從制定到執行應該需要磨合期。”李白表示,“現在只希望靴子能盡快落地,并且告訴大家政策組合拳已經出完,許多舉辦者前期投入不菲,還是愿意繼續下去,方向明確后就可以配合政策考慮自己的策略。一個行業只有政策有利且穩定,才會得到大發展。”
(文中園長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