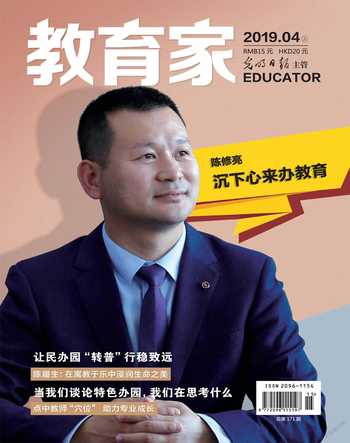發展更有質量的學前教育要信任民間力量
谷珵
伴隨著鼓勵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浪潮,上世紀末,民辦教育獲得了跨越式大發展。2017年9月,民辦教育“營利性、非營利性”的分類改革正式拉開大幕。此后,涉及幼教領域的重磅政策頻頻出臺,帶來利好大方向的同時,也因部分具體措施的不甚清晰,增添了民辦園舉辦者的猶疑與不定。如何理解普惠的內涵?公益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推進中可能遇到哪些問題?營利性幼兒園有多少生存空間?本刊記者采訪了國內民辦教育知名專家,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吳華,聽聽他的解讀與建議。
《教育家》:在您看來,“普惠”概念應該如何理解?
吳華:目前,關于“普惠園”的理解一直存在爭議,一些地區將“普惠”與“非營利”混為一談。實際上,兩者的區分并不復雜。從市場角度看,“普惠”通常是指產品的價格屬性,往往與低廉的價格關聯;“非營利”是機構的法律屬性,一個機構如果不分配經營結余,也不要求財產權利(分享剩余財產),“活著不分錢,死了不分財”,那就是非營利組織。產品沒有“營利”與否的審計,機構也沒有“普惠”與否的糾結。當產品價格低廉、大眾負擔得起的時候,這種產品或者勞務可以被稱為普惠性,它和機構的屬性沒有必然聯系。對于有差異化需求的產品而言,價格已經不是“普惠”的核心要素,借助市場化的自由交易才是實現“普惠”的不二選擇。
《教育家》:也就是說,理論上,“普惠”與“營利”具有兼容性。但根據各地已出臺的政策來看,除了個別地區,兩者并不能很好地達到平衡,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吳華:在當前的話語體系中,只有非營利才能申請普惠,這是概念錯誤。必須強調的是,普惠園不限于非營利,才能繼續討論,否則前提就不成立了。政策的出發點是讓百姓能有安全有保障、收費合理的幼兒園可以選擇,達到目標的前提當然是園所越多越好。一方面園所相互競爭,就不會漫天要價;另一方面如果不限定普惠必須做非營利,許多民辦園便能夠以營利園的身份提供普惠產品,“入園難”問題更容易解決,民辦園舉辦者的財產權利得到了保障,只是少賺一點錢。各退一步,大家都有積極性,才是雙贏的選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出“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幼兒園,只要符合安全標準、收費合理、家長放心,政府都要支持。”因此可以理解,營利性民辦園符合要求的照樣可以獲得支持。
從家長視角看,其實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幼兒園的品質、口碑、價格,關心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孩子能得到什么、付出的代價值得與否,園所自身的屬性、賺不賺錢等并不最終影響家長的決定。如果不糾結營利與否的問題,便會形成一個激勵相容的機制:市場的競爭決定了民辦園為了賺錢必須把品質搞好,而且價格還不能比別人高太多,并需不斷創新。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民間資金進入,自然就會競爭、淘汰,留下的即是更好的,這是市場經濟的普遍法則。但是許多人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不能接受教育營利。
《教育家》:普惠性民辦園的補貼標準是怎樣制定的?如何保障補貼的落實?
吳華:各地補貼標準不一致,全國大部分地方的補貼標準是按小學生均公用經費國定標準,也就是每年600元左右。以杭州為例,一級園收費在550-650元左右,兩倍之內算普惠,最多也就是1300元,也就意味著一年10個月是13000元。扣除“兩教一保”老師的工資,一個公辦園老師一年獲得的薪水大概是7萬元,再扣除房租,即便能生存,但結余是非常有限的,意味著學校的發展后勁不足。或者只有通過提高生師比控制成本。舉辦者做這些事業,除了教育情懷,也有經濟需要和改善生活的目的。
補貼的落實問題并不大,按民辦普惠園2000萬兒童全部補貼到位也不過120億元,大概占公辦園生均財政性經費的5%左右。即便民辦得到了補助,依然比公辦少得多。按照50%幼兒在公辦園的目標來說,那么誰應該讀公辦,誰應該讀民辦呢?
《教育家》:到2020年,全國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的占比達到80%。這樣的標準對地方政府提出怎樣的要求?如果非普惠幼兒園限定在20%,會不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壟斷?對于營利園所,有什么措施限制運營上的過度逐利行為?
吳華:在數字上完成任務并不困難,把所有的配套園全部收回,民辦比例必然收縮,此消彼長。目前全國有城區民辦園6萬所,非民辦園1.8萬所,其中政府辦的公辦園1萬所,其他部門辦園8千所;鎮區有民辦園5.8萬所,非民辦園2.7萬所,其中政府辦的公辦園2.3萬所,其他部門辦園4000所;鄉村有民辦園4.1萬所,非民辦園4.9萬所,其中政府辦的公辦園4.1萬所,其他部門辦園8千所。幼兒園的整體格局是按照城區、鎮區、鄉村三個層次劃分的,城區主要依靠配套園,鎮區相對問題大些,但鄉村和城郊接合部還有大量的“低、小、散”無證園。按目前全面收回小區配套園的政策設計,不管最終是辦成公辦園還是普惠性民辦園,會導致學前教育的公共財政資金更多流向城區。此外,在財力、師資、政策、風險等方面,普惠政策對地方政府都提出巨大的挑戰。
營利性的競爭者減少了,從常理推測,價格會進一步上漲。因為供給的力量減少了,需求相對增強,平衡供需矛盾一般就是通過價格杠桿,高端園的價格就更高了。但考慮到其他幼兒園整體收費下降,收費太高可能會失去競爭力,而導致價格不敢上升甚至下降,看起來是好事,但意味著營利園也會壓縮成本。普惠后價格限制,如果還想從中獲利,只能降低成本,質量就面臨下滑,和政府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還要根據實踐來檢驗,影響人們決策的政策因素非常復雜,地方也必然會采取更合理的變通做法,“摸著石頭過河”,也許擔心是多余的。至于針對營利園,目前還沒有相應措施出臺,需要繼續等待。
《教育家》:要想建好民辦普惠園,需要怎樣的制度設計?
吳華:民辦園發展的治本之策是實施“教育券”。要兼顧公平、效率、選擇性三大政策目標發展學前教育,一定要跳出公辦園的思維窠臼,尋找更加有效的發展路徑,這個路徑就是教育憑證制度,俗稱“教育券”。在學前教育的教育憑證制度中,政府將學前教育的公共財政資金等額量化給轄區內每一個適齡兒童,每個兒童由此獲得一張代表學前教育公共服務購買力(也是兒童權利憑證)的等值憑證,家長無論選擇公辦園還是民辦園,被選擇的幼兒園就得到一張上面所說的教育憑證,幼兒園憑其所獲得的全部教育憑證到教育局去換取公共財政資金,公辦園在教育憑證之外免費或限價,民辦園放開價格管制,教育券以外部分由家長承擔。
教育憑證制度做到了同時兼顧公平、效率、選擇性三大政策目標,但實踐上還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比如教育券的使用規則是按照學生人數,幼兒園招生越多就能得到越多的撥款。但不能只看到城市里,農村還有很多幼兒園,無法招收到那么多學生,這種情況下就要有特殊的政策來扶持。同樣在城里可以把教育券分成等級,達到一定數額以上,教育券是和價格成反比關系,價格越高,教育券的單價額度就越低。這樣百姓也能在品質和價格間做出綜合選擇。在真實的選擇中,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把品質和價格綜合考慮,而且個人對品質價值的認知有很大差別。教育券能極大激發民間資本投資學前教育的積極性,持續改善“入學難”和“入學貴”狀況,在中國香港地區已經有非常成功的實踐。
《教育家》:如何看待資本對于學前教育發展所發揮的作用?
吳華:對資本要有一定的規范,但不必過慮。經過多年的市場洗禮,現在發展比較好的園所大部分質價相符,否則早就被市場淘汰了。過去幾年,一些營利性民辦園為了逐利,想出了名目繁多的“雙語教學”“藝術特長”“早期潛能開發”等項目。很多家長“硬著頭皮”交贊助費、占坑費、空調費……應該整治的是這樣亂收費的園所。現在有一種認識誤區,認為資本進來就是為了把優質資產打包上市然后退出,退出后的一地雞毛變成園所承擔。實際上,從股市來說,資本和教育的關系并非那么絕對。收購非營利學校后上市,首先不是以學校的名義上市,因為非營利組織不具備上市資格,而是以公司名義上市。即便對于營利性民辦學校,假設以學校上市,那么上市以后,股東變化也不會劇烈影響到學校的運轉。至于擔心以學校名義舉債或者破產,這些需要采用證券市場的通行規則加以規范,比如不能舉債做些非教育類的事情,必要的規范和配套措施是需要的。
當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對政府和民間都是挑戰和考驗。大家都在互相摸索、磨合和交流中,這個時候互信非常重要,而互信的前提是首先要信任民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