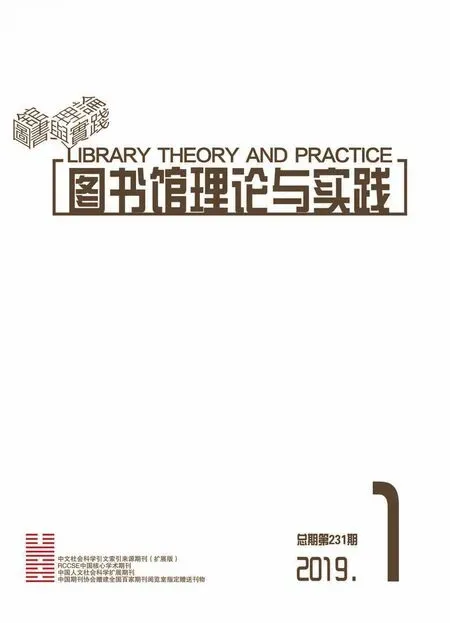圖書館與口述史學(xué):淵源、現(xiàn)狀和存在問(wèn)題
全根先
(國(guó)家圖書館)
人類區(qū)別于地球上所有物種的一個(gè)根本性標(biāo)志,就是概念式、符號(hào)化的記憶以及文明的傳承。所謂概念式、符號(hào)化的記憶,是指人類擁有可以脫離現(xiàn)場(chǎng)的某種情緒并回憶以前經(jīng)歷事情的一種能力,這是地球上任何其他物種所不具備的。人類因?yàn)閾碛羞@種能力,才有了歷史,才有文明的傳承。歷史就是傳承,沒有傳承就沒有歷史。人類傳承文明的手段或途徑,除了實(shí)物,主要是語(yǔ)言和文字。語(yǔ)言是口頭傳承,世代相傳;文字則是更高級(jí)的記錄與傳承手段,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文字發(fā)明以后,人類開啟了以書籍為主要載體記錄與傳承文明的偉大時(shí)代,而口頭傳承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有了文字,就有了圖書館。圖書館有賴于書籍文獻(xiàn)而誕生,千百年來(lái)一直履行著收藏與傳播人類文明的重要功能,是人類文明延續(xù)發(fā)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寶藏。同時(shí),在歷史發(fā)展的長(zhǎng)河中,圖書館本身也隨著文明的進(jìn)步而不斷地改變自己的面貌,拓展自己的職能。當(dāng)代圖書館面貌與職能的一個(gè)顯著變化,就是圖書館記憶功能的回歸,圖書館不僅僅滿足于作為文獻(xiàn)收藏與傳播的社會(huì)文化機(jī)構(gòu)的社會(huì)角色,也主動(dòng)地投入到活態(tài)的口述歷史文獻(xiàn)的搶救與記錄之中。這樣,圖書館與口述史學(xué)就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lái),成為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一個(gè)閃光點(diǎn)。
1 口述史學(xué):史學(xué)領(lǐng)域的后起之秀
人類通過(guò)口頭傳遞經(jīng)驗(yàn)、傳承文明的傳統(tǒng)可謂源遠(yuǎn)流長(zhǎng),但口頭傳承與口述史學(xué)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口頭傳承是一種自發(fā)的、本能的有時(shí)甚至是無(wú)意識(shí)的行為;而口述史學(xué)則是建立在一定理論基礎(chǔ)上、借助某種記錄手段進(jìn)行的有目的、有計(jì)劃的科學(xué)行為。與傳統(tǒng)史學(xué)不同,口述史學(xué)不是簡(jiǎn)單地收集和利用已有的文獻(xiàn)進(jìn)行研究,而是主動(dòng)地搜集甚至是創(chuàng)造新的文獻(xiàn)。在歷史學(xué)的大家庭中,口述史學(xué)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分支學(xué)科。
一般認(rèn)為,現(xiàn)代口述史學(xué)創(chuàng)立于1948年。美國(guó)口述歷史協(xié)會(huì)的一份報(bào)告指出:“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為一種記錄歷史文獻(xiàn)的現(xiàn)代技術(shù)而確立自己的地位的,當(dāng)時(shí)哥倫比亞大學(xué)的歷史學(xué)家A.內(nèi)文斯開始錄制美國(guó)生活中的要人們的回憶。”[1]實(shí)際上,早在1938年,現(xiàn)代口述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A.內(nèi)文斯就出版了《通往歷史之路》一書,主張開展口述歷史研究。1948年,內(nèi)文斯在哥倫比亞大學(xué)提出口述歷史科研項(xiàng)目,創(chuàng)建了美國(guó)歷史上第一個(gè)研究口述史的專門機(jī)構(gòu)——哥倫比亞大學(xué)口述歷史研究室。20世紀(jì)50年代,美國(guó)口述史學(xué)研究進(jìn)展不大。60年代初,有一些口述史學(xué)論著陸續(xù)問(wèn)世,較有影響的如W.鮑姆的《地方史學(xué)界的口述歷史》、C.戴維斯的《口述歷史:從磁帶到打字機(jī)》、R.柯蒂斯的《口述歷史計(jì)劃指南》等。1966年,美國(guó)口述歷史協(xié)會(huì)正式成立。與此同時(shí),口述史學(xué)研究開始由美國(guó)傳播到世界各地,加拿大、英國(guó)、法國(guó)、日本等許多國(guó)家和地區(qū)出現(xiàn)了一批口述史學(xué)者與研究團(tuán)體。1980年,美國(guó)口述歷史協(xié)會(huì)提出了一套評(píng)價(jià)口述歷史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定了口述歷史工作者和口述歷史機(jī)構(gòu)的義務(wù)。口述史研究被廣泛應(yīng)用于政治史、企業(yè)史、部落史、宗教史等領(lǐng)域。在亞洲,口述史學(xué)也很快發(fā)展成為一門新興的“熱門”學(xué)科。
什么是口述史學(xué)?對(duì)于這個(gè)問(wèn)題,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意見分歧較大。不少口述史學(xué)論著提出了各自對(duì)于口述史學(xué)的定義,如保羅·湯普遜、[2]唐納德·里奇、[3]周新國(guó)、[4]楊祥銀[5]等。筆者以為,探討口述史學(xué)的概念固然有必要,但是,也沒有必要對(duì)其進(jìn)行過(guò)分考究,各家所表達(dá)的觀點(diǎn)雖不盡相同,僅就口述史實(shí)踐而言,實(shí)則是大同小異。鐘少華先生認(rèn)為:“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chǎn)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yǔ)言,利用科技設(shè)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都是口述史料,將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jīng)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歷史專著。”[6]
口述史學(xué)自誕生以來(lái),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不斷變化,不同時(shí)期呈現(xiàn)出不同特點(diǎn)。20世紀(jì)50年代以“磁帶革命”為特色,70年代以“音像革命”為特點(diǎn),80年代發(fā)生“計(jì)算機(jī)革命”,90年代出現(xiàn)了“電子革命”;進(jìn)入21世紀(jì),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和信息化時(shí)代的到來(lái),口述史學(xué)的理論與實(shí)踐得到突飛猛進(jìn)的發(fā)展。每一次技術(shù)革命所帶來(lái)的口述史學(xué)理論與方法論上的突破,往往是人們始料未及的。至于口述史學(xué)的研究成果,姚力先生曾有過(guò)概括:一是帶有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傾向的口述史;二是立足文學(xué)的口述史;三是自傳體口述史;四是政要人物口述史;五是普通民眾口述史。[7]
如今,世界上幾乎找不到有哪個(gè)地方的人不進(jìn)行口述歷史的。正如唐納德·里奇所說(shuō):“自從世上第一套錄音設(shè)備出現(xiàn),由蠟盤滾筒逐漸發(fā)展到磁盤、有線錄音機(jī)、卡式錄音匣和卡式錄音帶,口述史家便開始使用這些設(shè)備進(jìn)行各式各樣的訪談,對(duì)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議者、原住民和移民、藝術(shù)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職人士和俗人。他們不僅錄制了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戰(zhàn)受監(jiān)禁的日裔美國(guó)人和蘇聯(lián)思想勞改營(yíng)的受刑人等的回憶錄;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區(qū)衛(wèi)星城鎮(zhèn)和偏僻鄉(xiāng)村內(nèi)家庭與社區(qū)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當(dāng)歷史學(xué)家意識(shí)到大部分的歷史書籍遺漏了婦女和少數(shù)民族時(shí),口述史家便為婦女和少數(shù)民族做錄音,以便建構(gòu)起更多元而精確的歷史畫面。”[3]
2 圖書館與口述史學(xué)的歷史淵源
口述史學(xué)雖然是較為年輕的學(xué)科,但是,對(duì)于圖書館而言,口述歷史卻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大量口述歷史文獻(xiàn)早已保存于浩如煙海的圖書館館藏之中。口述歷史其實(shí)是歷史學(xué)最古老的表現(xiàn)形式,其起源可追溯至遠(yuǎn)古時(shí)代的民間傳說(shuō)或口頭傳說(shuō)。口頭傳說(shuō)或民間傳說(shuō)未必都是歷史事實(shí),更不能與現(xiàn)代口述史學(xué)混為一談,但是,其中不乏歷史真實(sh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gè)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與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口頭傳說(shuō)和民間傳說(shuō)不僅是口述史學(xué)研究的歷史淵源,還是人種學(xué)和社會(huì)人類學(xué)研究的基本來(lái)源之一。
無(wú)論是中國(guó)還是西方,均有大量歷史文獻(xiàn)保存著口述史料。早在西周時(shí)期,中央政府就專門設(shè)有史官,記錄周天子與其臣下的言行事跡,《禮記·玉藻》說(shuō):“動(dòng)則左使書之,言則右使書之”。[8]司馬遷所著《史記》收錄了他通過(guò)口頭采訪而得到的歷史資料。如《刺客列傳》中,他最后談到荊軻刺秦王的史料來(lái)源:“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wú)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9]即關(guān)于荊軻刺秦王的資料,是他從公孫季功、董生處聽說(shuō)的,公孫季功、董生又是聽秦始皇私人醫(yī)生夏無(wú)且說(shuō)的。古希臘《荷馬史詩(shī)》中,有許多內(nèi)容本是民間行吟歌手的集體口頭創(chuàng)作,經(jīng)過(guò)荷馬整理,至公元前6世紀(jì)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lái),其中特洛伊木馬傳說(shuō)已為考古發(fā)掘所證實(shí)。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zhēng)史》中,也保留了許多口述史料。
事實(shí)上,即使在史學(xué)發(fā)達(dá)、文獻(xiàn)眾多的時(shí)代和國(guó)度,人們都沒有完全拋棄運(yùn)用口述史料。法國(guó)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參考包括個(gè)人回憶在內(nèi)的很多生動(dòng)形象的口述史料。再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英國(guó)工人階級(jí)狀況》中,均引用了來(lái)自報(bào)刊、白皮書、回憶錄等來(lái)源豐富翔實(shí)的口述史料。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L.麥考利在《英格蘭史(1848—1855)》一書中,也曾大量運(yùn)用口述史料。在中國(guó),宋元時(shí)期盛行“講史”傳統(tǒng),所謂“講史”,就是通過(guò)口耳相傳的方式在民間傳播歷史知識(shí),后來(lái)“講史”發(fā)展為歷史演義,這是中國(guó)古代口述歷史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唐德剛先生曾對(duì)口述史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A.內(nèi)文斯說(shuō):“你不是口述歷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詞的發(fā)明人,口述歷史是中國(guó)和外國(guó)都有的老傳統(tǒng)”。[10]
在人類歷史上,圖書館一直扮演著傳承文明的關(guān)鍵角色。古往今來(lái),圖書館名稱雖然不一,其規(guī)模、狀態(tài)、命運(yùn)更是各不相同,然而作為公共文化機(jī)構(gòu),圖書館記錄歷史、傳承文明的基本功能始終未變。圖書館之所以能履行這一社會(huì)功能,源于其記憶與傳播文明的能力,記憶又是傳播的前提與基礎(chǔ)。人類是需要記憶來(lái)延續(xù)和發(fā)展的一個(gè)物種。不同于個(gè)人,圖書館記憶人類的歷史與文明成果是個(gè)體記憶的有機(jī)聚合,是個(gè)體記憶在空間上的拓展與時(shí)間上的延伸。
圖書館以何種形式承載社會(huì)記憶?那便是通過(guò)記憶的“物化”。所謂記憶的“物化”,就是記憶的“外化”,主要存在形式是千百年來(lái)留存于世的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xiàn)。美國(guó)圖書館學(xué)家謝拉說(shuō):“圖書館正是社會(huì)的這樣一種新生事物,當(dāng)人類積累的知識(shí)大量增加以至于超過(guò)人類大腦記憶的限度時(shí),當(dāng)口頭流傳無(wú)法將這些知識(shí)保留下來(lái)時(shí),圖書館便應(yīng)運(yùn)而生了”。[11]隨著口述史學(xué)的興起,在收藏與傳播文獻(xiàn)的同時(shí),采集口述歷史,成為新型文獻(xiàn)的創(chuàng)造者、傳播者,記憶與傳播功能雙輪驅(qū)動(dòng),圖書館將真正成為“世界最美的知識(shí)花園”“人類永恒的思想天堂”。
3 圖書館界口述史學(xué)開展現(xiàn)狀
現(xiàn)代口述史學(xué)自誕生之日起,便與圖書館密不可分,圖書館員是口述史學(xué)研究的生力軍,圖書館是口述歷史項(xiàng)目的重要推動(dòng)者與支持者。美國(guó)早期口述歷史研究機(jī)構(gòu)大都設(shè)在圖書館。除了總統(tǒng)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計(jì)劃外,美國(guó)成立最早、影響力最大的兩個(gè)口述歷史研究室——哥倫比亞大學(xué)口述歷史研究室和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地區(qū)口述歷史辦公室,即分別設(shè)于巴特勒?qǐng)D書館和班克羅夫特圖書館。[12]國(guó)際圖聯(lián)(IFLA)一直致力于口頭傳統(tǒng)的搶救與保護(hù),1999年在泰國(guó)曼谷舉行的第65屆國(guó)際圖聯(lián)大會(huì)上,其中一個(gè)主題便是“口頭傳統(tǒng)的收集和保護(hù)”,對(duì)圖書館與口頭文化的關(guān)系以及圖書館新的職責(zé)定位進(jìn)行了交流與探討。
在實(shí)踐層面,圖書館界在口述歷史采集方面始終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美國(guó)為例,口述歷史已成為圖書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國(guó)總統(tǒng)圖書館、國(guó)家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都開展了口述歷史采集工作。富蘭克林·羅斯福早在1938年就建議設(shè)立總統(tǒng)圖書館,對(duì)歷任總統(tǒng)在任期間的各種文獻(xiàn)檔案、口述資料等進(jìn)行記錄收集。20世紀(jì)50年代起,每位美國(guó)總統(tǒng)卸任以后,總統(tǒng)圖書館都要對(duì)總統(tǒng)周圍的內(nèi)閣成員、高級(jí)參謀、政敵、政治要人以及親屬進(jìn)行采訪,整理和保存這些口述歷史資料。這是目前美國(guó)唯一的一個(gè)長(zhǎng)期受聯(lián)邦政府資助的口述歷史項(xiàng)目;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圖書館、美國(guó)國(guó)家醫(yī)學(xué)圖書館、美國(guó)國(guó)家農(nóng)業(yè)圖書館均開展口述歷史項(xiàng)目。美國(guó)各州公共圖書館自20世紀(jì)70年代起,也開展了許多口述歷史訪談?dòng)?jì)劃。如今,美國(guó)口述歷史研究工作主要由公共圖書館承擔(dān)。
英國(guó)、法國(guó)、德國(guó)、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以色列、墨西哥、西班牙、印度、巴西、新加坡、臺(tái)灣等國(guó)家和地區(qū)圖書館,都各自開展了口述歷史項(xiàng)目。1992年,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發(fā)起世界記憶工程,其關(guān)注重點(diǎn)不僅有手稿、圖片、各種檔案,還有口述歷史等資料,開展各種形式的記憶項(xiàng)目是其工作的核心內(nèi)容。許多國(guó)家的圖書館尤其是國(guó)家圖書館啟動(dòng)了國(guó)家記憶工程,如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圖書館的“美國(guó)記憶”、英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的“國(guó)家生活故事”、德國(guó)國(guó)家圖書館的“我們的故事——民族的記憶”、荷蘭皇家圖書館的“荷蘭記憶”、日本國(guó)會(huì)圖書館的“日本年歷”、新加坡圖書館管理局的“新加坡記憶”等。
中國(guó)大陸現(xiàn)代口述史學(xué)的源頭可以追溯至20世紀(jì)5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國(guó)外口述史學(xué)理論逐漸被引進(jìn),口述史學(xué)日益引起歷史學(xué)界以及社會(huì)各界的關(guān)注。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lái),口述史學(xué)研究蓬勃開展,國(guó)家圖書館以及各地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紛紛加入到口述歷史采訪活動(dòng)之中。2012年,國(guó)家圖書館啟動(dòng)“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時(shí)至今日,已開展了“東北抗日聯(lián)軍”“大漆髹飾”“蠶絲織繡”“中國(guó)年畫”“我們的文字”“學(xué)者口述史”“中國(guó)遠(yuǎn)征軍”“中國(guó)圖書館界重要人物”等口述歷史項(xiàng)目,獲得了大量有價(jià)值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并通過(guò)出版、展覽、講座、現(xiàn)場(chǎng)展示、網(wǎng)上發(fā)布等方式,向社會(huì)公眾傳播,得到了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和社會(huì)各界的一致好評(píng)。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2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guó)圖書館年會(huì)上,專門設(shè)立了“中國(guó)記憶資源共建共享”分會(huì)場(chǎng),國(guó)家圖書館與國(guó)內(nèi)30余家單位聯(lián)合發(fā)起并簽署了《全國(guó)圖書館界共同開展記憶資源搶救與建設(shè)倡議書》。2016年,中國(guó)記憶“中國(guó)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資源建設(shè)”項(xiàng)目正式啟動(dòng),除國(guó)家圖書館外,第一批申報(bào)單位共有18個(gè),受訪人28位,目前,采訪工作已基本完成。2018年6月1日,在河北廊坊舉行的中國(guó)圖書館年會(huì)“中國(guó)記憶資源建設(shè)”分會(huì)場(chǎng)上,又啟動(dòng)了“中國(guó)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資源建設(shè)項(xiàng)目”第二批申報(bào)工作。
圖書館進(jìn)行口述歷史采集,搶救活態(tài)文獻(xiàn),具有諸多有利條件。首先,圖書館具有豐富的文獻(xiàn)收藏與開發(fā)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作為新型文獻(xiàn)的口述歷史資料,圖書館將以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收藏與開發(fā)為基礎(chǔ),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與利用,特別是在口述歷史資料連續(xù)、長(zhǎng)久與有序保存方面優(yōu)勢(shì)更為突出。其次,圖書館具有獨(dú)特的資源與技術(shù)優(yōu)勢(shì),擁有覆蓋全社會(huì)的公共文化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加之圖書館的軟硬件設(shè)施齊備,將在口述歷史資料開發(fā)利用方面展示其技術(shù)優(yōu)勢(shì)。再次,在口述歷史采集方面,圖書館具備一定的人才優(yōu)勢(shì),圖書館員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和良好的專業(yè)素質(zhì),為開展口述歷史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最后,圖書館在開展口述歷史項(xiàng)目方面還具備一定的傳播優(yōu)勢(shì)。圖書館是讀者與書籍之間的橋梁,擔(dān)負(fù)著向社會(huì)公眾傳播文化知識(shí)的重任。圖書館可以利用其原有的知識(shí)傳播途徑,傳播最新的口述歷史成果,與廣大讀者互動(dòng)交流,成為社會(huì)公眾的“發(fā)聲”平臺(tái)。
4 口述歷史采訪中的主要問(wèn)題
目前,中國(guó)圖書館界已開展諸多口述歷史項(xiàng)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積累了一定的經(jīng)驗(yàn),但從總體而言,仍存在不少問(wèn)題。這些問(wèn)題中,既有國(guó)內(nèi)口述史界普遍存在的問(wèn)題,又有圖書館界自身問(wèn)題的特殊性。
首先,口述史學(xué)雖然在世界各地已開展了大半個(gè)世紀(jì),許多國(guó)家圖書館、地方圖書館、高校圖書館,以至民間機(jī)構(gòu)甚至個(gè)人都積極參與其中,然而,國(guó)內(nèi)圖書館界對(duì)口述史學(xué)的總體認(rèn)知程度還有待進(jìn)一步提高。在中國(guó)記憶“中國(guó)圖書館界重要人物資源建設(shè)”項(xiàng)目啟動(dòng)以前,開展口述歷史采集的省級(jí)公共圖書館相對(duì)較少,更不用說(shuō)市、縣級(jí)公共圖書館了;在高校圖書館系統(tǒng),情況也與此類似。長(zhǎng)期以來(lái),人們對(duì)于圖書館的認(rèn)識(shí)普遍停留在收集編目、收藏與開發(fā)利用已有文獻(xiàn);對(duì)于圖書館記錄歷史的職責(zé),即我們所說(shuō)的記憶職能,缺乏足夠認(rèn)識(shí),有的甚至根本不知口述史學(xué)為何物。筆者認(rèn)為,圖書館界開展口述歷史工作,領(lǐng)導(dǎo)重視是關(guān)鍵。領(lǐng)導(dǎo)如果不知道、不重視,不關(guān)注口述歷史的保存,口述歷史在圖書館界的開展必定會(huì)受到影響。
其次,目前圖書館界雖然不缺乏研究人員和高學(xué)歷的人才,但是,大多數(shù)人習(xí)慣于傳統(tǒng)的圖書館研究領(lǐng)域,沒有或較少關(guān)注口述史學(xué),對(duì)于圖書館存史之職責(zé)缺乏使命感和緊迫感,有的甚至寧愿去做一些沒有多少實(shí)際意義、低水平的重復(fù)研究,也不去接觸鮮活的社會(huì)生活,不去關(guān)注可能即將消失的文化遺產(chǎn)。也有一些人,他們想做一點(diǎn)事,或者也聽說(shuō)過(guò)口述史學(xué),但是,由于沒有深入了解口述史學(xué),缺乏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找不到有效路徑。有的人認(rèn)為,口述歷史是歷史學(xué)家的事,或者是學(xué)歷史專業(yè)人能做的事,別人無(wú)法涉足。這種說(shuō)法也不是沒有一點(diǎn)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對(duì),因?yàn)樗麄儧]有把記錄歷史與研究歷史區(qū)別開來(lái)。研究歷史,的確需要較深的史學(xué)修養(yǎng),然而,記錄歷史并不需要太多的專業(yè)知識(shí),只要你有熱情,懂得記錄歷史的基本方法,做好細(xì)致的準(zhǔn)備工作,就可以開展。實(shí)際上,目前真正用口述史料進(jìn)行歷史研究的作品并不多,大都是記錄歷史的口述作品,并且許多是非歷史專業(yè)人員、歷史學(xué)家的作品。
最后,目前圖書館界口述歷史工作中所存在的問(wèn)題有一些是國(guó)內(nèi)整個(gè)口述史學(xué)界存在的共性問(wèn)題,這些問(wèn)題主要有3方面。一是口述史學(xué)基本理論研究不夠,原創(chuàng)性、理論性的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二是口述歷史實(shí)踐缺乏工作規(guī)范,包括口述歷史訪談、文稿整理、影像編輯、編目加工等,缺乏比較權(quán)威的、操作性強(qiáng)的工作手冊(cè)。目前,國(guó)家圖書館中國(guó)記憶項(xiàng)目中心已草擬了“中國(guó)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共建共享手冊(cè),可以說(shuō)是這方面的有益嘗試。三是口述歷史采訪水平參差不齊,口述史料的采集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口述歷史研究所需。由于采訪者經(jīng)驗(yàn)不夠、準(zhǔn)備不足,一些口述歷史訪談項(xiàng)目往往未能充分挖掘,例如采訪一位學(xué)者,只談其專業(yè)領(lǐng)域的問(wèn)題,較少關(guān)注其求學(xué)經(jīng)歷、人生遭遇與時(shí)代背景。類似的問(wèn)題還有很多。
總之,開展口述史學(xué)研究與實(shí)踐,是圖書館保存社會(huì)記憶、傳承人類文明的職責(zé)所在,是一件利在當(dāng)代、功在千秋的崇高事業(yè),讓我們迅速行動(dòng)起來(lái),以舍我其誰(shuí)的使命感,積極投身到口述歷史工作之中,留住正在消逝的珍貴歷史記憶,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作出應(yīng)有的、更大的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