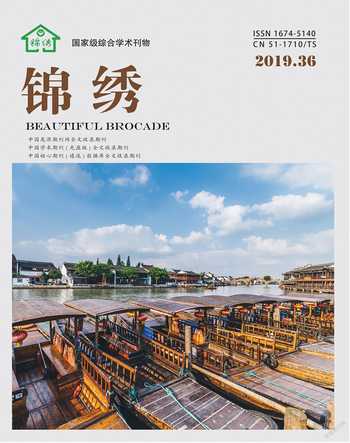從書法創作中的合文與拆分現象來看《張遷碑》
趙劉偉 李興邦 張翔
摘 要:《張遷碑》自明代出土以來,受到諸多金石學者及書法家的追捧,但同時也產生了諸多質疑,主要表現在《張遷碑》文本內容上的訛誤,以及在書寫過程中的用字不精準問題。因是碑書法典雅古樸,不像后人偽托之作,故歷史上對此褒貶不一,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之后,相應的如錢大昕、阮元等金石學家為之辯護。主要針對碑文中以“殯”為“賓”,以“忠”為“中”,以“既且”為“暨”等問題展開,對于以“殯”為“賓”、以“忠”為“中”阮元均找出了很好的例證進行反駁,唯以“既且”為“暨”不可解。本文大膽的從書法創作中的合文與拆分的角度提出了“既且”為“暨”字的拆分現象,本應拆為“既旦”,但因常年風化而導致“旦”為“且”字,故有此不可解之疑。
關鍵詞:《張遷碑》; 訛誤;合文; 拆分
《張遷碑》乃漢碑名品,于明朝初年再度現世。據說當時不為人看好,懷疑是后人的偽作。由于筆者長期伏案臨池,對《張遷碑》的藝術價值深信不疑,愛不釋手。偶爾看到有關《張遷碑》為后人偽托之作的言論,總覺心有不快之意,故深翻閱相關資料而追究之,并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張遷碑》做一定的介紹與挖掘,以期解內心不平衡之結。其一,《張遷碑》之出土與流傳;其二,從書法創作中合子與拆分來看《張遷碑》之文本文字問題。
一、《張遷碑》之出土與流傳
根據舊志所述,《張遷碑》出土于明代,“掘地得之,未詳其處,意必漢時古城舊境也。”[ 《漢碑集釋》引“府舊志”,見《漢碑集釋》,第489頁。]由上可知,其出土具體地點并未作出具體的交代,不僅如此,具體的出土時間亦未做交代,這不禁讓人心生疑慮。明代楊士奇(1365—1444)《東里集》續集卷二十有“漢谷城長張遷碑”一條云:“右漢谷城長張君碑,未有碑額,蓋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辭字畫皆古雅。碑在今東平州學。余得之宗丈東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明·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二十,文淵閣《四庫全即楊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東平州太守,見《東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詩序》及卷七《送李永懷歸東平序》。楊士奇題跋中稱楊季琛為“東平州守”,則其得到《張遷碑》之拓本,當在楊季琛在任東平州守之時。楊季琛之子楊黻字民服,與楊士奇往來頻繁,交情甚厚,民服死后楊士奇為其撰墓志銘,即現存《東里集》續集卷三十六之《衛府右長史楊君墓志銘》。墓志銘中提到楊黻“永樂甲申侍父官東平”,楊季琛任東平太守在永樂二年(1404)年前后,楊士奇從楊服民手中得到《張遷碑》拓片應是這一年。《東里集》是在目前的文獻中有關《張遷碑》最早的記錄。
目前所知,最早著錄《張遷碑》的金石學著作是都穆的《金薤琳瑯》,其書卷六錄《張遷碑》文,并有題跋云:“此碑予官京師時嘗于景太史伯石處見舊拓本,不及錄,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二、從書法創作中合子與拆分來看《張遷碑》之文本文字問題
最早對《張遷碑》碑文提出質疑的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在《金石文字記》中說:“其文有云‘謊遠既殯’者,‘賓’之誤;‘中謇于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加‘歹’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 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事實上,字法上或想通或錯誤,于此碑中已不下十余處,品鑒、習書者當明察而細辨之;就行文而論,此碑又有浮夸或張冠李戴之弊。譬如簡述張遷身世,將張仲、張良、張釋之、張騫諸賢皆扯來裝扮門面,或東或西,所居相去遙遙,其宗系亦絕不相及。其中“晉陽珮瑋,西門帶弦”還有個典故。“珮”通“佩”,“瑋”通“韋”,“韋”者皮繩也,喻緩也。“弦”則弓弦,喻急也。《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即晉陽宰。顯而易見,此處典故顛倒了是非。
文中產生了諸多錯誤,使人生疑也是常理,然不可因此而否定其藝術價值。換言之,經典未必八面玲瓏,蓋因行文、書寫、鐫刻非一人而為之,各道工序的水平良莠不齊,各司其職,于結點處難免出錯,亦是情理之中。如將“暨”分書為“既且”二字,便可意會當時情景。
張遷初為谷城長,后改任蕩陰令,由山東東阿遷往河南湯陰縣。漢制上,萬戶以上設令,不足萬戶則設長。也就是說,張遷此行官位略有升遷。谷城故吏集資為其立了塊功德碑,亦即前人所謂“去思碑”。碑文句法整飭而涉筆成韻,卻將歷代張氏名人不加分辨,作為張遷的祖先來記載,而對其直系祖、父一概不論,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想必立碑之時,張遷已離世,他人對其資料不詳,成碑后也未做校正,因此才出現此張冠李戴之誤吧。顧亭林對此結論是:“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同1。]
總的來說,顧炎武質疑的根據在于“忠”字誤寫成“中”,“賓”字誤寫成“殯”,“暨”字誤寫成“既且”二字,對于這三點疑慮我們逐一細考之。
清顧靄吉《隸辨》卷八云:“按以‘殯’為‘賓’,見《禮記·曾子問》,以‘忠’為‘中’,與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真二韻。唯以‘既且’為‘暨’,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拙,恐非摹刻也。”[ 清·顧靄吉:《隸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顧靄吉針對顧炎武所提出的三點疑慮進行辯解,對于“殯”為“賓”,“忠”為“中”,這兩點找到了強有力的佐證,對于第三點疑惑,為何將“暨”誤寫為“既且”雖然不好解釋,但觀碑文古雅樸茂,斷非后人摹刻所能及。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張遷碑》作為去思碑而言,除了歌頌其功德外,其書法藝術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從藝術創作的角度出發,有時為了考慮到章法疏密布局的安排,我們常會有將一字拆分成幾部分來寫,或將幾個字合為一字來書寫的行為。由于為了照顧整體章法的需要,這種合文與拆分的手段,在篆刻創作當中用的尤為廣泛,這樣的一種書寫方式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中。因此,我們不妨站在藝術創作的立場,大膽的提出這樣的結論:此“暨”字應是拆分成“既旦”二字來書寫的,只是碑面經年累月的腐蝕,將“旦”字混為“且”字,遂造成了顧氏的第三點疑慮,而得出此碑為后人偽托之作的結論。即便假設此碑為偽作,那么,偽托者又何故將“暨”字分寫成“既且”二字呢?豈不終為未解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