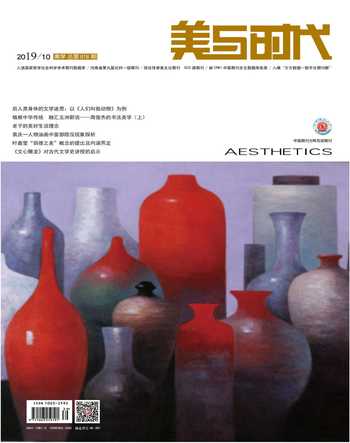老子的美好生活理念
摘? 要:《老子》哲學文本中的“德”“無為”“道”等核心概念含蘊著老子對于美好生活的獨到見解。通過“德”與“得”“無為”與“為”“道”與“無道”這三對相連相通的概念,老子對他的美好生活理念做出了最為精妙和最具洞察力的解釋。其中,厘清“德”與“得”的復雜關系,表達的是人與自我之內外協調;處理好“無為”與“為”的關系中,反映的是人與他人之間,特別是社會治理者與百姓之共存共榮;最后,超越“無道”回歸“有道”,指向的是整個生命世界之和諧永續關系的最高維度。正是這種氣韻生動的生命哲學辯證法,彰顯了老子美好生活理念的根本旨趣。
關鍵詞:老子;美好生活;德;無為;道
老子對于美好生活的理解有其獨到之處,在《老子》哲學文本中,“德”“無為”與“道”等核心概念就含蘊著對美好生活的思考。本文嘗試對這些核心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做出新的闡釋,力求較為真實客觀地反映老子的美好生活理念。
一、“德”與“得”:人與自我之內外協調
“德”是老子哲學思想的核心范疇之一,“有德”是老子美好生活觀的重要組成內容。“德者,得也。”(《禮記·樂記》)在這里,“有德”指的是得道的狀態,“德”即是符合于道之德。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①“孔”即是空,即生命內部沒有那些不合乎于道的異質之物的擾亂。以“孔”為德,就是以“道”為德。以“道”為德,生命本身才能夠動作從容,長久運行下去。
老子重視“有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到現實生活中人們醉心于種種“有得”而忽視“有德”所導致的生命被異化的危機。“有德”與“有得”在老子這里是有重大區別的。“有德”,是指得道;而“有得”,指得器。一個是無名隱匿的形上之道,一個是有形可欲的名與貨,二者有本質不同。老子所批判的“有得”生活,是過分追逐各種官能欲望滿足的物化生活。面對生活中花樣繁多的形名器物,人往往是貪得無厭而不是少私寡欲,各種感性欲望易放難收,并因此給生命自身造成嚴重損害。“馀食贅形。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二十四章)意思是說,人占有的過多器物,就像每日剩飯和身上贅肉,不僅毫無用處,還產生了使人墮落為“物”的危險。人圍繞著種種可欲之器不停旋轉,同時走向“得道”狀態的反面。因此,老子生命減法的哲學一再告誡人要降低對“器”的過度欲望。但是面對各種器物帶給人的即時性快感,人該如何克制欲望、重返自然需要,去過一種“為腹不為目”的“有德”生活呢?這就需要對“得”有一個全面且透徹的認識。
理解“得”,需要厘清“得”與“失”的微妙關系。得失相隨、福禍相依的普遍規律,不僅適用于人自身,同時也適用于人與外物之間的關系處理。得到美好之結果,必然會伴隨著相應損失。問題關鍵就在于所得與所失之間的權衡,反思所得之物是否值得付出所失之物。老子有感于亂世中欲望橫流的現象,發出“得與亡孰病?”的斥問,反思就人自身而言,“得”與“失”究竟哪一個對人更有害呢?(四十四章)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人與生俱來的敏銳感知官能會因過度“有得”而變得遲鈍麻木乃至喪失。當人為了獲取名與貨而大費智慮、棄其所守,甚至產生為物所役的異化狀態時,這種“得”無疑是得不償失。
從個人與外物之間的關系角度來看,當有限資源過分集中于一身,必然會影響到他人生命的圓滿。這一點,我們從當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就可以看出。人類暴力掠奪大自然的果實據為己有,所得之物遠遠抵不上大自然所失。當受損的自然開始對人類世界進行報復,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需要后世一代代人的努力修補才能有所緩解。也就是說,得之過,必然失。當然,在老子所生活的時代,人與自然之間的問題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老子更多地是論述人與人之間的得失關系,在老子看來,只有符合于“德”的“得”,才會是真實的得,這種“得”也即是“德”。“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二十三章)有德之人在求取過程中心中有“道”,十分注意知止、知足、知恥,懂得去甚、去奢、去泰。“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二十六章),因為他時時警惕物化生活,還特別兼顧他人的生命保全。
需要澄清的是,合于道的“有德”生活,并非徹底脫離“有得”,也并非與之截然對立。事實上,這種“德”同時也是“有得之德”。在老子那里,“德”與“得”是相互沖突又彼此需要的關系,二者相互關聯,共同組成人類世界的美好生活。我們看到,美好的“美”字上部是一個“羊”形,在《說文解字》中,“羊”即“祥”。對于上古游牧民族來說,羊多肥美能供人飲膳就是一件吉祥的事。這里表達的是人們對生活基本物質享受的追求,即適度“有得”的生活。老子看到,滿足基本物質需求乃是美好生活的基礎前提。比如《老子》第三章講,人要“實其腹”“強其骨”。百姓需要食、服、居、俗這些必要生活物質保障才能安居樂業(八十章)。而老子的深刻之處在于看到這種“得”絕不能過度,“得”必須符合“德”,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
面對生活中常常出現“得”與“德”之間沖突難兩全的難題,老子提醒我們要“知得守德”,寧可少一點“得”,也要守護“德”。因為“德”(也即是“道”)乃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始源性存在,“德”是種種“得”所由出的“玄牝之門”。《老子》二十三章中說:“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意即“得”只是因順于“德”的水到渠成之結果。反之,不合于德之“得”終究會失去,所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九章)這也正是王弼所強調的“守其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1]95。與此相反,若“舍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1]95。老子強調的“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五十六章)就是在提醒人要充分認識到種種可得器物的非本質屬性,唯有“德”(也即“得道”)才是根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就是說,人得珍寶壁馬,不如得道(即“有德”)。“得”與“德”(道)絕不能一概而論。FB5E4584-9B31-4EFA-B577-D686742CC93D
厘清“德”與“得”的復雜關系,所表達的是人與自我之內外協調的狀態。老子在此反復強調克服過度、感性欲望對于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礎意義。在這里,“得”與“德”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適度張力,“得”必須浸潤于“德”中,才是有“德”之“得”。此時,“德”亦是有“得”之“德”。如此,人即能夠“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1]81,回歸有德的美好狀態,也就達到了“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精神境界(二十六章)。
二、“無為”與“為”:人與他人之共存共榮
“無為”是道家哲學的重要概念,主要針對社會治理方面,指的是因循“道”的自然狀態。無為之“無”,是相對于沒有“偽”而言,即沒有妄為和強為;無為之“為”,是有德之為,是因循大道的行為,也就是“法自然”之為(二十五章)。老子說,圣人應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意思是說社會治理者要居處、行走在大道的正路上,因循大道之清靜無為的自然狀態。這樣才能達到民風淳樸、清明安定的美好社會。
老子倡導治理者采取無為治理原則是有較強現實針對性的。春秋戰國時期,正值亂世,社會治理者為了挽救搖搖欲倒的禮樂制度等上層建筑,急于采取各種“有為”政治措施以亡羊補牢。但事實上,正是盲目“有為”治理,才是六親不和、國家昏亂、偽智泛濫,乃至大道廢棄的真正禍源(十八章)。有為治理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是妄為。所謂“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五十八章)這里的“奇正(政)”即是妄為。治理者若出于私欲而肆意妄為,就會嚴重擾亂生命自然狀態。老子解釋道:“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在這樣的社會中,治理者不相信“無為”治理能使百姓自身所具有的生長秩序自然展現,人的步步行動被周遍細密的政令指揮著。百姓亦不相信如此的“有為”治理會給他們帶來美好生活。由此,人與人之間互相懷疑,詐謀奇計滋起,各種不符合自然常道的社會怪象層出不窮。
有為治理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強為。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二章)老子對美好社會的理解是很不尋常的。他認為美一旦成為像名利一樣的可欲之物,就極容易具有標準化、絕對化的意識形態。這時美就不再是客觀普遍的真理,而會成為一種權力話語。相應地,不管以何種“美名”把廣大百姓鉗錮于某一剛性標準之下,都必然會破壞百姓原本豐富多樣的真實本性和意愿。人或不自覺地成為強權工具;或競心紛起成為名利欲望的奴隸;或躲避在現實之外只求自保;或表面服從做消極抵抗。只有少數人愿意犧牲自己,幻想沖破固化規制。顯然,老子認為這種違背百姓自然本心的強為治理,就是不美、不善的。
老子認為能托付天下的人,正是這些能夠深刻認識到“妄為”和“強為”治理巨大危害的人。老子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只有珍視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給他來治理。因為一個真正愛惜自己生命的人,不會任由自己被政治權力欲望擺布而肆意妄為,而是做好自己生命的主人。這里的“愛身”,指的是治理者對待百姓之身的態度。以百姓之心為心,不把百姓強硬統一在某一固定標準之下,真正把百姓的美好生活作為治理的終極目的。事實上,強硬的“有為”治理本來就不可能實現。世人的品性有行有隨,有覷有吹,有強有羸,有載有隳,具有無限豐富多樣性和不斷生成性(二十九章)。生命神圣,難以按照把握物的簡單邏輯來把握人的存在。因此“強為”就一定會敗之、失之,難以實現美好生活的真義。
老子倡導的無為之治,與“妄為”和“強為”的有為治理是完全不同的。但需要注意,無為絕不是表面意思所理解的毫無作為。它不是空,而是內含著有。實際上,無為乃是內在含蘊著“有德之為”,它時刻在因循著大道而為。這就是老子推崇的“無為之為”。大道之為,就體現在大道包容萬物、成全萬物和收留萬物的整個過程之中。
大道包容萬物。萬物能夠在無為大道的這個空疏開闊的生命場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章)。大道無所偏私愛矜,萬物在其中各得一席。當其中異質之物產生矛盾時,大道能夠祛除其虛假對立鋒芒,甚至能使天上之光和地面塵土都于其中和諧共處。相應地,大國治理者若能循道而治,就能使得小國安全地見容于大國,大國亦能平穩會聚小國,使之和平相處、各得其所(六十一章)。
大道成全萬物。它善利萬物而不爭(八章),滋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與大道的關系就像魚與淵一樣,各種生命能依照各自稟賦,自由平等地在大道生命場中勃勃生長,無累無抑,無爭無礙。大道像世界的終極治理者,更像是生命的守護人。類似地,老子“烹小鮮”治國之策(六十章),認為治理大國不能大動干戈,攪得人人不得安寧。他強烈批判“妄為”和“強為”等有為治理,正是為了使百姓能夠順應生命內在生長機制而自然發展。
大道收留萬物。老子說:“道者萬物之奧。”(六十二章)這里的“奧”是說大道乃是萬物的庇護之所。萬物的生長即是離道而去的過程,他們依各自本性,自由地成就自己。但這個過程并不是單向道,待功名既有,萬物又自覺重返其所由的大道,正如川谷復歸于江海(三十二章)。所謂“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八十章),就是特別重視生命的最終完成與歸宿。讓生命有始有終,使生命不總是處在離道向外行走的無盡漂泊歷程中。待每一個生命完成自己天命之后,自覺復歸于大道,從而對于整個生命歷程無所抱怨、無所執戀、無所愧憾,始終處于順我所自然的安寧狀態。總之,因循道的自然狀態,就體現在大道包容、成全和收留生命的整個過程之中。治理者只有循道而為,才能夠使萬物共生共榮。
正確理解有為與無為生活的關系,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特別是社會治理者與百姓之間的共存共榮狀態。老子所反對的“有為”,是那些出于治理者私欲的妄為和霸道強為。而無為大道是“有德之為”,事實上它時時在循道而為。在這里,無為大道顯然無法以簡單的“有為”或“無為”來界定了,因為它本身已將這二者圓融無礙地包含在自身之中,是“有為”,亦是“無為”。遵循這種無為大道來治理社會,便自然實現“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共生同榮的美好社會(五十八章)。FB5E4584-9B31-4EFA-B577-D686742CC93D
三、“道”與“無道”:生命世界之和諧永續
美好生活面向屬人的生活世界,在“德”與“得”“無為”與“為”兩對核心范疇中,明確表達了老子哲學思想中關于人與自我之內外協調的狀態,人與他人之間的共存共榮狀態。但是,老子對美好生活的思考并不局限于人類社會中。老子的道乃是對于整個生命世界的終極關懷。如果我們把“德”理解為“得道”的狀態,把“無為”,理解成“循道”的狀態,那么,道就是含蘊在“生生不息”生命世界的一種和諧有序狀態。“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十六章)這里的“常”,是指“道”。理解“道”,人的行動就會從容,社會就能平等公正。君王之道、自然之道都因遵循這個普遍常道而得以周行不息。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三十章)與有道完全相悖的狀態就是“以兵強天下”的無道。在老子看來,人類世界中最大的無道就是戰爭。戰爭是人類“有得”感性欲望的極度膨脹,是人類種種“有為”的極端顯露。老子反對戰爭,與他對感性欲望的批評態度是根本一致的。老子說:“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意思是說,沉潛于水中的魚兒不能躍出水面暴露自己,國家的鋒利兵器不能隨意拿出來顯耀。否則,就是驕、伐、矜,是種種欲望的表露,容易被歙之、弱之、廢之、奪之,難以長久。與之不同的是,柔弱兒童之所以不會被兵器所傷,就在于赤子沒有過分欲望,不掠取、不侵擾他物。老子推崇君子對待戰爭勝而不美的恬淡態度,正是因為君子能夠克服由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巨大名利的欲望。追逐欲望足以使人走向死路,人若能戰勝欲望,也就擺脫了“死地”(五十章)。
老子反對戰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戰爭是最為殘酷的有為手段,是對生命的極度漠視。“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四十六章)在無道的社會中,小馬生于戰場,婦女和兒童去參戰赴死。老子深刻意識到戰爭對生命的巨大危害,因此他說:“殺人之眾,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三十一章)這里所體現的是對生命的尊重、珍惜和崇尚的態度。沒有遭受過戰爭的摧殘,難以意識到活著的幸福與生命的寶貴。老子關于戰爭的警戒,對于長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義無反顧地追求美好生活的人們來說,顯得尤為可貴。“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八十章)應該是我們對待戰爭的根本態度。留有武器,是為了保護生命不受暴力破壞;不輕易使用武器,同樣是為了保護生命的自然安寧狀態。要之,當人類戰勝了戰爭的欲望,突破了“有為”的層次,也就真正走向了“生生不息”的和諧有序狀態。
超越無道,回歸有道,是老子美好生活觀的根本追求。老子之道并不是脫離現實、高高在上的外在于人的“天帝”,而是如日常生活隨處可見、可感的活水泉源。有道的世界始終處于一種生動而有序的不斷發展的狀態之中,這就是一種永續不息、變動不居、有序和諧的狀態。
道是永續不息的。大道“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它作為天下之始母,綿綿若存,衣養萬物而用之不竭。(六章)大道總是處在造生萬物、包容萬物、成就萬物和收留萬物的無盡運動過程中。“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二十一章)。意即萬物經由大道之門開闔而獲得生命,同時在返本復初的漫長旅程中來理解自身生命存在的意義。老子所言的“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道。它致虛、貴柔,以下為基,以無為為本。老子之所以特別重視這些弱性品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乃是生命的象征,充滿著生長能量。大道虛而不空,在空疏中能容納各種生命;大道弱而不衰,它隨物而予,盡心呵護生命;大道下而不賤,篤靜居下,不宰制生命;無為而無不為,方能任生命自由生長。以嬰孩為代表柔弱之物,是生命體的起點與根基,他骨弱筋柔卻握固,終日哭嚎卻音不啞,形雖小而猛獸不侵。人類正是在生命展開和成長的過程中,才充分發揮了自身“潛藏”的神跡。萬物生命的律動伴隨著道的不息運動,從容不迫地展露出自身的生命氣息來。
道是變動不居的。大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它無名無形無音,難以把捉。它隨時隨境而改變,是無竟的可能性,永恒的無定存在(二十一章)。老子說:“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十四章)就是在告訴我們,所謂大道運行的規律(即“道紀”),絕不是被規定好了的現成之物。“道”不是教條,我們只能在當下的日常生活的變化中來感知它。那么,我們是如何感受到道的變動呢?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四十章)是說生命的狀態若發生相反的動勢時(如由弱變壯,由缺轉盈,由低變高),特別是在朝向生命初始本根的返回運動過程中,道的作用就開始顯現出來了。老子把這個生命世界比喻成一個巨大的風箱,它“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章)生命體正是在一呼一吸的發動過程中,不斷汲取營養、釋放能量,進而達到平衡,因此得以“生生不息”。這樣來看,道盡管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搏之不得,但其中確有精、有真、有信,豈虛言哉!
道是有序和諧的。大道的運動變化不是亂序急躁,而是循序漸進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二十六章)就是說,有道之人能夠在輕與重、靜與躁的兩極之間掌握分寸,不偏執于一端,在二者之間達到平衡協調。身處亂世,老子感嘆:“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十五章)在眾人對某一事件趨之若鶩時,老子提醒人們,有道之人要回歸致虛守靜的沉靜狀態,使外界紛擾隨時間發展而慢慢沉淀下來,才能靜觀事情本然面目。而當一切喧鬧歸于寧靜之后,有道之人還要在無趣中創造出活力,防止生命固化僵死,緩緩活動起來,使萬物有條不紊地恢復活力。正是因為大道有序運行,才使得各種生命在道生、德畜、物形與勢成的整個運行過程之中處于和諧狀態。所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五十一章)。
超越無道,回歸有道的生活,指向的是整個生命世界之和諧永續關系的最高維度。“生生不息”乃是老子對生命世界的最大期待。盡管老子愛人、相信人,對人的未來生活充滿美好期待,但他對現實人類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無道”行為卻有著極為清醒的體知。所謂“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五十三章)、“人之迷其日固久”(五十八章)老子對于處于亂世中人們的種種妄為和強為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并沒有因為對現實失望就放棄對有道的追求,而是像蘇格拉底一樣不斷警醒君主和百姓莫忘“道”,去過一種有道的生活。他殷切希望每一個生命體能夠平等、自然地勃勃生長,整個生命世界生生不息地有序和諧運轉。
四、結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八十一章)老子對于美好生活的深刻思考,常常是在批判那種人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有得”“有為”和“無道”生活。老子認為美好與不美始終是作為一對相互糾纏的矛盾體出現的。美與惡同根,善與不善同門,美好生活與不美生活往往相生相隨。這樣一來,仔細甄辨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各種包裝巧妙的“有得”“有為”和“無道”,時刻警惕美好異化就成了必須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氣韻生動的生命哲學辯證法中,老子美好生活理念的根本旨趣得以彰顯。
通過“德”與“得”“無為”與“為”“無道”與“道”這三對相連相通的概念,老子對他的美好生活觀做出了最為精妙和最具洞察力的解釋。相比于成書之時,現在看來,其真實性和適用性愈發強大。在人們處理“有得”與“有德”生活的之間關系時,老子警醒人們要減少對身外名利的過度欲望。現代社會處于人類歷史上物質文明最為發達的時期,社會的商品化力量空前增強,人們只有自覺擺脫物化生活,在滾滾物欲中堅守自然本真之德,才能理解美好生活的真諦。在“有為”與“無為”生活之間,老子批判了社會治理者不顧生命自然生發規律而任意妄為、強為的管理方式。我們正在經歷著中國社會發展轉變最為頻繁的時代,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盤根錯雜,聯動性和風險性都大大增強,想實現一種好的治理變得越發困難。人們日益繁忙焦躁,離老子推崇的“無為”狀態愈加遙遠。突破妄為和強為,走向自然無為,才能真正實現無為之治的美好社會。超越“無道”回歸“有道”的生活,充分表達了道家哲學對于整個生命世界的深切關懷。老子對人生命內在具有的純真與神圣有極大追求,他堅信人人都可以感受美好,每個生命體只要依憑自我內在生長機制就可以圓滿自身,從而使自己合于“道”。人們也只有在這種實踐方式、思維方式和生命方式中,才能一步步更加靠近美好生活。
注釋:
①《道德經》,下文沒有注明出處的,均引自本書,不再注明。
參考文獻:
[1]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注校釋[M].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2008.
作者簡介:馬珊珊,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FB5E4584-9B31-4EFA-B577-D686742CC93D